作者:
凌宗亮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审判员
付 凡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法官助理
【裁判要旨】
著作权法对作品独创性的要求虽然不高,但并不是没有要求,特别是对于商业标识是否构成著作权法中的作品,应当着重审查该标识的审美和艺术价值。在具体认定中,还应当注意区分创意和对创意的表达之间的关系。即使对图案的设计可能体现了设计者高超的创意,但著作权法保护的是表现创意的外在表达,因此,过于简单、缺乏一定美感和艺术价值的表达,不应作为美术作品进行保护,否则将会影响公共元素在美学领域的正当使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基本案情】
原告:上海布鲁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布鲁可公司)
被告:广州橙奥科技有限公司,原名比特橙子(广州)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橙奥公司)
被告:上海橙季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橙季公司)
原告布鲁可公司成立于2014年,原名上海葡萄纬度科技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积木、教育、动画等,在儿童编程教育领域具有一定知名度。布鲁可公司于2015年创作完成等系列图案(以下称葡萄头图案),并自创作完成之日起即通过举办产品发布会、参加展会以及新闻宣传报道等形式,持续对外公开宣传使用上述作品。2016年11月21日,布鲁可公司将其中的
图案申请注册为第18066681号商标。2018年10月18日,上海市版权局出具沪作登字-2018-F-01198370号《作品登记证书》,将布鲁可公司的
图案登记为美术作品。2020年1月23日,上海市版权局出具沪作登字-2020-F-01567671号《作品登记证书》,将布鲁可公司的“
”图案登记为美术作品。
被告橙奥公司成立于2017年,主营业务为儿童编程教育,在北京、成都、广州、上海等地成立多家关联公司,开设门店进行经营。橙奥公司于2018年委托案外人创作“”图案(以下称橙子图案),并于同年将该标识注册为第32719589号商标,在帆布袋、服装、门店显著位置使用。被告橙季公司作为橙奥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实际经营“比特橙子编程学院(上海浦东世纪汇店)”。
原告布鲁可公司认为:橙奥公司、橙季公司使用的橙子图案与其在先创作完成的葡萄头图案构成实质性相似,侵犯了其著作权。据此,原告布鲁可公司提起侵害著作权纠纷之诉,请求法院判令两被告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并赔偿经济损失、合理开支共计106万元。
被告橙奥公司、橙季公司辩称:两被告使用橙子图案未侵犯原告著作权。第一,橙子图案系由橙奥公司独立设计完成并已申请著作权登记,与葡萄头图案不存在相似,也不会导致消费者误认;第二,橙子图案与葡萄头图案的相似部分即类似机器人脸的动漫表达形式,属于社会公有领域的惯常表达,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第三,即使认定相似,原、被告双方的主营业务差别很大,两被告不存在接触原告葡萄头图案的可能。
【裁判结果】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原告布鲁可公司主张权利的葡萄头图案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美术作品,两被告作为原告的同业经营者,存在接触葡萄头图案的可能性,但葡萄头图案与橙子图案不构成实质性相似,二者的相同部分属于不受到著作权法保护的公有领域表达,故判决驳回原告布鲁可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原告布鲁可公司不服,向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提起上诉。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二审认为,首先,原告布鲁可公司主张权利的葡萄头图案不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美术作品。著作权法对作品独创性的要求虽然不高,但并不是没有要求,特别是对于商业标识是否构成著作权法中的作品,应当着重审查该标识的审美和艺术价值。在具体认定中,还应当注意区分创意和对创意的表达之间的关系。即使对图案的设计可能体现了设计者高超的创意,但著作权法保护的是表现创意的外在表达,因此,过于简单、缺乏一定美感和艺术价值的表达,不应作为美术作品进行保护,否则将会影响公共元素在美学领域的正当使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中,原告布鲁可公司主张权利的葡萄头图案是对面部形象的惯常设计元素予以简单的组合和取舍,虽具有一定的创意,但该创意的外在表达尚无法达到著作权法保护美术作品所要求的审美意义和艺术性,不满足美术作品最低限度的独创性要求,不构成受到著作权法保护的美术作品。
其次,即使认定原告布鲁可公司主张权利的葡萄头图案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美术作品,但通过局部比对,二者相同部分的表达形式在美术作品创作领域较为常见,属于公有领域范围;通过整体比对,二者在色彩选取、构图、含义、整体视觉效果上均明显不同。因此,葡萄头图案与橙子图案不构成实质性相似,二被告的行为不构成著作权侵权。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例评析】
我国商标法规定的可作为商标申请注册的客体,包括文字、图形、字母、数字、三维标志、颜色组合和声音等。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可作为作品受到保护的客体,包括文字作品、美术作品、摄影作品等。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客体类型的重合导致商业标识可能同时构成商标法和著作权法的保护客体,受到双重保护。实践中,许多商标专用权人亦通过此种商业标识作品化的方式,延伸其知识产权权利边界。但商业标识是否具有受到著作权法保护的正当性,如果有,商业标识作品化的构成要件、保护类型等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明确。
(一)商业标识著作权保护的正当性基础
关于商业标识作品化后不具有双重保护正当性的观点,主要是基于知识产权选择原则理论而作出的。根据知识产权选择原则,当商业标识既可以受到商标法保护,又可以受到著作权法保护时,由于知识产权各保护形式间界限分明,故权利人获得其中一种形式的保护,即视为自动放弃了其他形式的保护。【1】在知识产权选择原则的控制下,权利人无论是将美术作品用作商标或装潢,就其使用方式和法律性质而言,都是一种质变,此种变化导致美术作品从具有文学和艺术价值的美的产物嬗变为具有实用和商业价值的工业复制品,因而该美术作品的著作权应当在其被用作商标或装潢之际即穷竭。【2】其次,也有观点认为双重保护模式的存在将造成权利保护的无序扩张,从而致使创新成本不断提高,创新回报的分配产生失衡,进而制度异化,导致对“知识公地”的侵占。例如,商业标识作品化后将使得商标的保护类别从按类保护扩展至全类保护,保护地域从某一国家扩展至世界多国,权利取得从申请注册转变为自动取得等。
1.商标权与著作权之间并非界限分明
商标权与著作权固然属于两个不同种的知识产权保护形式,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二者并非呈现出割裂、独立的形态。在当前知识经济时代,美术作品大多通过艺术衍生品的形式赋予其新的时代价值。艺术衍生品,是指以原美术作品为基础创造的类工艺产品,既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又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是对原美术作品审美与艺术价值的进一步挖掘,使得美学设计能够充斥于日常生活当中,契合社会公众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需要。正如有学者所言,商业标识的“审美”与“认知”两功能是分不开的,社会公众对商业标识产生认知可能及认知记忆的前提在于其具有一定美感、令人难以忘怀,否则生产商为何专门选择名家绘画作品用作商标,而不是为了避免任何权利冲突自己随意乱画几笔去作商标呢?【3】由此可见,商标权与著作权并非完全对立,商标的认知构建需以具备一定审美价值为基础,而作品艺术价值的高低同样与其知名度即认知程度的多少密不可分。因此,知识产权选择原则本身即不符合现实的生产生活实际,审美价值与认知功能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知识产权各保护形式间亦并非界限分明。
2.双重保护模式不会致使利益失衡
就知识产权利益平衡而言,首先,商标权与著作权虽然可对同一客体进行保护,但双重保护与利益失衡并不具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以明星自拍照为例,该明星对自拍照同时享有肖像权和著作权,且肖像权与著作权的保护目的均在于防止他人未经许可使用或篡改,但理论与实务中却不存在主张此类双重保护模式将导致利益失衡的相关观点。其次,双重保护模式的存在并不会造成权利保护的无序扩张。商标法的立法目的在于维护商誉、防止混淆,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则在于促进文化和科学事业的繁荣发展;商标权的禁用范围包括禁止他人在相同或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业标识,著作权的禁用范围则仅限于禁止他人对作品进行复制、抄袭,而无法禁止他人在未复制、抄袭的情形下进行与作品相同或近似的创作。立法目的与禁用范围的不同导致商标权与著作权的保护范围各有侧重,因而不会造成权利保护的无序扩张。即使认为商标权与著作权的保护范围存在重叠,此种重叠亦不会导致利益失衡。主张利益失衡观点的依据在于,若给予商业标识著作权保护,著作权保护并不存在类别上的限制,将导致有限的商标资源被进一步挤占,后来者在设计商标时的创新成本将进一步提高,但成本的提高却无法相应地扩充公有领域的知识含量。该观点实际上混淆了双重保护模式的前提,即并非所有商业标识均能获得著作权法保护。获得著作权保护的前提在于作品本身具有独创性,能够达到一定的创作高度,但商业标识的设计出于易被消费者识别记忆的目的,往往不会采用较为复杂的设计,例如耐克公司、苹果公司等商业标识的图案设计虽然在商标法领域具有很高的知名度,但因其仅是由公有领域常见设计元素而得,不具有独创性,故无法受到著作权法保护。因此,由于著作权法并不对公有领域的设计元素和简单常见的图形、字母、短语等予以保护,故赋予商业标识双重保护并不会抢占商标领域的公共设计资源,亦不会提高后来者的创作成本,契合知识产权保护的利益平衡原则。
(二)商业标识作品化的保护模式:实用艺术品
实用艺术品,是指具有实用功能的美术作品。我国著作权法将绘画、书法、雕塑三类列举为法律明文规定的美术作品类型,虽然其未明确将实用艺术品作为美术作品进行保护,但是作品类型一般具有举例和指示意义,未明确指明的作品类型,可能属于某作品类型项下,也可能属于符合作品构成要件的无名作品。【4】同时,《实施国际著作权条约的规定》第六条明确规定对外国实用艺术品给予保护。因此,实用艺术品属于我国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
商业标识作为商业活动中识别商品来源作用的标识,是工业生产的产物,这也是为什么商标权往往和专利权一并被称为工业产权。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美术作品大多通过衍生工业品的形式赋予其新的时代价值,而传统工业品亦为了迎合人们的审美和生活需要增添更多的艺术设计元素。因此,工业产权与著作权呈现出融合趋势,而实用艺术品正是此种融合趋势背景之下的产物。
实用艺术品一方面能够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便利,另一方面也能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美感,兼具实用性和艺术性。实用性要求其能够被批量生产、制造,满足人们某种生产与生活的需求;艺术性则要求其具有审美价值和美学追求。从实用艺术品的特征出发,商业标识作品一方面能够批量应用于工业领域之中,满足人们识别商品来源的需求,降低选择成本,实现良好的经济效益,具有实用性;另一方面能够被复制在商品或服务的包装、广告之上,满足人们对美的追求,具有艺术性。因此,商业标识作品符合实用艺术品的两大基本特征,可以作为实用艺术品进行保护。
有观点认为,商业标识受到著作权法保护将使得权利人怠于申请商标注册,对商标注册制度造成严重冲击。实用艺术品的保护模式恰能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就保护期限而言,商标法的保护期为十年,但可无限次续展;而《实施国际著作权条约的规定》第六条明确规定实用艺术品的著作权保护期仅为二十五年,远远短于传统作品的五十年保护期,且无法延续。就保护力度而言,著作权法对于传统美术作品,只要在后作品的权利人能够证明作品系独立创作完成的,在后作品亦可享有著作权;但《实施国际著作权条约的规定》第六条明确将美术作品用于工业制品的排除适用,事实上排除了商标权人使用他人在先创作的美术作品作为商标从而获得双重保护的可能,即实用艺术品仅限于权利人出于实用艺术目的创作的作品,不包括权利人出于实用目的使用的在先美术作品,防范商标权人通过投机行为获得双重保护抢占知识资源。
(三)商业标识著作权保护的构成要件
诚然,商标权人有权通过双重保护模式实现商业标识的充分保护,但能否获得双重保护的关键仍在于该商业标识是否属于著作权法所保护的实用艺术品。因此,不能仅因商业标识具有显著性或知名度较高而当然认为其构成作品,仍应回归著作权法本质进行判断。根据著作权法原理,实用艺术品应当符合以下三个条件才能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第一,实用功能和艺术美感能够相互独立;第二,独立存在的艺术设计是独立创作的;第三,艺术设计应达到一定的创作高度。【5】
1.实用功能和艺术美感能够相互独立
实践中,实用功能和艺术美感的相互独立主要包括两种,即物理层面的相互独立和思想层面的相互独立。就商业标识作品而言,具有实用功能的标识图案和具有艺术美感的作品图案无法融为一体,无法实现物理层面的相互独立。因此,判断商业标识作品的实用功能和艺术美感能否相互独立,应从思想层面着手,判断其实用功能对应的艺术美感表达是否唯一。当商业标识的实用功能部分设计空间较大,即表达方式多样时,可以认为该商业标识的实用功能和艺术美感能够相互独立。但如果商业标识的实用功能部分由于受到功能的限制,表达方式唯一或者仅具有有限的表达方式时,则其实用功能和艺术美感无法相互独立,不应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6】
2.独立存在的艺术设计是独立创作的
著作权法所要求的独创性中的“独”意指作品由作者独立创作产生。因此,实用艺术品所保护的作品,其艺术设计部分应是由作者独立创作完成的,而非利用他人已有作品,仅通过改变作品载体,将其再现于实用品之上。正如上文所述,将美术作品用于工业制品的,不构成著作权法所保护的实用艺术品。
3.艺术设计应达到一定的创作高度
关于作品的创作高度问题,主要有“高低论”和“有无论”两种观点,“高低论”认为作品应达到最低限度的创作高度才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有无论”则认为无论创作是否达到一定创作高度,只要与他人的表达不同,即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对此,我们认为,虽然我国著作权法对创作高度的要求不高,作品既可以指“阳春白雪”,也包括“下里巴人”,但并不意味着对创作高度没有要求,即受到著作权法保护的商业标识应当达到最低限度的创作高度。【7】原因在于:
第一,我国著作权法相关规定明确将达到一定创作高度作为美术作品的构成要件。根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的规定,美术作品,是指绘画、书法、雕塑等以线条、色彩或者其他方式构成的有审美意义的平面或者立体的造型艺术作品。但从该条例的规定出发,其明确将具有审美意义作为美术作品的构成要件,实际上是要求美术作品必须达到一定的创作高度,因此商业标识作品化同样应以达到一定创作高度、具有审美意义作为构成要件。
第二,我国司法实践亦以商业标识是否达到最低限度的创作高度作为认定其是否构成作品的依据。在“卫龙案”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 ”商业标识由汉字“卫龙”和拼音“Weilong”经简单排列组合而成,虽然对其中的拼音首字母“W”进行了一定的图案处理,但此种程度的处理无法使该商业标识达到美术作品所要求的创作高度,因此不构成著作权法所称的美术作品。【8】在“BEABA案”中,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
”商业标识由汉字“卫龙”和拼音“Weilong”经简单排列组合而成,虽然对其中的拼音首字母“W”进行了一定的图案处理,但此种程度的处理无法使该商业标识达到美术作品所要求的创作高度,因此不构成著作权法所称的美术作品。【8】在“BEABA案”中,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 ”商业标识从美术作品的角度考虑,虽然采用了将字母加粗、将“A”“B”字母中空之处做填充处理的变形方式,但这种艺术化处理方式与在线字体设计相比,仅在边缘角度等处存在细微差别,未达到基本的创作高度,因此不构成作品。【9】在原告上海是你商贸有限公司与被告深圳影儿时尚集团有限公司等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纠纷案中,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在认定服装是否具有独创性时指出,服装的艺术性部分只有具有艺术美感才能符合美术作品的独创性要求,虽然艺术美感与艺术高低无关,但仍需能够体现作者具有个性的安排和选择,因为著作权法调整的是“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的表达,如果相关公众无法将某一服装归入“艺术”领域,则其仅系实用品而归入专利、商标等工业产权的保护范畴。【10】
”商业标识从美术作品的角度考虑,虽然采用了将字母加粗、将“A”“B”字母中空之处做填充处理的变形方式,但这种艺术化处理方式与在线字体设计相比,仅在边缘角度等处存在细微差别,未达到基本的创作高度,因此不构成作品。【9】在原告上海是你商贸有限公司与被告深圳影儿时尚集团有限公司等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纠纷案中,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在认定服装是否具有独创性时指出,服装的艺术性部分只有具有艺术美感才能符合美术作品的独创性要求,虽然艺术美感与艺术高低无关,但仍需能够体现作者具有个性的安排和选择,因为著作权法调整的是“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的表达,如果相关公众无法将某一服装归入“艺术”领域,则其仅系实用品而归入专利、商标等工业产权的保护范畴。【10】
本案中,原告布鲁可公司诉称其设计的葡萄头图案独创性较高,但从美术作品的角度考虑,首先,在设计理念的表达方面,葡萄头图案虽然采用了以圆点表示眼睛、椭圆形状表示面部、纯色填充表示额头的设计理念,但该设计理念极为简单且平常,在现有拟人化面部形象设计领域较为常见。其次,在图案的整体构成方面,由于原告布鲁可公司设计及使用葡萄头图案主要是作为商业标识使用,图案的整体构成较为简单,能够赋予艺术创作高度的空间极为有限,难以达到著作权法保护美术作品所要求的审美意义和艺术性。
(四)商业标识著作权保护的创作高度认定
著作权法相关规定及司法实践皆认可商业标识作品化应以达到一定限度的创作高度为构成要件,避免文艺创作与实用功能之间的相互垄断。但在具体认定过程中,还应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达到一定创作高度的应为艺术设计表达,而非艺术设计理念。“思想应如空气那样自由,没有人能对他主张所有权”。【11】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每一次的思想解放与创新发展无一不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完成的,若将思想纳入著作权保护范围当中,固然可以增强对于权利人的保护力度,但却会使得后人的再创作过程变得困难重重。著作权制度的立法目的在于激励文化创作、促进文化传播,因此,为了避免“公地悲剧”,我国著作权法明确规定其保护的客体是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智力成果”。《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第九条第二款亦明确表示,版权的保护仅延伸至表达方式,而不延伸至思想。在原告北京全脑立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与被告北京翼趣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等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案中,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认为,以眼睛流泪的形式表示“哭”,以米粒造型表示“米”,以萝卜造型表示“萝卜”等均采用形象表达方法,通过选取与汉字字义相关的元素、色彩等排列组合成美术字,该表达方法属于思想的范畴,不受著作权法的保护。【12】
第二,商标法中的显著性并不等同于著作权法中的独创性。著作权法规定的独创性,是指独立完成且达到一定创造高度的具有文艺或科学美感的智力劳动成果。商标法规定的显著性,是指用于特定商品或服务的标志具有的识别该商品或服务的来源,从而能够区分市场中提供同种或类似商品或服务的提供者的特性。商业标识是否具有显著性与其是否具有独创性属于两种保护形式背后两个毫不相干的法律问题,即使认为其具有一定关联,那么此种关联实质上亦属于反向关联。商业标识的显著性高低取决于其识别商品来源作用的大小,商标权人通过广泛、突出性使用,使得相关领域的消费者对商业标识产生强烈印象,进而对该商业标识背后的商品或服务所熟知。因此,商标权人在设计商标时,为了提高其识别商品来源的作用,便于消费者记忆和传播,通常会选用简洁明了的图案。但美术作品的独创性往往体现于作品通过线条、色彩等元素表达的视觉艺术效果中,若商标图案过于简洁明了,反而无法体现作者的个性化表达,因而不符合独创性的基本要求,不构成作品。例如,美国耐克公司的“![]() ”商标作为国内外驰名商标,早已深入每个消费者的心中,就该图案本身而言,简洁明了的“对勾”形象令其跨越语言和国界取得了突出的显著性,但正因如此,使得一般社会公众难以认定其具有一定的审美意义和艺术美感,构成美术作品。
”商标作为国内外驰名商标,早已深入每个消费者的心中,就该图案本身而言,简洁明了的“对勾”形象令其跨越语言和国界取得了突出的显著性,但正因如此,使得一般社会公众难以认定其具有一定的审美意义和艺术美感,构成美术作品。
第三,享有著作权登记证书并不代表其当然享有著作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根据《作品自愿登记试行办法》第一条的规定,为维护作者或其他著作权人和作品使用者的合法权益,有助于解决因著作权归属造成的著作权纠纷,并为解决著作权纠纷提供初步证据,特制定本办法。由此可见,作品登记制度的目的及著作权登记证书的意义并不在于解决智力劳动成果是否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这一问题,而是在于明确该成果的创作归属者,以便在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时明晰权属。同时,著作权登记制度仅对智力劳动成果进行形式审查,其中的作品属性、创作时间等登记事项均依赖于申请者自行填报,国家版权局对此不作实质审查,在有证据证明著作权登记证书登记的内容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的情形下,该登记证书亦可被推翻。因此,著作权登记证书不能作为商业标识构成作品的直接证据,司法实践中仍应采用个案认定的方法对商业标识作品化的法律属性进行最终认定。
本案中,原告布鲁可公司以已获得著作权登记证书为由主张其对葡萄头图案享有著作权。但著作权登记证书的目的仅在于初步确权,享有著作权登记证书并不代表商业标识图案必然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布鲁可公司是否办理著作权登记与葡萄头图案是否构成作品不具有必然联系,未办理登记但具有一定创作高度的商业标识图案同样可以构成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
注释:
【1】凌宗亮:“失效的外观设计专利仍受著作权法保护”,载《人民司法·案例》2010年第4期。
【2】刘春田:“‘在先权利’与工业产权——《武松打虎》案引起的法律思考”,载《中华商标》1997年第4期。
【3】郑成思:“‘武松打虎’图法院判决及行政裁决引发的思考”,载《法学》1997年第10期。
【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申4397号民事裁定书。
【5】王迁:《知识产权法教程(第六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1月,第77-80页。
【6】参见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申4397号民事裁定书。
【7】王迁:《知识产权法教程(第六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1月,第37-38页。
【8】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高行终字第546号行政判决书。
【9】参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浙民申3362号民事裁定书。
【10】参见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21)沪73民终880号民事判决书。
【11】李雨峰:“为什么著作权不保护思想”,载《电子知识产权》2007年第5期。
【12】参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8)京73民终1383号民事判决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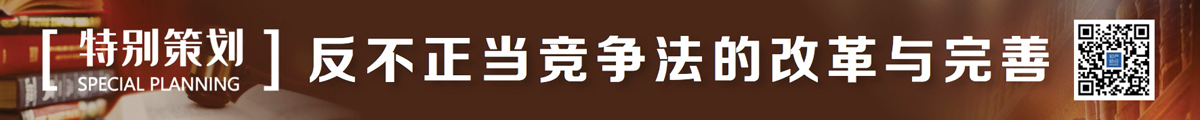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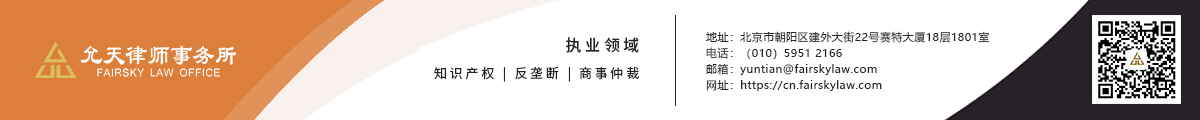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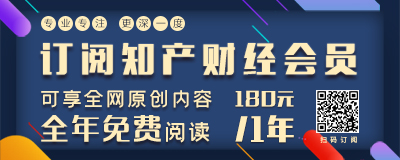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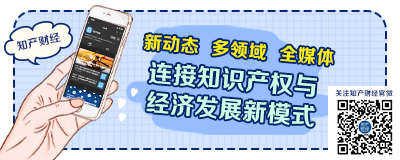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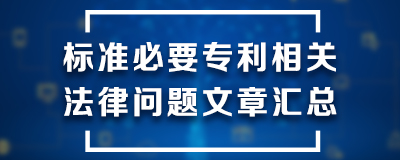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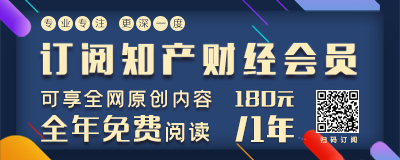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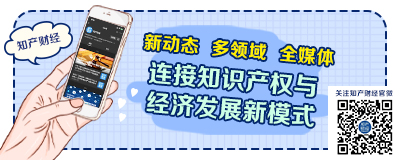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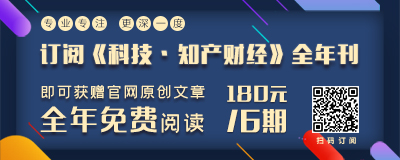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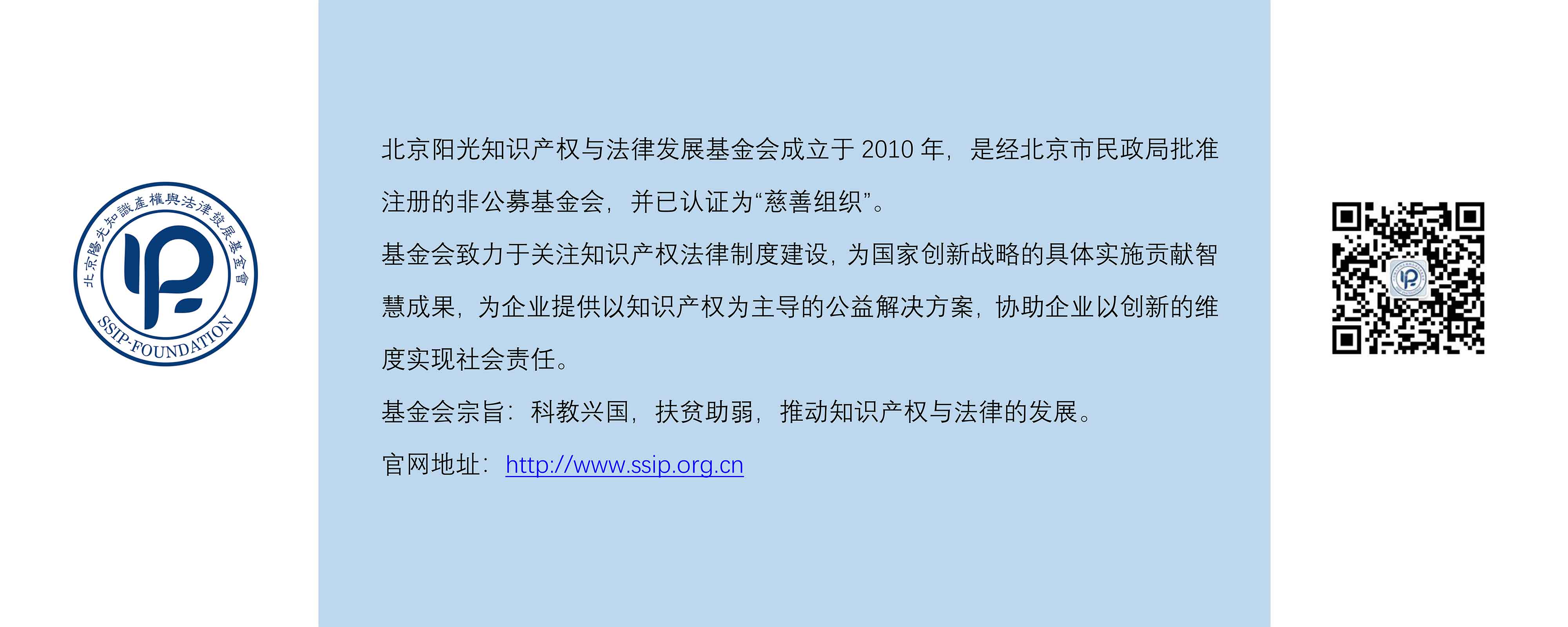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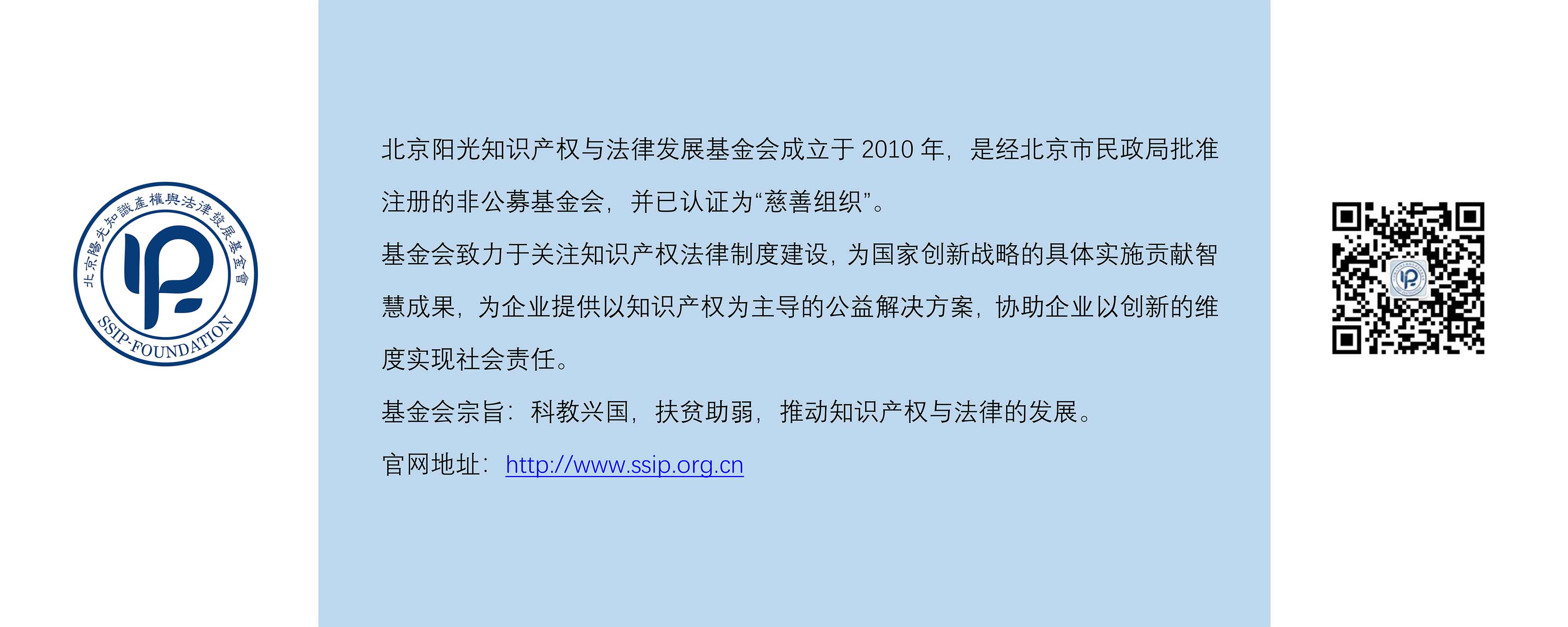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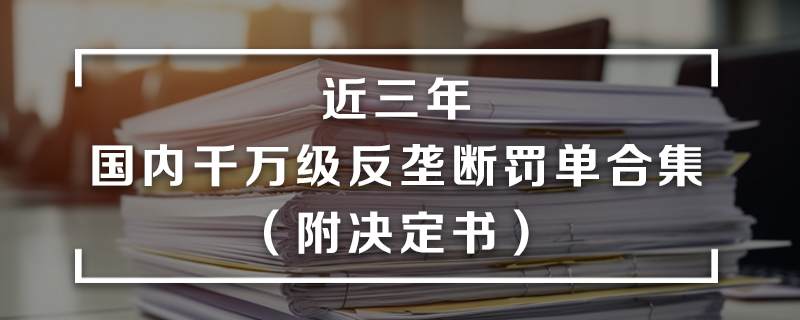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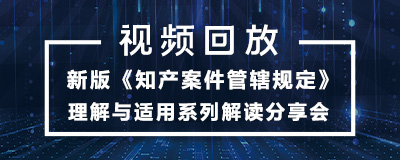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9464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946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