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洪燕 清华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法研究中心秘书长、创新合规研究中心秘书长
笔者根据实务办案中总结的经验得出,知识产权诉讼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商标诉讼为代表的维权阶段,权利人的权利因被抄袭等方式遭受严重侵犯,遂发起诉讼制止侵权,维护权利,诉讼主要发生在权利优势方和劣势方之间;第二阶段是以专利诉讼为代表的竞争阶段,知识产权诉讼成为商业运营的环节和工具,利用重大知识产权诉讼阻止对方上市或者谋求高额许可费,诉讼发生在实力相当的商业竞争对手之间;第三阶段是以商业秘密为代表的仇恨诉讼阶段。
美国商业秘密诉讼律师James Pooley曾在其文章中指出,“商业秘密诉讼是关系破裂后情绪驱动的纠纷。”[1]笔者认为此种说法较为形象地描述了商业秘密诉讼的特质:无论是员工离开后采用相同技术另立门户,还是核心团队出走至竞争对手带走商业秘密,在优势竞争资源丢失的同时,都伴随着深深的信任崩塌和关系破裂,案件中往往夹杂着情感伤害因素。这也是在商业秘密案件中,权利人会倾向于通过刑事程序解决纠纷的重要原因。当然,刑事案件的推进也与之前民事案件推进困难有一定关系。由此形成的现状是,绝大多数的商业秘密案件中,权利人在酝酿法律行动时均同时考虑刑事途径和民事途径,且大量案件在现实中存在刑民交叉。在此补充说明一点,张明楷教授在其文章《“刑民交叉”概念是个伪概念》[2]中指出,“‘刑民交叉’所表达的只是现象层面的刑民关系”,本文所涉“刑民交叉”亦属于上述层面。
一、商业秘密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比较
2019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以下简称“反法”)第九条规定了侵犯商业秘密的法律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2020年修正案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了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犯罪构成。刑法和反法的修订,统一了侵犯商业秘密的主体、客体和行为。但二者最为显著的区别首先体现在传统刑法理论对于犯罪主观方面的证明上,其次体现在对侵犯商业秘密的程度和后果要求上。根据反法的规定,只要有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存在,即便没有损失,也可提起诉讼要求停止侵权。而根据刑法的规定,侵犯商业秘密需要达到情节严重以上。
图1 刑民流程比较
商业秘密民事诉讼案件办理的流程为:当事人和律师配合一起调查取证,然后做诉讼方案分析,再向具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由法院进行审理。而商业秘密刑事案件的流程则是先去向公安报案,公安受理案件并立案侦查,侦查结束后移交检察院,经审查后决定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进行审理。直接提出的刑事自诉案件数量很少,在此不做具体讨论。
就办案环节来看,当事人首先要推动公安受理案件。在司法资源紧缺,大案要案多发的情况下,推动公安接受认可并受理可能涉及高端技术的商业秘密案件,对当事人来讲是很大的考验。另外,在刑事案件推动过程中,笔者也深深感受到排除合理怀疑证据原则与民事诉讼程序高度盖然性的巨大不同。例如在某公司推进的案件中,犯罪嫌疑人A在B公司工作期间接触并掌握了A公司的技术秘密,C公司知晓后利诱其携带技术秘密离职加盟C公司。后因条件未能谈妥,A窃取秘密离开B公司后独立成立公司,与C合作实施窃密技术。最初原告认为侵权行为已经得以充分证实,但公安机关基于审慎态度,依然希望能够找到A、C公司合谋共同侵权的直接证据,以达成客观确认,排除合理怀疑。
《反法》新增加的第32条规定,在证据表明存在高度窃密可能的情况下,将不构成商业秘密以及不构成侵权的证明责任转移到被告,很大程度地降低了民事案件办理的举证难度,减轻了 “秘密性”、“同一性”和“价值性”三大报告给原告带来的成本压力。同时第32条规定原告初步举证的重点在窃密嫌疑,而非密点成立,笔者认为这是符合商业秘密案件办理逻辑的,偷窃首先是不对的,不管偷走的是什么。如果偷窃行为得以证实,应由偷窃者证明偷走的是公知信息,以平衡个别人将公知信息据为己有,不当获利。
二、与刑民交叉相关的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二十三条和二十五条具体规定了民事程序和刑事程序之间的协同。
第二十二条规定了刑事诉讼程序中形成的证据调取和采信。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在民事诉讼程序中,如当事人申请法院调查搜集刑事诉讼程序中所形成的证据,在不影响刑事诉讼案件办理的情况下,法院可以准许并调取。
第二十三条规定了刑事诉讼案件判决中关于损害赔偿的效力。即,如果当事人主张刑事判决已经确认的违法所得或者违法获利作为民事诉讼案件中民事赔偿数额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条规定了在先刑事生效判决就损害赔偿金额的即判力。
第二十五条规定了刑事诉讼程序和民事诉讼程序同时推进时的协同,这里是典型的刑民交叉问题处理。“先刑后民”指在民事诉讼活动中,发现涉嫌刑事犯罪的,应当在侦查机关对涉嫌刑事犯罪的事实查清后,由法院先对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后就涉及的民事责任进行审理,或者由法院在审理刑事犯罪的同时,附带审理民事责任部分。[3]当针对同一侵权事实的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同时推进时,传统上有先刑后民的说法,然而在商业秘密领域,该条司法解释做出了明确的答复,法院审查后确定,并不必然先刑后民。
今年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也规定了刑民交叉的情况。
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如果发现跟本案有关联,但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案件,涉嫌犯罪的,应移送到公安机关或者是检察机关继续审理刑事案件。这是基于不同法律关系刑民相互分离并行的规定,当然这一规定并非指同一法律关系。
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这是将不属于经济纠纷的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公安或检察院,最终达成民消刑起的结果。
第十二条规定针对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并书面通知当事人,退还案件受理费;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是有关刑民程序选择的规定。
三、典型案例
图2 案例1诉讼过程
案例1:(2016)粤民终770号、(2018)粤刑申305号
本案的核心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中对于关联刑事案件判决或裁定认定的适用。法院在商业秘密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可以直接确认同一侵犯商业秘密事实的关联刑事生效裁判所认定的基本事实、侵权数量、经济损失、鉴定意见、质证意见等。
原告(被害人)系珠海欧比特控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比特公司),于2003年4月着手研发1553BIP核技术,用于航空航天设备的测试,该IP核由三个主要功能模块组成:总线控制器(BC)、远程终端(RT)、总线监视(BM)。被告房树磊作为原告的原技术负责人,负责研发此技术。2005年10月,被告房树磊在1553BIP核BM模块尚未完成情况下(BC、RT等模块已研发完成)提出辞职申请,离职获批准后遂转到其妻子付永利为法定代表人的珠海矽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矽微公司)工作。自2009年开始,被告房树磊违反约定,披露、使用、允许矽微公司使用其掌握的欧比特公司1553BIP核技术。矽微公司先后生产销售系列1553B测试仪17个,销售金额达800多万元,其中,在2010年至2012年期间,生产销售相关产品11个,给原告欧比特公司造成250余万元经济损失。
本案于2012年11月16日由广东省珠海市公安局立案,并指定高新区公安分局侦查。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7月12日对房树磊以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批准逮捕,并于2014年3月12日提起公诉。同年11月6日,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矽微公司罚金二百五十万元;判处被告人房树磊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二十万元。2015年6月15日,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后房树磊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25日裁定驳回申诉。
在关联民事案件中,原告欧比特公司于2013年8月起诉至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作出(2013)珠中法知民初字第848号民事判决,判决房树磊等赔偿原告人民币约548万元。后房树磊于2016年8月上诉至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4)珠香法刑初字第647号刑事判决和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珠中法知刑终字第5号刑事裁定认定的司法鉴定意见、侵权数量、经济损失等,于2016年12月26日作出(2016)粤民终770号民事判决,基本维持一审判决。
该案是刑民同时推进的典型案例,刑事诉讼程序推进过程中,原告又向珠海中院提起了民事诉讼,民事程序中止,直到珠海中院作出刑事判决,民事程序才继续推进。珠海中院在之后的民事程序中,直接采信了生效刑事判决以及裁定中确认的事实,包括侵权数量、经济损失,以及鉴定意见的质证意见。
图3 案例2诉讼过程
案例2:(2019)最高法知民终333号
本案的核心是商业秘密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原则。法院认为因违反保密义务引发的商业秘密许可合同纠纷案件,与关联侵犯商业秘密刑事案件并非基于同一法律要件事实所产生的法律关系,人民法院可以在移送犯罪嫌疑线索的同时,继续审理该商业秘密许可合同纠纷案件。
原告浙江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系上市公司,被告宁波必沃纺织机械有限公司部分员工曾系原告离职员工,2016年3月,双方曾签署《采购协议》和附件《保密协议》,由原告委托被告加工部分零部件。2018年11月,原告发现被告生产的电脑针织横机的部分部件与其委托加工的部件外观和技术要求相同,认为被告违反协议中“依据原告提供的技术图纸只能为原告生产加工横机设备零部件”的约定,遂以“技术秘密许可使用合同纠纷”为由诉至法院,法院2018年12月予以立案。2019年5月,原告又以“侵犯商业秘密罪”为由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经审查予以立案。之后,当地公安机关致函宁波中院并要求调卷。[4]
针对当地公安机关的函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以及第十二条“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相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并书面通知当事人,退还案件受理费;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宁波中院作出裁定称,由于公安机关审查的事实涵盖了两公司签订的《采购协议》《保密协议》及相关图纸的内容,与法院审理的法律事实有重合之处,被告公司具有侵犯商业秘密罪嫌疑,故裁定移送公安机关处理。[5]
原告2019年8月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本案原告以被告将其“被许可的技术秘密”用于合同约定事项之外为由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可见原告以违反合同约定为由提起的合同之诉,系技术秘密许可合同法律关系,而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涉嫌商业秘密犯罪,系商业秘密侵权法律关系,二者所涉法律关系不同,并非基于同一法律事实所产生之法律关系,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涉嫌经济犯罪,仅案件所涉事实具有重合之处。原审法院应将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机关,但也应继续审理本案所涉技术秘密许可合同纠纷。据此,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撤销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裁定,本案由宁波中院继续审理。
四、商业秘密保护取决于企业管理水平
商业秘密相关权利具有一定特殊性。笔者认为,其最为特殊之处在于是否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权利取决于权利人的内部管理,权利保护的强度反映了企业商业秘密管理强度,甚至某些商业秘密的具体归属均取决于企业管理制度的博弈,管理水平越高,商业秘密越多。
事实上,管理较为规范严密的企业,会明确规定员工从研发立项到推进、从完成到验收各个环节中所涉技术记录、技术沟通、资料浏览、信息传送的权限。一旦有技术秘密泄露,可以简单快速地追查到每一位接触者,能够做到及时确认情况,快速处理防范。相比而言,很多企业在这方面还有待完善。因此笔者认为,保护商业秘密应从企业内部管理做起。
注释:
[1] James Pooley:《How Mediation Can Help Both Sides Win a Trade Secret Case》,IPWatchdog,March 29, 2021.
[2] 张明楷:《“刑民交叉”概念是个伪概念》,法商研究,2021年第1期。
[3] 陈训达:《“先刑后民”原则如何正当适用》,中国法院网福州频道,2010年9月25日。
[4] 参见:《宁波市公安局关于立案侦查“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被侵犯商业秘密案”的函》,甬公函[2019]31号。
[5] 参见:(2018)浙02民初2329号民事裁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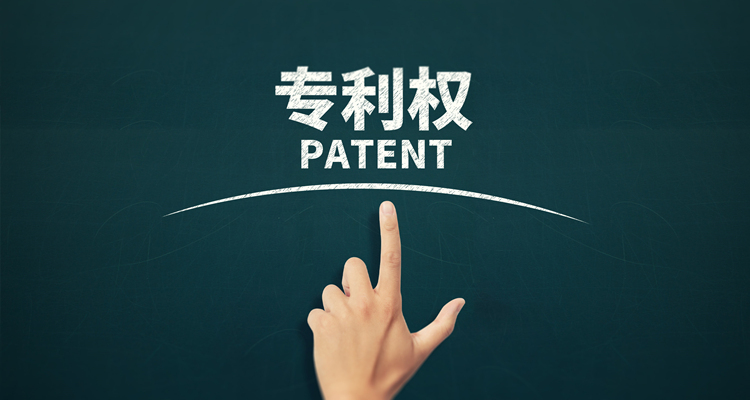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9464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946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