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陈锦川 全国审判业务专家。曾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长期从事著作权审判工作,代表作有:专著《著作权审判:原理解读与实务指导》等。
根据《商标法》第32条的规定,申请商标注册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该规定中的在先权利包括著作权、外观设计专利权、姓名权、肖像权等,从实践中看,因申请注册商标损害他人在先权利的案件中,涉及著作权的占了大部分。涉及的著作权问题,较为常见的是主张著作权的客体是否构成作品、著作权人、利害关系人的证明、诉争商标是否与作品相似以及著作权的保护期等问题,本文拟聚焦于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中有关著作权的保护期问题。
对于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中著作权的保护期的确定,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和司法机关的观点基本一致。
在原告上海万丰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万丰公司”)与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三人奇异有限公司(下称“奇异公司”)案中,奇异公司称,被异议商标的申请注册侵害其在先著作权。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下称“北京高院”)认为:奇异公司“蜘蛛侠”系列漫画的首次发表时间为1962年,……。对“蜘蛛侠”头部图形的著作权保护期限自1962年版“蜘蛛侠”头部图形发表之日起计算,已经超过著作权保护期,本案中的诉争商标标志系万丰公司在进入公有领域的“蜘蛛侠”头部图形基础上另行创作的作品,并未侵害奇异公司已经超过著作权保护期限的“蜘蛛侠”头部图形作品的著作权。[1]该院的《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审理指南(2019年修订)》16.6系关于【超过保护期限的作品】的规定,该规定指出:诉争商标申请注册时,当事人以超过著作权法规定保护期限的作品主张著作权的,不予支持。可见,北京高院的观点是明确的,即超过著作权法规定保护期限的作品不能再主张著作权。
最高人民法院(下称“最高法院”)亦指出,超过保护期的作品不再享有著作权。在“雄狮标识”商标异议复审行政纠纷一案中,米高梅公司称埃索公司恶意抄袭、模仿其商标并侵犯其在先著作权。米高梅公司自1924年起将雄狮图形作为公司的标识进行使用。其在本案主张在先著作权的作品系1987年1月1日在其前身使用的公司徽志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雄狮标识美术作品。埃索公司则称,米高梅公司的雄狮标识已超过了著作权法规定的50年保护期限,不应再给予著作权法的保护。
最高法院认为,米高梅公司1987年“雄狮标识”作品与其自1924年起使用的雄狮图形的设计手法、整体视觉更为近似,而与被异议商标的差异较大。在判决书中,最高法院虽然没有明确说明米高梅公司雄狮标识是否已超过著作权保护期因而不应保护,但其引用了《著作权法》第21条第3款关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作品、本法第10条第1款第(5)项至第(17)项规定的权利的保护期为50年的规定,并最终支持了埃索公司的主张。[2]
商标行政管理机关也保持了与司法机关相同的观点。2021年11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新一版《商标审查审理指南》下篇第四章3.2.2指出,认定申请商标侵害他人在先著作权的适用要件之一是:在系争商标申请注册之前他人已在先享有著作权,且在著作权在保护期限内。
问题在于,所有著作权权利都有保护期限吗?仅提“超过著作权法规定保护期限的作品都不再享有著作权”是否全面和准确?怎样的说法才更为符合法律的规定?本文拟就上述问题谈谈个人的一点看法。
一、对著作权保护期含义的准确理解
著作权包括财产权和人身权。在著作权内容的立法上,一般来说,英美法系国家认为著作权仅为财产权,大陆法系国家认为著作权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在大陆法系看来,作品除了有经济价值外,同时也是作者人格的延伸和精神的反映,作品体现了作者的思想、情感,因而是精神和人格的产物。按照大陆法系著作权理论,著作权法保护的首先是作者的著作人身权,其次才是作者的著作财产权。[3]我国采用大陆法系的做法,《著作权法》第10条规定,著作权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因此,虽然人身权与财产权密切相关,但是又互相独立。人身权与财产权一样都应该得到尊重,侵害人身权同样也是侵害著作权,在某种意义上,割裂作品与作者的联系、歪曲篡改作品,对作者造成的伤害,比侵害财产权造成的损害后果更为严重。
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的著作权法对著作财产权和人身权确定了不同的保护期。对于著作财产权,为了平衡作者与使用者及公共利益的关系,通常都给予一定的期限限制。而由于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这几项权利与作者本人的品德、才智、声誉、荣誉直接相关,并且涉及作品的归属,以及作品是否真实地反映了作者的创作原意等。因此,对作者的这几项权利的保护,不仅仅体现在作者生前,也有必要给予永久保护。”[4]我国著作权法对著作人身权、著作财产权的保护期的规定即体现了这种思想。《著作权法》第22条规定,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保护期不受限制。第23条对著作权人享有的发表权、财产权的保护规定了期限限制,并且根据不同的著作权主体和作品的不同种类作了不同的规定。
据此,虽然我国《著作权法》第2章第3节”权利的保护期“的规定涵盖了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但只有发表权、著作财产权有保护期的限制,而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事实上并没有保护期,他们是永久性的权利,永久受到保护,因而不存在超过保护期的问题,因此,简单地说“超过著作权法规定的保护期限的作品,不应再给予著作权法的保护”并不能反映著作权不同性质权利的保护期问题。
二、未经许可将他人作品申请注册为商标既可能侵害著作财产权,也可能侵害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等著作人身权
未经许可将他人作品申请注册为商标并投入市场使用,通常会侵害他人对该作品的复制权、发行权等著作财产权,但亦存在着侵害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等著作人身权的可能。
有观点认为,未经许可将他人作品作为商标使用不会侵害署名权,因为商标上无法给作者署名。而根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19条“使用他人作品的,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由于作品使用方式的特性无法指明的除外”的规定,法律允许无法指明作者姓名的可以不给作者署名,并且不构成侵害署名权。笔者以为,对此规定应作全面分析。署名权,即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仅从字面看,署名权仅是关于署名的权利,但署名权除了是署名的权利外,它同时也包含了身份权,在著作权法的语境下,署名权要赋予作者的是通过署名来昭示作者身份,以保障作品与作者之间的联系;行使署名权的实质是要求他人承认作者的身份。
因此,“署名权是作者身份的一种表现方式,但不是全部。因为作者身份权的实现还可通过对作者的身份介绍、真名登记等署名以外的方式来实现。”[5]故不能在商标上署名,并不意味着以不存在可以表明作者身份的其他方式,就可以不通过其他方式来体现作者的身份。当商标持有人可以署名之外的方式来实现作者的身份权时,商标持有人怠于行使表明所使用作品作者身份的义务的,有可能侵害作者的署名权。因此,未经许可将他人作品作为商标使用是否会侵害署名权,并非没有讨论的空间。
理论和实务界对修改权存在较大的争议。但其中一种比较有影响的观点认为,修改权控制的是对作品的各种修改行为,只要对作品进行了修改,而这种修改没有达到实质程度的变化,没有对原作进行歪曲、篡改,就属于修改权的规制行为。在“天下粮仓”案中,“天下粮仓”四个字之间散落着很多墨迹,代表血泪和粮食。被告在图书封面上使用该书法作品时去掉了墨迹。法院认为,被告对作品的这种改动,侵犯了作者享有的修改权。[6]在将他人作品设计为商标时,这种改动极有可能发生,因而存在着落入修改权范围的可能。
保护作品完整权即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对他人作品进行改动达到歪曲、篡改的程度的,是侵害保护作品完整权的行为。在“《汤加丽写真》”案中,被告对原告的39幅摄影作品的部分人体、背景或道具进行了裁剪,法院认为,上述行为“损害了原告对其作品的构思和艺术追求,破坏了上述作品的构图和视觉效果,侵犯了原告对其作品的保护作品完整权。”[7]将作品当做商标时,当然不排除这种情形的出现。商品或服务的类别涉及各个方面,将某一作品用在某类商品或服务上,有可能会违背作品欲表达的本义,从而出现歪曲篡改的效果。在摄影作品“《跳帮》”案中,法院认为,被告“在明知作品的主题反映的是海关人员的英勇无畏精神的情况下,为达到自己使用的目的,却在刊物封面上配印与作品主题相反的图案和文字,突出了海关腐败的内容,这种使用严重歪曲、篡改了原告的创作本意,……,侵犯了原告的保护作品完整权。”[8]
可见,将他人作品申请注册为商标并使用,并不能完全排除侵害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等著作人身权的可能。
我国著作权法以罗列著作权具体权项的方式界定著作权的权利内容和范围,共规定了十七项著作人身权和财产权,它们相互独立,但共同组成了著作权人对其作品的专有权利。审理侵害著作权民事案件的基本逻辑是:原告首先明确其主张的具体权利,法院在此基础上展开审理,判定原告是否享有该权利、被告实施的行为是否落入该权利范围并作出判决。但上述案例中,当事人都只是笼统提出诉争商标侵害了其著作权,并没有明确其著作权是哪项权利,是著作人身权还是财产权;法院也没有要求当事人明确其主张的是什么权利,而是直接把当事人主张的权利当做著作财产权,从而适用了著作权法有关著作财产权保护期的规定认定当事人的作品超过了著作权保护期,违反了审理著作权侵权案件的基本逻辑和要求。
个案中著作权的保护期取决于当事人主张的是人身权还是财产权。不能笼统地说超过著作权保护期的作品不能再主张著作权。为此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1、从当事人的角度,当事人主张诉争商标侵害其著作权的,应当在请求书或者起诉请求中明确其主张的具体权利,是人身权中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还是发表权、著作财产权。
从法院的角度,要区分当事人主张的是著作人身权还是著作财产权,并在此基础上确定是否以及如何适用保护期的规定。如果是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则无保护期的限制;如果是发表权、著作财产权,则需要依据事实和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确定作品是否已超过著作权保护期。
2、《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审理指南(2019年修订)》16.6、《商标审查审理指南》下篇第四章3.2.2应对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和发表权、著作财产权作出区别并分别作出规定,而不是仅仅将保护期局限于著作财产权的保护期。比如,《商标审查审理指南》下篇第四章3.2.2可修改为“认定申请商标侵害他人在先著作权的适用要件之一是:在系争商标申请注册之前他人已在先享有著作权中的发表权、著作财产权,且在著作权在保护期限内;或在系争商标申请注册之前他人对其作品已在先享有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
三、确定视听作品中可单独使用作品的著作财产权保护期应注意的问题
《著作权法》第23条区分著作权主体(自然人与法人、非法人组织)、针对合作作品、视听作品等情况分别规定了作品发表权、财产权的保护期。从商标审查实践看,当事人以视听作品中的美术作品主张著作权的占有一定比例,比如上述“雄狮标识”案。那么,当事人以视听作品中的美术作品主张著作权时,能否因当事人是视听作品的著作权人就理所当然认为其就是该美术作品的著作权人呢?是否就按照著作权法关于视听作品著作权保护期的规定确定保护期吗?对此,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
1、视听作品与包含其中的美术作品是各自独立的作品,分别产生著作权。作品的独创性体现在作品的表达中,并以该独创性表达确定作品的著作权范围,因此,不同类型作品以不同表达来划分。视听作品的本质特征在于一系列加伴音或者无伴音的滚动的画面,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指出,电影作品是指“由一系列有伴音或者无伴音的画面组成”的作品。因此,视听作品作为综合性艺术作品,虽然也包含有小说、剧本、美术、音乐、摄影等内容,但仅以连续画面为其表达,其独创性亦体现在连续画面中,而不是体现在文字、旋律和节奏、线条和色彩之中。视听作品与其中的剧本、美术、音乐、摄影等可单独使用的作品是不同性质、不同类型作品,应区别开来。
我国《著作权法》第17条第1款规定,视听作品中的电影作品、电视剧作品的著作权由制作者享有;第2款又规定,视听作品中的剧本、音乐等可以单独使用的作品的作者有权单独行使其著作权。据此,视听作品的著作权由制作者享有,但其中的剧本、美术、音乐、摄影等可以单独使用的作品的著作权并不属于制作者,而是属于剧本、美术、音乐、摄影等作品相应的作者。在“大头儿子案”中,法院认定:动画片的人物造型本身属于美术作品,其作者有权对自己创作的部分单独行使著作权。[9]在“奥特曼美术形象案”中,法院认定,迪迦奥特曼角色形象构成独立于影视作品、可以单独使用的作品。不能简单地或当然地推定这个单独作品的著作权由影视作品的著作权人享有。影视作品的著作权人应举证证明其享有奥特曼美术作品的著作权。[10]
2、视听作品与视听作品中美术作品的发表权、著作财产权的保护期应分别确定。对视听作品,依据《著作权法》第23条第3款确定保护期,即:视听作品,其发表权的保护期为50年,截止于作品创作完成后第50年的12月31日;著作财产权的保护期为50年,截止于作品首次发表后第50年的12月31日,但作品创作完成后50年内未发表的,不再保护。对于视听作品中的美术作品,则要区分是自然人作品还是法人、非法人作品,以及是否合作作品,分别适用《著作权法》第23条第1、2款确定保护期。
“孙悟空”美术作品形象案是其中的典型案例。在本案中,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有限公司(下称“美影厂”)以电影作品《大闹天宫》中的“孙悟空”美术作品形象主张著作权。美影厂称,“孙悟空”美术作品最早发表于1978年,且该作品属合作作品,作者为美影厂、张光宇和张正宇,根据作品的发表时间和张正宇的死亡时间,“孙悟空”美术作品的著作财产权仍在著作权法规定的保护期内。法院认为,没有证据证明张正宇是“孙悟空”美术作品的合作作者之一,不能按张正宇的死亡时间计算“孙悟空”美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期。法院认定,美影厂是“孙悟空”美术作品的作者或作者之一。
对此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规定:“著作权法(2010年著作权法,笔者注)第15条第2款所指的作品,著作权人是自然人的,其保护期适用著作权法第21条第1款的规定;著作权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其保护期适用著作权法第21条第2款的规定。”《大闹天宫》上集的发表时间不迟于1962年。“孙悟空”美术作品作为电影作品《大闹天宫》里的一部分,也随之公之于众,根据《著作权法》第21条第2款,“孙悟空”美术作品的复制权、发行权等著作财产权保护期最迟于2012年12月31日止。本案被控侵权行为发生在2016年2月,因此,“孙悟空”美术作品的著作财产权已经超过了著作权法规定的保护期。
关于张光宇作为合作作者对著作财产权可能的影响,法院认为,张光宇的死亡时间为1965年5月4日,第50年后的12月31日即为2015年12月31日。因此,即使张光宇是“孙悟空”美术作品的合作作者之一,该作品的著作财产权也已经超过了依据张光宇死亡时间计算的著作权法规定的保护期。综上,无论是依据“孙悟空”美术作品的发表时间,还是依据张光宇的死亡时间,“孙悟空”美术作品的著作财产权均已超过了著作权法规定的保护期,被告的行为不构成侵害著作权。[11]本案法院对视听作品中可单独使用的美术作品属于法人作品、合作作品的情况下如何确定发表权、著作财产权的保护期,依据法律作出了正确判决,对类似案件具有借鉴意义。
注释:
1.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京行终599号行政判决书。
2.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再11号行政判决书。
3.王迁著,《知识产权法教程(第七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8月第7版第147页。
4.黄薇、王雷鸣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导读与释义》,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1年3月第1版第135页。
5.吴汉东等著,《知识产权基本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第1版第251页。
6.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3)二中民终字第10610号民事判决书。
7.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3)高民终字第1006号民事判决书。
8.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3)高民终字第1006号民事判决书。
9.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4)三中民初字第7916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杭知终字第357号民事判决书。
10.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鄂民三终字第23号民事判决书。
11.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01民初2010号民事判决书、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鄂民终71号民事判决书。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知产财经立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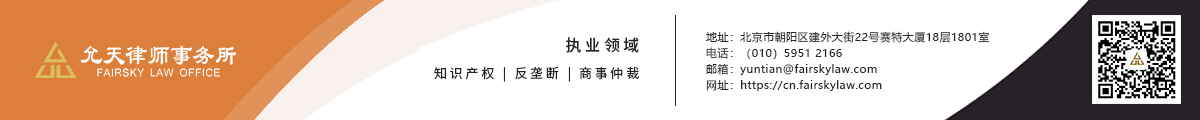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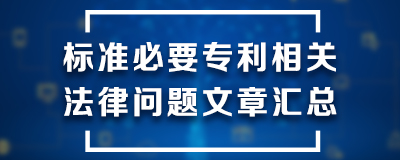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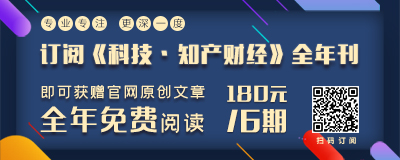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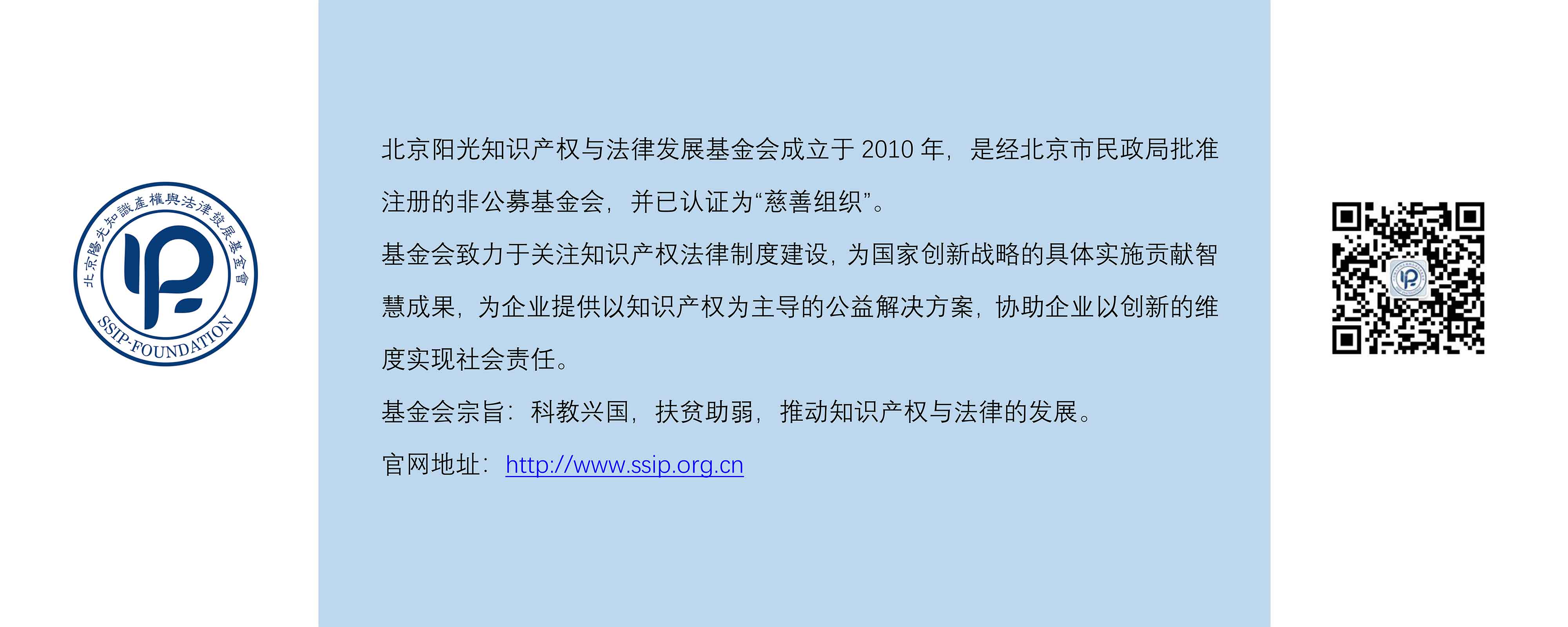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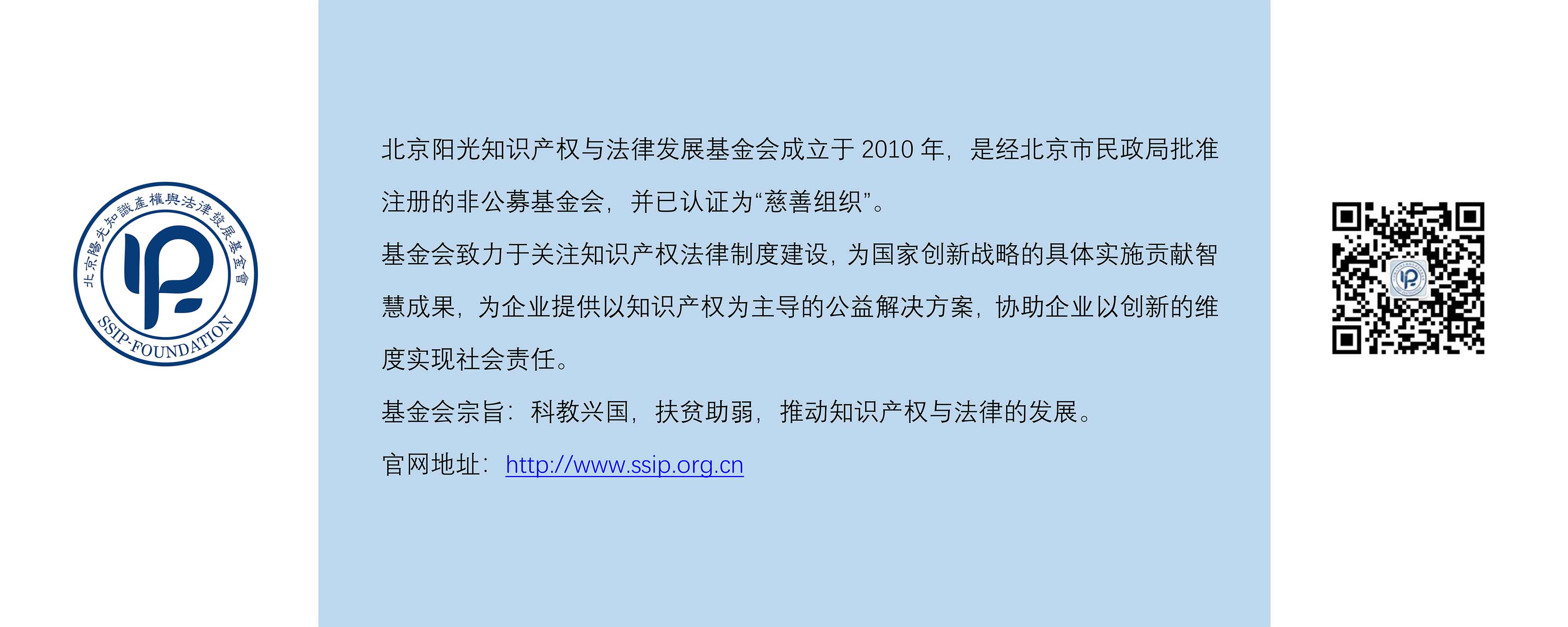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9464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946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