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健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原资深法官,全国审判业务专家,厦门大学业界名家
一、问题的提出
驰名商标(well-known trademark)是指为相关公众所熟知的商标,[1]体现出经长期经营的商标所累积的较高市场知名度与声誉。但2013年商标法第三次修正增加规定“不得宣传条款”,即第14条第5款:“生产、经营者不得将‘驰名商标’字样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上,或者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这显然是为了纠正之前相当时期内存在的驰名商标“异化”现象。
而实践中,早在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简称“最高法院”)在相关司法解释中就已经确立严格“按需认定”的原则。[2]在此之后,司法认定驰名商标的标准堪称严格甚至严苛。根据最近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发表的报告,通过对2016-2020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等法院审理的146件驰名商标民事侵权案件进行实证研究,其中针对“关于目前司法实践对驰名商标认定标准的高低”的问卷调查,律师群体和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人员中认为认定标准“过高”和“比较高”的比例分别为60.27%和 61.66%;而从法院裁决结果看,认为有必要进行驰名商标认定的占比为36.99%,而认为没有必要进行驰名商标认定的占比为63.01%。[3] 以上数据表明,法院最终支持权利人诉请认定驰名商标的比例尚不足四成,反映出司法实践中对于驰名商标认定标准的严格把控,对此学界也有相关的反思与探讨。[4]
对于是否应该认定驰名商标,有时在个案中也明显可见司法的某种“困惑”,即究竟是认还是不认?不过近期的变化是,认定商标驰名的案件有所增加。最近,商标法第五次修正已经启动,其中涉及驰名商标条款的修订。本文旨在通过回顾我国驰名商标制度的历史沿革,梳理司法严格“按需认定”驰名商标的实践现状,反思我国驰名商标制度存在的问题,以期推动司法认定驰名商标回归事实认定的理性,并为构建更为合理的驰名商标制度,即统一驰名商标同类保护和跨类保护的标准提出相应的修法建议。
二、我国驰名商标制度的历史沿革
追溯我国驰名商标制度的发展历史,有助于深刻理解驰名商标制度及其实践在我国的历史走向。
我国1982年颁布商标法时并未规定驰名商标制度,驰名商标保护的实践始于1985年我国加入《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简称《巴黎公约》)。因涉及“如何按照公约的要求保护驰名商标的问题”,国家工商总局采取了积极保护驰名商标的态度。1987年8月,国家商标局在商标异议程序中认定美国必胜客国际有限公司“PIZZA HUT ”商标及屋顶图形商标为驰名商标,这是中国加入《巴黎公约》后认定的第一件驰名商标。1996年8月,原国家工商管理局发布《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明确国家商标局负责驰名商标的认定与管理工作。2003年4月,国家工商总局发布《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进一步明确国家商标局和商标评审委员会可以在商标异议、注册商标撤销和商标管理过程中认定驰名商标。
同期,人民法院在个案中开始对驰名商标作出认定,尽管对此曾存在争议,但鉴于这是国际通行做法,“我国学术界也取得了人民法院有权在个案中认定驰名商标的一致性意见”。[5]在2001-2002年期间,最高法院先后发布关于网络域名纠纷案件、商标民事纠纷案件相关司法解释,[6]初步确立了驰名商标个案认定、被动认定和按需认定的司法认定原则。但此时,“按需认定”原则的具体内容并不明确,只是提出“原告未提出主张的,或者根据案情无需对商标是否驰名予以认定的,人民法院不予认定。”[7]
为了满足中国加入WTO的要求,2001年商标法第二次修正从立法上正式引入驰名商标制度。其中,第13条区分驰名商标是否在中国注册,分别给予不同范围的保护:(1)就相同或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制、募仿或者翻译他人未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2)就不相同或不相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制、募仿或者翻译他人已经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误导公众,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权利可能受到损害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上述规定,意味着未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可以获得同类保护,已注册驰名商标可以获得跨类保护。
但是,自我国2001年商标法正式确立驰名商标制度后,以行政认定为主导的驰名商标认定逐渐偏离了初衷,一是由政府主导的驰名商标认定演变成“政绩”工程,使得驰名商标保护非正常地承载了其他意义;[8]二是驰名商标认定开始超越个案保护的意义,而主要被应用于企业的广告宣传。此外,驰名商标司法认定中也出现为获得认定而虚假诉讼的情形。上述种种异化现象,使得驰名商标认定制度遭到社会的普遍质疑和诟病。[9]
出于规范驰名商标司法认定工作的考虑,最高法院于2009年发布了《关于审理涉及驰名商标保护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为《驰名商标司法解释》)。在该司法解释中,首先是明确商标是否驰名属于事实认定;其次是明确驰名商标“按需认定”即认定驰名商标“必要性”的具体适用条件,概言之,一是驰名商标司法认定实行“双跨类”机制,即跨类别保护与跨字号保护;二是商标是否驰名实行“双不审查”限制 ,即同类保护不审查与商标不近似不审查等。[10]至此,最高法院通过司法解释确立了驰名商标严格“按需认定”原则,且在个案中对于认定商标驰名的需要专门阐述认定“必要性”的裁判理由,而之后2013年商标法修正则进一步增加“不得宣传条款”。
综上,我国驰名商标制度历经加入国际公约——驰名商标认定实践先行——2001年商标法修正立法规定驰名商标制度——驰名商标认定出现异化现象——2009年司法解释确立严格“按需认定”标准——2013年商标法修正增加“不得宣传条款”等发展过程,此为我国驰名商标制度及其实践现状的历史背景。
三、我国驰名商标司法实践现状梳理
客观而言,驰名商标适用严格“按需认定”原则,对于矫正特定时期驰名商标异化现象具有积极作用,但也难免“矫枉过正”。原因是,尽管同时期最高法院的司法政策强调:“对于确实符合法律要求的驰名商标,要加大保护力度,坚决制止贬损或者淡化驰名商标的侵权行为,依法维护驰名商标的品牌价值”,但同时亦强调:“严格把握驰名商标的认定范围和认定条件。凡商标是否驰名不是认定被诉侵权行为要件的情形,均不应认定商标是否驰名;凡能够在认定类似商品的范围内给予保护的注册商标,均无需认定驰名商标。”[11]这导致在司法实践中驰名商标认定的范围被大幅度压缩。
首先,就跨类保护而言,法院在个案中通过尽量扩张类似商品/服务的认定,以减少跨类认驰的需求。关于类似商品/服务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为《商标民事司法解释》)规定了宽泛且弹性的标准。可简要概括为:判断类似商品/服务采取混淆标准,以相关公众的一般认识进行综合判断,《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表》《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可以作为参考。[12]
以“安踏眼镜案”[13]为例。该案中,原告的“安踏”商标核定使用在第25类服装、游泳衣、运动鞋上,且国家商标局早在2002年3月22日就已认定原告运动鞋商品上的“安踏”商标为驰名商标,而被诉侵权商品是眼镜及眼镜框。在该案中,法院认为,两者的消费群体均为一般社会公众,消费对象具有重合性,均可用于穿戴、具有一定防护功能,功能、用途相近,故两者构成商标法第57条规定的类似商品,且两者商标构成近似,判定构成侵权,赔偿损失及合理支出15万元。实践中,此类案件及其相应的裁判说理很常见,举不胜举。
如果说,以消费群体具有重合性以及功能和用途相近为由回避跨类认驰,尚可接受,那么在另一些案件中刻意回避跨类保护,则反映出严格认定政策的深刻影响。以“和睦佳宠物医院案” 为例。[14]该案中,原告的“和睦家”注册商标广泛用于医疗服务,且已有五份商标无效宣告请求裁定书中认定“和睦家”注册商标经过长期宣传,在“医院;保健;疗养院”服务上已为相关公众所熟知。被告在其开设的“宠物医院”使用“和睦佳宠物医院”等标识,其攀附的故意明显。法院认为,一方面,“和睦家”注册商标核定服务的类别中包含了“兽医辅助”,被告未经许可在相同类别之上使用近似标识,容易导致消费者对服务来源或者服务提供主体关联性产生混淆或者误认,依法构成侵权;另一方面,“和睦家”作为高端医疗以及个性化医疗的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而被诉侵权标识使用领域为宠物医院,在医院与宠物医院均属医学领域,两者行业属性存在一定关联的情况下,被诉标识的使用容易使消费者对两者服务主体是否存在特定关系产生不当联想,也会一定程度破坏“和睦家”作为高端医疗品牌的市场定位,并且对其商标声誉亦会产生相应的影响。最终法院同时适用2013年《商标法》第57条第(2)项近似条款和第(7)项“其他损害”条款,认定构成商标侵权。从裁判理由看,人类医疗服务显著区别于兽医服务,本案具有跨类认驰的事实基础,但最终法院没有选择跨类保护,显然是碍于权利人同时在“兽医辅助”类别上也注册有“和睦家”商标。由此带来的思考是,当权利人在不同类别上均有注册商标时,究竟应当如何保护驰名商标?换言之,在多个类别的注册商标中,被告攀附的究竟是权利人的驰名商标还是同类别注册商标?这其实是驰名商标保护中长期未能完全达成共识的问题。
其次,就同类认驰而言,在司法解释的严格限制下,驰名商标同类保护仅作为普通商标侵权案件进行审理。由于普通商标侵权判定适用混淆要件,然而混淆的判定本身具有一定的主观性,这既增加了驰名商标保护的某种不确定性,也使得驰名商标同类保护的力度事实上弱于跨类保护。
在此,“河底捞案”无疑具有重要的样本意义。 [15]该案中,法院查明,海底捞公司成立于2001年4月16日。2011年5月27日,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认定海底捞公司使用在第43类餐馆服务上的“海底捞”注册商标为驰名商标。被告河底捞餐馆正门上方宣传招牌为“河底捞家常菜”,正门右侧宣传招牌为“河底捞,吃洞庭河鲜就到河底捞”,正门处的木制招牌以及被告店内的餐具、宣传标语、代金券、宣传单、名片均标注“河底捞好味道”字样。由于“海底捞”与“河底捞”同属餐饮类服务,属于对商标是否驰名不予审查的情形,故作为普通商标侵权案件,一二审法院重点审理“是否容易导致混淆”,但两审的裁判结论迥异。一审认为:“无论从字体的字形、读音、构图、颜色,还是从原告、被告经营的菜品等方面,均不会使一般的消费者对河底捞的餐饮服务的来源产生误认或者认为其来源与原告注册商标‘海底捞’之间有特定的联系,故被告河底捞餐馆不构成对原告海底捞公司的注册商标‘海底捞’的商标权的侵犯”,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而二审则认为:“考虑到两枚商标在市场知名度上的悬殊差别,如以相关公众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进行隔离比对,有可能导致公众对服务来源及其关联性产生混淆误认”。最终二审改判认定构成侵权并判决赔偿损失。
从结果上看,二审改判支持“海底捞”公司的诉讼请求,体现了司法保护驰名商标的价值导向。不过,分析该案一、二审裁判理由,仍可见驰名商标同类保护适用混淆要件存在的现实困境,即我国商标法并未给予同类认驰充足的制度供给,对此笔者将在后文中作进一步探讨。此外,还值得关注的是,海底捞公司一审败诉后在短时间内连续申请包括“淮底捞”“池底捞”“渠底捞”“清底捞”“海底淘”“海底捡”“海底煎”“海底挑”等在内的263件商标,[16] 这种“报复性”大量注册申请防御性商标的行为,也会反向推助我国注册商标申请量巨大泡沫的膨胀。[17]
不过,近年来也偶见个别突破同类认驰限制的案例。例如,在“佳联迪尔案”[18]中,法院认为,被诉侵权商标“佳联迪尔”核准使用在第4类工业用油等商品上,与原告“约翰·迪尔”等注册商标所核准使用的第7类农业机械等商品以及第12类拖拉机等商品构成类似商品。原告的上述商标在农业机械、拖拉机等商品上进行了大量的宣传推广且销售数量大,具有较高的市场声誉,在被告的“佳联迪尔”商标申请注册之前已经达到驰名程度,故认定被诉“佳联迪尔”商标的显著识别部分“迪尔”,构成对驰名商标显著识别部分“DEERE”及“迪尔”的翻译和复制。但仔细分析下来,本案并非典型的同类认驰,而是在扩大类似商品认定范围基础上采取的同类认驰,这与前述“安踏眼镜案”依普通侵权案件审理的思路并不相同。但如果本案适用跨类认驰,其裁判结果和保护效果也并无差异。
总结来看,本节四个案例中,前三个案例从结果上看即便不认定商标驰名,最终也不会影响涉案商标权获得司法保护。但驰名商标认定不仅涉及到商标侵权判定以及侵害驰名商标判赔额应当更高等个案问题,还涉及到作为驰名商标受保护的记录,可以有效阻却对“复制、募仿或者翻译”他人驰名商标的恶意申请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等,更涉及到驰名商标司法保护的整体价值导向以及同类与跨类保护裁判尺度统一等更深层次的问题。
以笔者主审的“阿里斯顿商标侵权案”[19]为例。马奇公司于1997年8月19日在第11类热水器产品上获准注册“阿里斯顿”商标,自2004年起“阿里斯顿”牌燃气热水器在全国各地市场占有率稳居前十。在该案中,马奇公司坚持主张司法认定驰名商标的必要性,理由之一是即便其当时已在多个类别上累积申请注册了80多件“阿里斯顿”商标,但仍无法阻却竞争对手的恶意注册,且在多件行政案件中,相关行政和司法机关均认为商标权人在与被诉产品相同类别上注册有相同商标,不具备认定驰名商标的必要性。对此二审判决认为,权利人可能在不同类别上有多个注册商标,知名度不同,但被告攀附的显然是权利人最具知名度的商标,而认定马奇公司第11类热水器产品上的“阿里斯顿”商标为驰名商标,给予该驰名商标与其长期累积的品牌商誉程度相当的保护力度,既符合本案基本事实,也体现了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裁判导向。[20]
四、我国驰名商标制度问题分析
基于我国驰名商标司法实践的现状,有必要对我国驰名商标制度本身以及所依据的法理基础进行深入探讨。
(一)关于商标混淆。所谓商标混淆,是指相关公众对商品/服务的来源发生混淆和误认,包括实际混淆与混淆可能性。普通商标侵权判定适用混淆标准。我国1982年商标法、2001年商标法修正均未规定混淆要件,而是简单规定未经商标注册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的”,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
但实践中商标侵权的情形要复杂得多,为了明晰商标侵权的判断标准,2002年《商标民事司法解释》第9条开始区分相同商标侵权和近似商标侵权。[21]所谓相同商标侵权,是指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当发生相同商标侵权时,通常直接推定商标混淆;所谓近似商标侵权,则是指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或者在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而对于混淆要件的认定,第9条采用“混淆性近似”的判断标准,简言之,只有发生商标混淆才构成商标近似,进而构成商标侵权;反之,不混淆则不近似,不近似则不侵权。此外,该司法解释还将传统的“来源混淆”扩张到“特定联系混淆”,即“易使相关公众对商品的来源产生误认或者认为其来源与原告注册商标的商品有特定的联系”。对此,2009年《驰名商标司法解释》第9条[22]则进一步明确:“特定联系混淆”是指“足以使相关公众认为使用驰名商标和被诉商标的经营者之间具有许可使用、关联企业关系等特定联系。”
2013年《商标法》修正第57条[23]在吸收司法解释区分相同商标侵权和近似商标侵权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将商标近似侵权的判定标准由“混淆性近似”修正为“构成要素近似+容易导致混淆”,简言之,商标构成要素近似且容易导致混淆的,才构成商标侵权;反之,商标构成要素近似但不容易导致混淆的,则不构成商标侵权。
例如在前述“河底捞案”中,一、二审均系遵循上述裁判逻辑进行的审理。一审认定不构成商标侵权,其中提到的理由有:“海底捞”经营“川菜系列火锅”;而“河底捞”是典型的湘菜系列,“均不会使一般的消费者对‘河底捞’的餐饮服务的来源产生误认或者认为其来源与‘海底捞’公司注册商标‘海底捞’之间有特定联系”。而二审则认为:“如以相关公众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进行隔离比对,有可能导致公众对服务来源及其关联性产生混淆误认”。二审得出以上结论,系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在商标混淆判定时应当充分考量权利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的影响;二是一审以“‘海底捞’公司旗下所有店铺经营的菜谱全部是川菜系列的火锅,而河底捞餐馆经营的菜谱是典型的湘菜系列”作为侵权判定的事实基础,实质上将“海底捞”商标的保护范围不当缩限为“‘海底捞’公司目前的主营菜品‘川菜系列的火锅’”。这说明,即便存在现有法律框架的束缚,二审亦已经关注到驰名商标同类保护不能简单按照普通商标侵权处理。不过,依笔者的观察,基于“海底捞”在餐饮界的影响加之其采取直营餐厅的经营模式,相信绝大多数消费者未必发生混淆,而更多可能是因联想到“海底捞”而发出会心一笑,即“河底捞”在蹭热度,换成法律术语是在不正当利用“海底捞”的声誉。由此可见,仅适用混淆标准并不足以解决驰名商标同类保护问题,还需要引入驰名商标保护的淡化理论,否则有可能导致驰名商标同类保护弱于跨类保护。
(二)关于商标淡化。传统观点认为,所谓商标淡化,是指“在非同类或非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上使用他人的驰名商标,尽管不会造成消费者在商品或服务来源上的混淆,但是却降低了该商标指示商品或服务的能力”。[24]《驰名商标司法解释》第9条第2款规定:“足以使相关公众认为被诉商标与驰名商标具有相当程度的联系,而减弱驰名商标的显著性、贬损驰名商标的市场声誉,或者不正当利用驰名商标的市场声誉的,属于商标法第13条第3款规定的‘误导公众,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由此,我国驰名商标淡化包括弱化、贬损丑化和不正当利用三种情形,相关案例也是不胜枚举。
(三)关于理论适用的反思。传统观点认为,商标混淆只发生在同类商品/服务中,商标跨类使用并不会导致混淆,但可能导致驰名商标淡化,因此有必要为驰名商标提供跨类保护。然而可观察的是,在现代市场经济以及全球贸易的背景下,市场主体尤其是大公司的跨国经营或跨产业经营,已使得传统场域下区分混淆与淡化变得不再具有实际意义。首先,《驰名商标司法解释》第9条第1款规定的“特定联系混淆”与第2款规定的“具有相当程度的联系”,在实践中,两者之间有时很难界分。从跨类保护的角度看,当驰名商标被使用在不相同或者不相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上时,相关公众有时并非不发生混淆,也极有可能会误认为商标权人系跨类经营;而从同类保护的角度看,正如前述“河底捞”案的分析,当驰名商标被使用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时,未必导致相关公众混淆,亦存在因为产生联想而导致驰名商标淡化的极大可能性。其次,即便法院在个案中回避认定驰名商标,但涉案商标的知名度与影响力都成为侵权判定的重要考量因素,例如前述“和睦佳宠物医院案”和“河底捞案”中,法院都对此进行了重点阐述。可见,严格“按需认定”以及区分跨类保护与同类保护,已无实际意义,且个案中明显增加法院裁判说理以及法律适用的难度,我国驰名商标制度亟待加以修正。
回顾《巴黎公约》最终设立驰名商标制度的初心,就是为了规制在相同或者类似商品上实施侵害驰名商标的行为,即对驰名商标构成复制、仿制和翻译或者在商标的主要部分构成对驰名商标的复制、仿制,并且可能产生混淆的,“拒绝或撤销注册,并禁止使用”。[25]此后,为弥补《巴黎公约》仅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保护驰名商标的不足,《TRIPS协定》第16条2款进一步将驰名商标保护由商品商标延伸至服务商标;《TRIPS协定》第16条3款还首次将驰名商标保护扩大至不相同、不类似的商品或者服务上。[26] 可见,国际驰名商标制度的发展路径,充分体现出对驰名商标保护范围的扩大以及保护力度的增强,这与我国特定背景下排斥同类认驰并限制跨类认驰,大相径庭。
事实上,在域外实践中,淡化理论并不仅适用于跨类保护,也适用于同类保护。例如,在L’Oreal欧莱雅案中,针对原、被告均用于香水类产品的商标,欧共体法院认为,“‘不当利用他人商标声誉’并不要求一定要产生混淆,或一定要对他人商标构成损害。只要第三人可以从这种‘搭便车’行为中获取利益,且并未因此给予商标权人任何经济补偿即可。”另,欧共体法院2003年1月9日在C-292/00 DAVIDOFF诉GOFKID一案的初步裁决中认为,虽然一号指令第5条第2款所规定的对声誉商标的保护是授权性而不是强制性的规定,但实际适用这一规定立法的国家在执法过程中,不能导致著名商标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所获得的保护反而少于非相同或类似商品上所获得的保护的结果,[27]域外的司法实践经验值得借鉴。
五、总结与建议
1.如前所述,我国2001年《商标法》第13条区分未注册驰名商标与注册驰名商标并分别给予同类保护和跨类保护,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而驰名商标司法解释确立严格“按需认定”的原则,主要是为矫正驰名商标异化现象,且实际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转向创新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现行商标法驰名商标条款及其相应的司法解释已呈现出明显不适宜之处,从而导致驰名商标司法认定的门槛过高,不利于强化对驰名商标的司法保护。
2.我国驰名商标制度及其司法解释应当适应形势发展需要进行相应的修正。其一,应当坚定地选择加大驰名商标保护的基本裁判价值导向。正如有学者深刻指出的,“企业表现在具体商品或服务中的超额利润或商誉,在本质上仍然有赖于企业的长期经营,最终归功于企业在研发创新、生产设计、质量控制、售后服务、人员培训及社区贡献等方面的持续投入和经营成效”“若无企业的核心商誉,商标的显著度再高,也只能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28]因此,相较于普通商标而言,加大对驰名商标的保护,体现的是司法保护对企业通过长期诚信经营所积累商誉的重要激励;其二,在现行商标法“不得宣传条款”的约束下,驰名商标认定应当理性回归事实状态的认定,即驰名商标并非荣誉,只是在商标达到驰名状态下给予其较宽的保护范围和较强的保护力度。因此,无论是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还是商标民事侵权案件中,对商标驰名与否的事实应当正常作出认定,而无需专门阐述认定“必要性”的理由,徒增裁判说理的不必要负担。即凡具备驰名商标事实基础的都应当正常作出认定,并给予驰名商标与其长期累积的商誉程度相当的保护强度;其三,应当统一驰名商标的保护标准。对于普通商标侵权判定仍适用混淆标准,而对于驰名商标的保护,则应当改变现行法的规定,即无论是同类保护还是跨类保护,均应当采用混淆标准+淡化标准,统一裁判尺度。
3.据悉,商标法第五次修正有意参照国际惯例,不再对驰名商标依照注册与否进行保护,这是很大的进步,但仍未考虑将淡化理论扩张适用于同类保护。基于本文的分析论证,笔者建议,商标法第五次修正应当结合以往立法及司法解释规定,对驰名商标条款作如下修正:“就相同或类似商品或者不相同或不相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制、募仿或者翻译他人的驰名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或者足以使相关公众认为被诉商标与驰名商标具有相当程度的联系,而减弱驰名商标的显著性、贬损驰名商标的市场声誉,或者不正当利用驰名商标的市场声誉,误导公众,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与此相应,建议最高法院对《驰名商标司法解释》亦适时作出相应的修订。
注释:
1.well-known trademark,在英文中意为“众所周知的商标”,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翻译为“著名商标”。
2.详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侵犯商标权等民事纠纷案件中认定和保护驰名商标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9】第3号,简称“驰名商标司法解释”)。
3.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课题组:《新发展格局下驰名商标的司法认定和保护》,载《中国审判》2022年第21期,“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022年12月8日,https://mp.weixin.qq.com/s/lotqh-qQ4Vi1Gmo9CJO2zw。
4.王莲峰、胡丹阳:《驰名商标的司法认定原则——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认定“bilibili”属于驰名商标案》,“知识产权那点事”2022年9月30日,https://mp.weixin.qq.com/s/3coaYhnJN6jx0t6jcJ4rwA。
5.《依法正确审理计算机网络域名纠纷案件——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蒋志培就<关于审理计算机网络域名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答记者问》。
6.详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计算机网络域名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法释【2001】24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2】32号,简称《商标民事案件司法解释》)。
7.蒋志培:《如何理解和适用<关于审理商标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载《人民司法》2002年第2期。
8.孔祥俊、夏君丽:《<关于审理驰名商标保护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载《人民司法》2009年第13期。
9.王俊、龙小宁:《驰名商标认定机制对企业经营与创新绩效的影响》,《经济科学》2020年第2期,第61-73页。
10.《驰名商标司法解释》第2条规定:“在下列民事纠纷案件中,当事人以商标驰名作为事实根据,人民法院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认为确有必要的,对所涉商标是否驰名作出认定:(一)以违反商标法第十三条的规定为由,提起的侵犯商标权诉讼;(二)以企业名称与其驰名商标相同或者近似为由,提起的侵犯商标权或者不正当竞争诉讼;(三)符合本解释第六条规定的抗辩或者反诉的诉讼。”第3条规定:”在下列民事纠纷案件中,人民法院对于所涉商标是否驰名不予审查:(一)被诉侵犯商标权或者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成立不以商标驰名为事实根据的;(二)被诉侵犯商标权或者不正当竞争行为因不具备法律规定的其他要件而不成立的。”
11.详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经济形势下知识产权审判服务大局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09】第23号)第8条规定。
12.《商标民事司法解释》第11条规定:“类似商品,是指功能、用途、生产部门、销售渠道、消费对象等方面相同,或者相关公众一般认为其存在特定联系、容易造成混淆的商品。类似服务,是指在服务的目的、内容、方式、对象等方面相同,或者相关公众一般认为存在特定联系、容易造成混淆的服务。商品与服务类似,是指商品和服务之间存在特定联系,容易使相关公众混淆。”第12条规定:“认定商品或者服务是否类似,应当以相关公众对商品或者服务的一般认识综合判断;《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表》《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可以作为判断类似商品或者服务的参考。”
13.安踏(中国)有限公司诉李某某、深圳荣韵眼镜有限公司等侵害商标权纠纷案,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20)粤0306民初38969号民事判决。详见“安踏”眼镜涉嫌侵权,四被告共担责任,“知产宝”2021年10月28日,https://mp.weixin.qq.com/s/86GQlcJ_t1R-7oJGT1OQSQ。
14.和睦家医疗管理咨询(北京)有限公司诉吴中区木渎和睦佳宠物医院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一审: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苏05民初1459号民事判决。法院认定,自1996年3月北京和睦家医疗中心有限公司成立以来,2002年7月至2015年5月,“和睦家”医疗品牌在北京、上海、天津、青岛、广州等地先后开设 了 14 家诊疗机构,包括医院、诊所及综合门诊部等;涉案第 4182278 号“和睦家”注册商标核定服务项目为第44类:医院;保健;医药咨询;疗养院;美容院;理发店;兽医辅助;眼镜行;卫生设备出租;理疗等。该案中原告提交《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基于尼斯分类第十一版》(2019 年文本),根据该区分表,“医院;保健;医药咨询;疗养院”等服务归入 4401“医疗服务”中;而“兽医辅助”归入 4403“为动物提供服务”中。
15.四川海底捞餐饮股份有限公司诉长沙市雨花区河底捞餐馆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一审: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2019)湘0103民初7568号民事判决;二审: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湘01民终7063号民事判决。一审查明,截止至2020年6月30日,“海底捞”公司在全球开设了935家直营餐厅,其中868家位于中国大陆的164个城市,67家位于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及海外等地。
16.钱小莉、吴佳灵:《海底捞告输“河底捞”后,申请池底捞、渠底捞等263个商标!》,南方都市报2020年11月6日,https://mp.weixin.qq.com/s/Dh_F33DjW_G_Ni6fiw5Ogw。
17.宋健:《严格知识产权保护最新进展综述》,载《知产财经》2021年第2期,“知产财经”2021年2月22日,https://mp.weixin.qq.com/s/yQPg-npRJ3UsjRIJ2mSbSw。
18.上诉人约翰迪尔(北京)农业机械有限公司等与被上诉人迪尔公司、约翰迪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京民终413号民事判决。
19.马奇和布雷维提有限公司(简称“马奇公司”)、阿里斯顿热能产品(中国)有限公司诉嘉兴市阿里斯顿电器有限公司等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简称“阿里斯顿商标侵权案”)。一审: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宁知民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二审: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苏知民终字第00211号民事判决。
20.宋健:《关于商标权滥用的司法规制》,载《知识产权》2018年第10期,https://mp.weixin.qq.com/s/1HMJWIRIIYtO-58Htb3BBg。
21.《商标民事司法解释》第9条规定,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一)项规定的商标相同,是指被控侵权的商标与原告的注册商标相比较,二者在视觉上基本无差别;第(二)项规定的商标近似,是指被控侵权的商标与原告的注册商标相比较,其文字的字形、读音、含义或者图形的构图及颜色,或者其各要素组合后的整体结构相似,或者其立体形状、颜色组合近似,易使相关公众对商品的来源产生误认或者认为其来源与原告注册商标的商品有特定的联系。
22.《驰名商标司法解释》第9条规定:足以使相关公众对使用驰名商标和被诉商标的商品来源产生误认,或者足以使相关公众认为使用驰名商标和被诉商标的经营者之间具有许可使用、关联企业关系等特定联系的,属于商标法第13条第2款规定的“容易导致混淆;足以使相关公众认为被诉商标与驰名商标具有相当程度的联系,而减弱驰名商标的显著性、贬损驰名商标的市场声誉,或者不正当利用驰名商标的市场声誉的,属于商标法第13条第3款规定的“误导公众,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
23.2013年《商标法》第57条规定:“(一)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的;(二)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或者在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
24.详见李明德著:《知识产权法》,2008年5月版,第262-266页。
25.《巴黎公约》第6条之二增补于1925年海牙外交大会,现行驰名商标条款形成于1958年里斯本外交大会形成的文本,之后1967年斯德哥尔摩外交大会对此未调整。具体内容:“本联盟各国承诺,如本国法律允许,应在依职权,或依得利害关系人的请求,对商标注册国或使用国主管机关认为在该国已经驰名,属于有权享受本公约利益的人所有,并且用于相同或者类似商品的商标构成复制、仿制或者翻译,易于产生混淆的商标,拒绝或撤销注册,并禁止使用。这些规定,在商标的主要部分构成对上述驰名商标的复制或者仿制,易于产生混淆的,也应适用。”详见《知识产权国际条约集成》,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3月第1版,第6页。
26.详见《知识产权国际条约集成》,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3月第1版,第375页。
27.黄晖著:《商标法》(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16年1月第2版,第257-259页。
28.龙小宁:《反向混淆案件中应该如何确定损害赔偿金额?》,《知产财经》2022年第4期,“知产财经”2022年8月4日,https://mp.weixin.qq.com/s/o9ce1AwkhBqy9pAfk_wb4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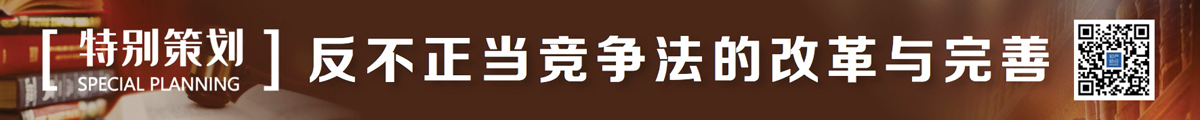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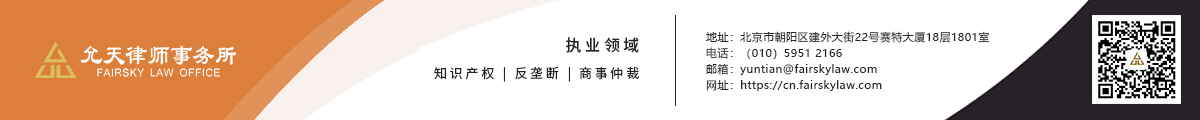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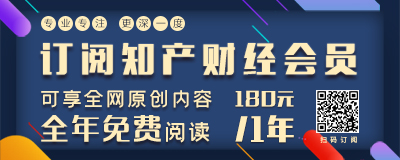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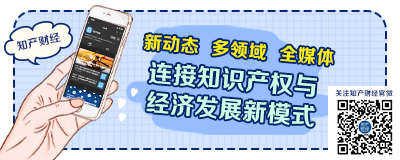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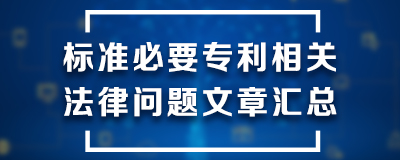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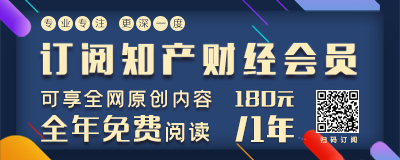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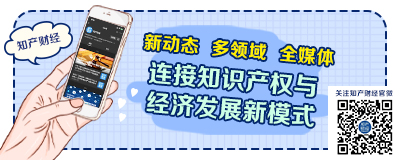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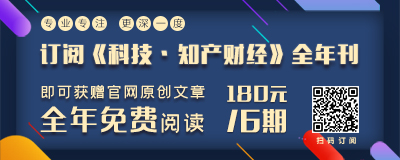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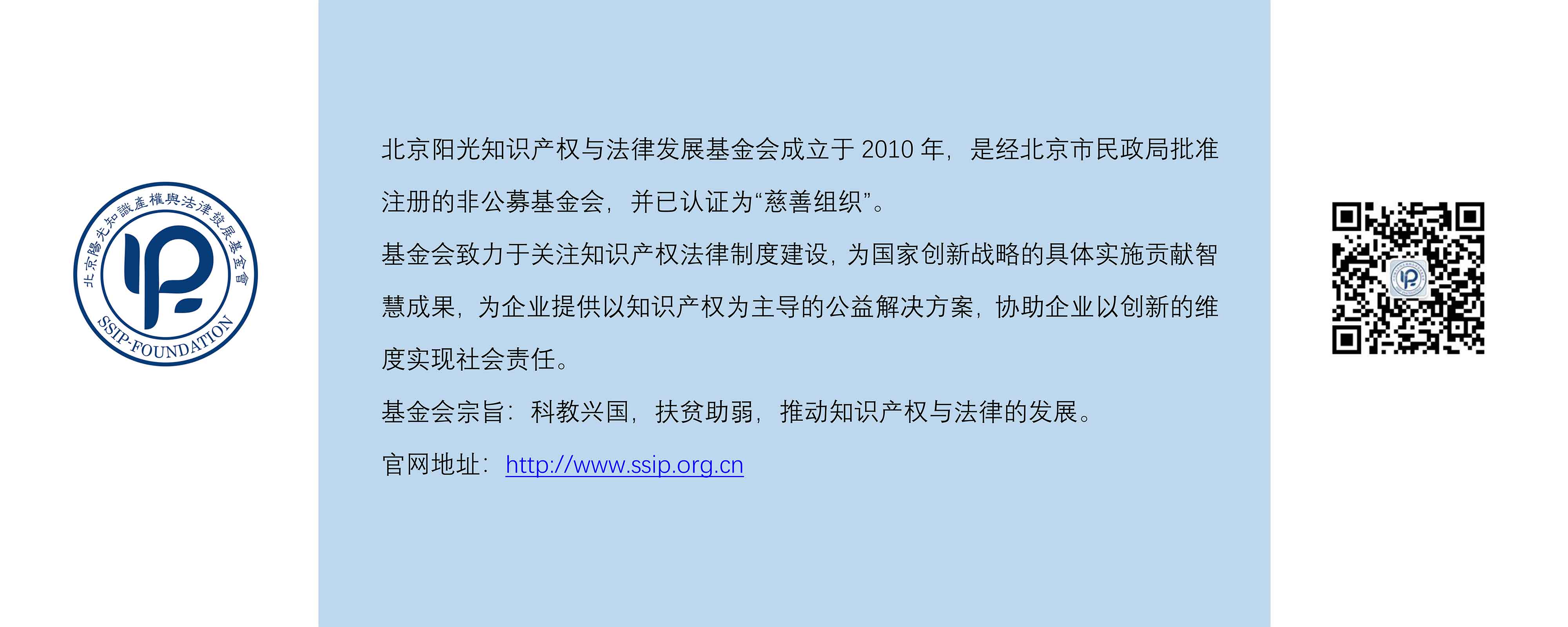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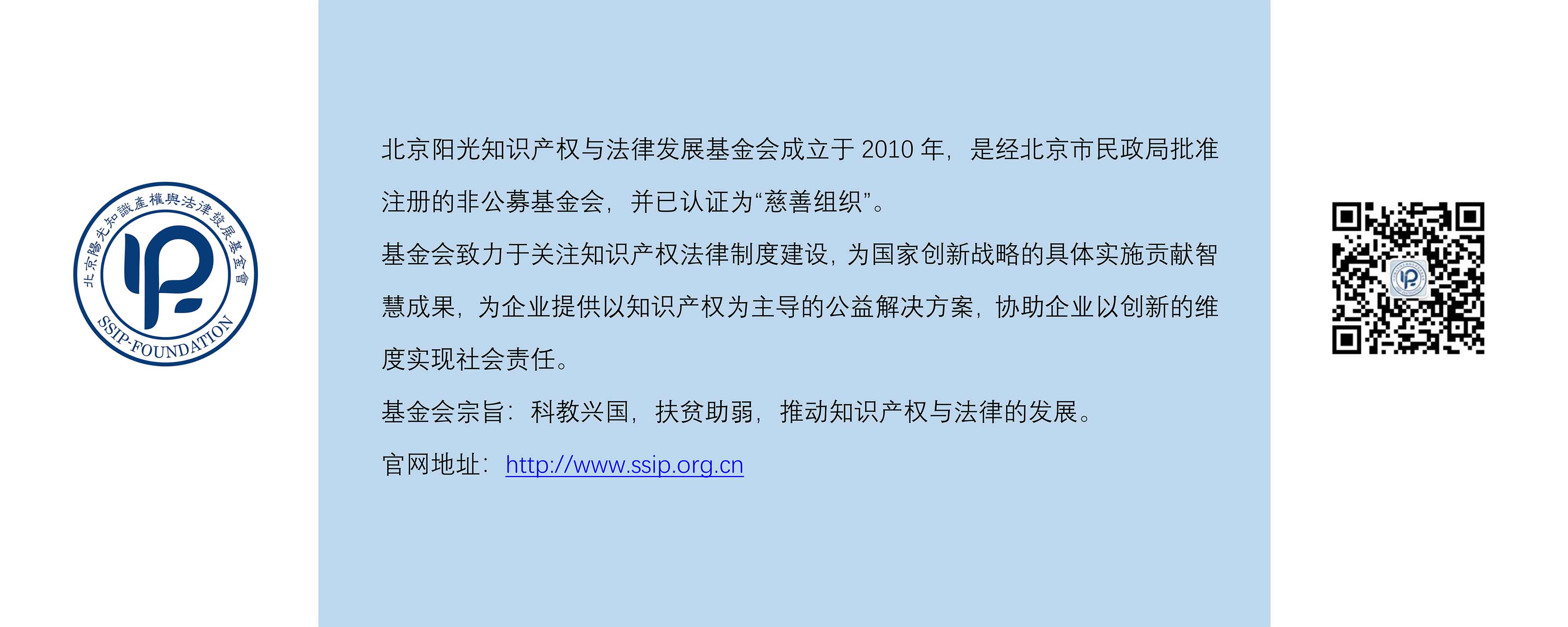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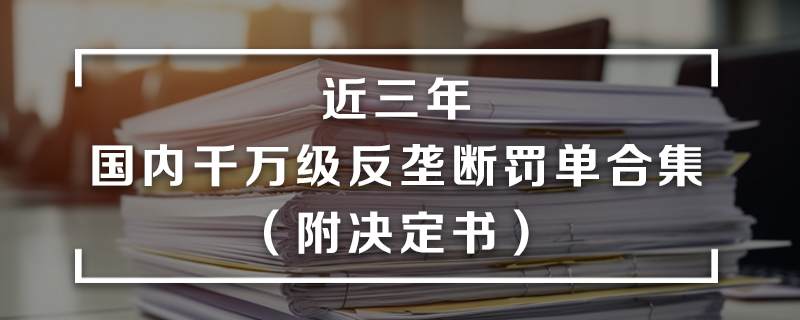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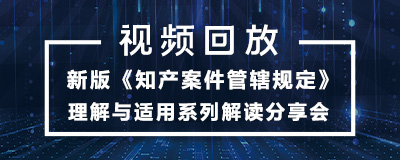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9464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946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