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卫驰翔 上海融力天闻律师事务所
2022年8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22)最高法民辖42号民事裁定书。【相关链接:附裁定下载┃最高院:信网权案件的管辖应以信网司法解释第十五条为依据】最高法在该案裁定中认为,原告住所地法院对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件没有管辖权,理由为以下三点:
1.最高法的司法解释对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件的地域管辖作了特别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中的“信息网络侵权行为”针对的是发生在信息网络环境下,通过信息网络实施的侵权行为,并未限于特定类型的民事权利或者权益。与众不同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定”)第十五条针对的是信息网络传播权这一特定类型的民事权利,是规范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这一类民事案件管辖的特别规定。在确定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的管辖时,应当以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定第十五条为依据。
2.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件的地域管辖以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为原则
2013年1月1日施行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只有在“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均难以确定或者在境外”的例外情形下,才可以将“原告发现侵权内容的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视为侵权行为地。2020年,该司法解释经过修正,前述第十五条规定的内容并未修改,仍然继续施行。
3.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案件不宜将侵权结果发生地作为确定管辖的依据
基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性质和特点,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一旦发生,随之导致“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其侵权结果涉及的地域范围具有随机性、广泛性,不是一个固定的地点,不宜作为确定管辖的依据。
最高法的这一裁定推翻了多年来各地法院对于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件的地域管辖问题所普遍适用的裁判规则。在此之前,各地法院一般认定原告住所地作为侵权结果发生地,原告住所地法院对于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件具有管辖权。例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0日发布的《关于立案审判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答(二)》第17条中对于网络侵权行为的理解:“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二十五条的适用范围,除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和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民事纠纷可以适用外,涉及网络商业诋毁纠纷、仿冒纠纷等不正当竞争纠纷也可适用,但应满足‘侵权行为是利用信息网络载体通过上传、下载、链接等信息网络方式实施’的条件。”上述(2022)最高法民辖42号案件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正是根据这一理解,认为该案不应移送至被告所在地法院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继而依法报请最高法指定管辖。
笔者经检索发现,上述案件并非最高法首次对“信息网络侵权行为”的范围作出界定。本文通过梳理近年来最高法发布的司法解释和裁判文书以及最高法各业务部门编著的“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丛书”,深入探究最高法关于“信息网络侵权行为”地域管辖的意见。
一、最高法曾明确“信息网络侵权行为”包括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
2013年1月1日施行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定第十五条规定:“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侵权行为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网络服务器、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均难以确定或者在境外的,原告发现侵权内容的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 在地可以视为侵权行为地。”2020年,该司法解释经过修正,该条规定的内容并未修改,仍然继续施行。
2015年2月4日施行的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第二十五条规定:“信息网络侵权行为实施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计算机等信息设备所在地,侵权结果发生地包括被侵权人住所地”。2020年以及2022年,该司法解释经过两次修正,上述两条规定的内容并未修改,仍然继续施行。《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2015年3月,由“最高人民法院修改后民事诉讼法贯彻实施领导小组”编著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一书,对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二十五条涉及侵害信息网络侵权行为的地域管辖问题作出解答:“信息网络侵权行为实施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计算机等信息设备所在地,侵权结果发生地包括被侵权人住所地,与《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相一致,明确了网络信息的侵权行为实施地和侵权结果发生地”。关于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的管辖问题,最高法在该图书中亦明确:“在本司法解释起草过程中,也有观点认为,按照上述解释(指信息网络传播权解释,笔者注),可以随意界定被诉侵权行为的网络服务器、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计算机有便捷移动的特征,任何地方都可以视为侵权行为地,这也是无法回避的问题。规定‘信息网络侵权行为实施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计算机等信息设备所在地,侵权结果发生地包括被侵权人住所地’也是为了便于确定管辖”。[1]
2022年6月,由“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工作实施领导小组办公室”编著的《最高人民法院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一书,再次对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案件的管辖问题作出解答,解答内容相较上述2015年3月的版本没有变化。[2]
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定第十五条实施在前,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二十五条实施在后,两部司法解释均历经修正,该等条款内容均未作修改。根据最高法对于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二十五条的条文理解,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的“信息网络侵权行为”明确包括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件,原告住所地法院具有管辖权。
事实上,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也曾对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案件的地域管辖问题作出认定。最高法曾在《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2019)摘要》(以下简称“2019最高法知产案件年报”)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裁判要旨(2019)摘要》(以下简称“2019最高知产法庭裁判要旨”)中,公布了关于“作为管辖连结点的信息网络侵权行为的认定”的裁判规则,通过典型案件(2019)最高法知民辖终13号予以说明。最高法在该案的民事裁定书中认为:“民诉法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的信息网络侵权行为具有特定含义,指的是侵权人利用互联网发布直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信息的行为,主要针对的是通过信息网络侵害他人人身权益以及侵害他人信息网络传播权等行为,即被诉侵权行为的实施、损害结果的发生等均在信息网络上,并非侵权行为的实施、损害结果的发生与网络有关即可认定属于信息网络侵权行为”。
二、最高法发布的其他司法解释关于“信息网络侵权行为”地域管辖问题的“特别规定”
如上所述,尽管(2022)最高法民辖42号案件与最高法在先的条文理解和裁判规则存在法律适用分歧问题,但作为最高法最新裁判生效的案件,该案仍具有较强的参考性。遵循该案中“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定是规范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这一类民事案件管辖的特别规定”这一裁判理由,笔者检索了最高法发布的其他司法解释中对于“信息网络侵权行为”所作出的“特别规定”。
1、人格权纠纷
2014年10月10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侵权行为实施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计算机等终端设备所在地,侵权结果发生地包括被侵权人住所地”。2020年,该司法解释经过修正,上述第二条被删除。
因此,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他人人身权益引起的纠纷,最高法并未通过司法解释作出“特别规定”,适用作为“一般规定”的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二十五条,原告住所地法院具有管辖权。
2、知识产权侵权纠纷
(1)著作权侵权纠纷
除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之外,侵害其他著作权权项或邻接权的行为,也可以通过信息网络实施,如侵害作品发表权、署名权、广播权纠纷以及表演者权纠纷、广播组织权纠纷等。2002年10月15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著作权法解释”)第四条规定:“因侵害著作权行为提起的民事诉讼,由侵权行为的实施地、侵权复制品储藏地或者查封扣押地、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2020年,该司法解释经过修正,该条规定的内容并未修改,仍然继续施行。
作为“特别规定”的著作权法解释并未规定“侵权结果发生地”这一地域管辖连接点,因而原告所在地不能作为确定管辖的依据。至于“侵权行为的实施地”的确定,著作权法解释未作具体规定,适用作为“一般规定”的民事诉讼法解释,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计算机等信息设备所在地。
(2)商标权侵权纠纷
2002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商标法解释”)第六条规定:“因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提起的民事诉讼,由侵权行为的实施地、侵权商品的储藏地或者查封扣押地、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2020年,该司法解释经过修正,该条规定的内容并未修改,仍然继续施行。
作为“特别规定”的商标法解释确定的管辖连接点同样不包括“侵权结果发生地”。据此,针对在信息网络中实施的侵害商标权行为提起的诉讼,原告住所地法院不具有管辖权。关于“侵权行为的实施地”,同样适用作为“一般规定”的民事诉讼法解释,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计算机等信息设备所在地。
(3)专利权侵权纠纷
侵犯专利权的商品可能通过信息网络进行销售或许诺销售。2001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专利法规定”)第五条规定:“因侵犯专利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侵权行为地包括:被诉侵犯发明、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产品的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等行为的实施地;专利方法使用行为的实施地,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的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等行为的实施地;外观设计专利产品的制造、许诺销售、销售、进口等行为的实施地;假冒他人专利的行为实施地。上述侵权行为的侵权结果发生地”。2013年、2015年和2020年,该司法解释经过三次修正,该条规定的内容并未修改,仍然继续施行。
作为“特别规定”的专利法规定包括了“侵权行为的侵权结果发生地”这一管辖连接点。但是,原告住所地并不能当然作为专利权侵权行为的结果发生地。2019最高知产法庭裁判要旨及2019最高法知产案件年报指出:“作为管辖连结点的信息网络侵权行为系指在信息网络上完整实施的侵权行为;若侵权行为仅部分环节在线上实施,则不构成上述信息网络侵权行为”。在典型案件(2019)最高法知民辖终13号民事裁定书中,最高法认定:“交易过程中,网站和微信仅仅是双方交易的媒介,被诉侵权人仅通过互联网不能实施被诉侵害专利权的行为。在网络普及化程度很高的当代社会,如果案件事实中出现网站平台或者双方通过微信等涉网络相关的方式沟通,抑或双方系通过信息网络平台进行被诉侵权产品的交易,即认定为构成信息网络侵权行为,属于对民诉法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制的范围理解过于宽泛,不符合立法的本意……侵权结果发生地应当理解为侵权行为直接产生的结果的发生地,不能以权利人认为受到损害就认为其所在地就是侵权结果发生地”。
(4)侵害网络域名纠纷
2001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域名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网络域名解释”)第二条规定:“涉及域名的侵权纠纷案件,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对难以确定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的,原告发现该域名的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可以视为侵权行为地”。2020年,该司法解释经过修正,该条规定的内容并未修改,仍然继续施行。
作为“特别规定”的网络域名解释并未界定“侵权行为地”的范围,适用作为“一般规定”的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二十四条和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侵害网络域名纠纷的地域管辖连接点包括原告住所地。
3、不正当竞争纠纷及垄断纠纷
不正当竞争行为中的仿冒、虚假宣传、侵害商业秘密、商业诋毁以及网络不正当竞争等行为,均可以通过信息网络实施。2022年3月20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因不正当竞争行为提起的民事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当事人主张仅以网络购买者可以任意选择的收货地作为侵权行为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同样,该“特别规定”并未界定“侵权行为地”的范围,适用作为“一般规定”的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二十四条和第二十五条的规定,通过信息网络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产生的纠纷,原告所在地法院具有管辖权。
关于垄断纠纷,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可能发生在信息网络中,例如“抖音诉腾讯垄断纠纷案”。2012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的地域管辖,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依照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有关侵权纠纷、合同纠纷等的管辖规定确定”。2020年,该司法解释经过修正,该条规定的内容并未修改,仍然继续施行。据此,通过信息网络实施垄断行为的管辖,直接适用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二十四条和第二十五条的规定确定。
4、网络侵权责任纠纷
处理网络侵权责任纠纷的法律依据主要是《民法典》第1194-1197条,《电子商务法》《网络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最高法未发布相关司法解释对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件的地域管辖作“特别规定”。
三、最高法曾明确《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与“信息网络侵权行为”相关案由的地域管辖均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和侵权结果发生地”
2021年11月,由“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著的《最高人民法院新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理解与适用》一书,该书出版说明记载:“本书编写以第三级案由为基准,从释义、管辖、法律适用和确定该案由应当注意的问题四个方面进行阐述……‘管辖’部分结合现行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明确指出管辖法院,以便当事人起诉和立案法官审查”。
笔者发现,根据该书“条文理解与适用”部分的阐述,人格权纠纷、著作权侵权纠纷、商标权侵权纠纷、专利权侵权纠纷、侵害网络域名纠纷、不正当竞争纠纷、垄断纠纷以及网络侵权责任纠纷,这些可能涉及“信息网络侵权行为”案由的地域管辖,均可以适用一般民事侵权纠纷案件的规定,即《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和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二十四条,管辖连接点除了被告住所地外,还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和侵权结果发生地。尽管著作权法解释、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定和商标法解释并未规定“侵权结果发生地”作为地域管辖的连接点,但该书并未因该等“特别规定”而排除适用一般民事侵权纠纷案件地域管辖的规定。[3]
四、最高法各业务部门关于“信息网络侵权行为”地域管辖的法律适用分歧有待进一步解决
通过以上梳理不难发现,最高法各业务部门关于“信息网络侵权行为”地域管辖的法律适用问题存在分歧,具体表现为:
1.(2022)最高法民辖42号裁定确立的裁判规则与最高法在先发布的条文理解和裁判规则不一致;
2.著作权侵权纠纷以及商标权侵权纠纷的地域管辖连接点是否包括“侵权结果发生地”不明确。
2019年10月28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法律适用分歧解决机制的实施办法》第一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是最高人民法院法律适用分歧解决工作的领导和决策机构。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最高人民法院各业务部门和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根据法律适用分歧解决工作的需要,为审委会决策提供服务与决策参考,并负责贯彻审委会的决定”;第二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各业务部门在案件审理中,发现存在以下情形的,应当向审管办提出法律适用分歧解决申请:(一)最高人民法院生效裁判之间存在法律适用分歧的;(二)在审案件作出的裁判结果可能与最高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确定的法律适用原则或者标准存在分歧的”;第十一条规定:“审委会关于法律适用分歧作出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各业务部门、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各专门人民法院在审判执行工作中应当参照执行”。
目前,尚不清楚(2022)最高法民辖42号裁定是否属于最高法审委会就法律适用分歧问题进行讨论后所作出的决定。关于上述法律适用分歧问题,有待最高法以适当的形式和范围作进一步明确,以便当事人起诉和各级人民法院参照执行。
注释:
[1]最高人民法院修改后民事诉讼法贯彻实施领导小组编著:《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3月第1版,第170-173页。
[2]详见: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工作实施领导小组办公室编著:《最高人民法院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2年6月第1版,第126-128页。
[3]详见:杨万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著:《最高人民法院新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年11月第1版,第66-89、456-467、484-489、504-512、517-520、524页。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知产财经立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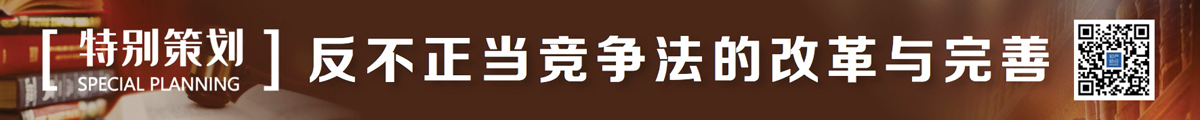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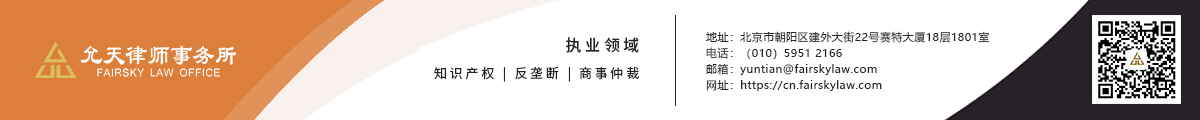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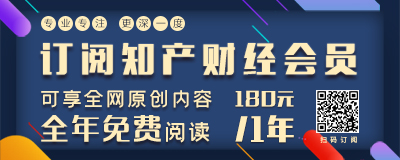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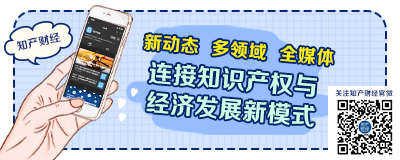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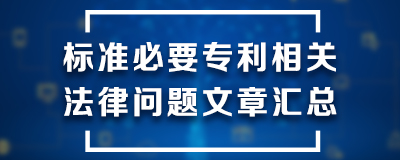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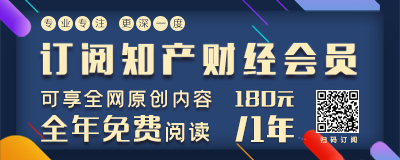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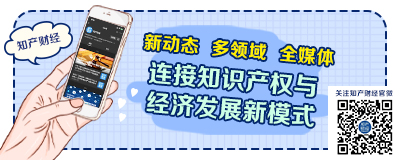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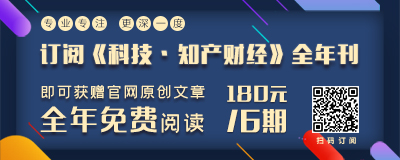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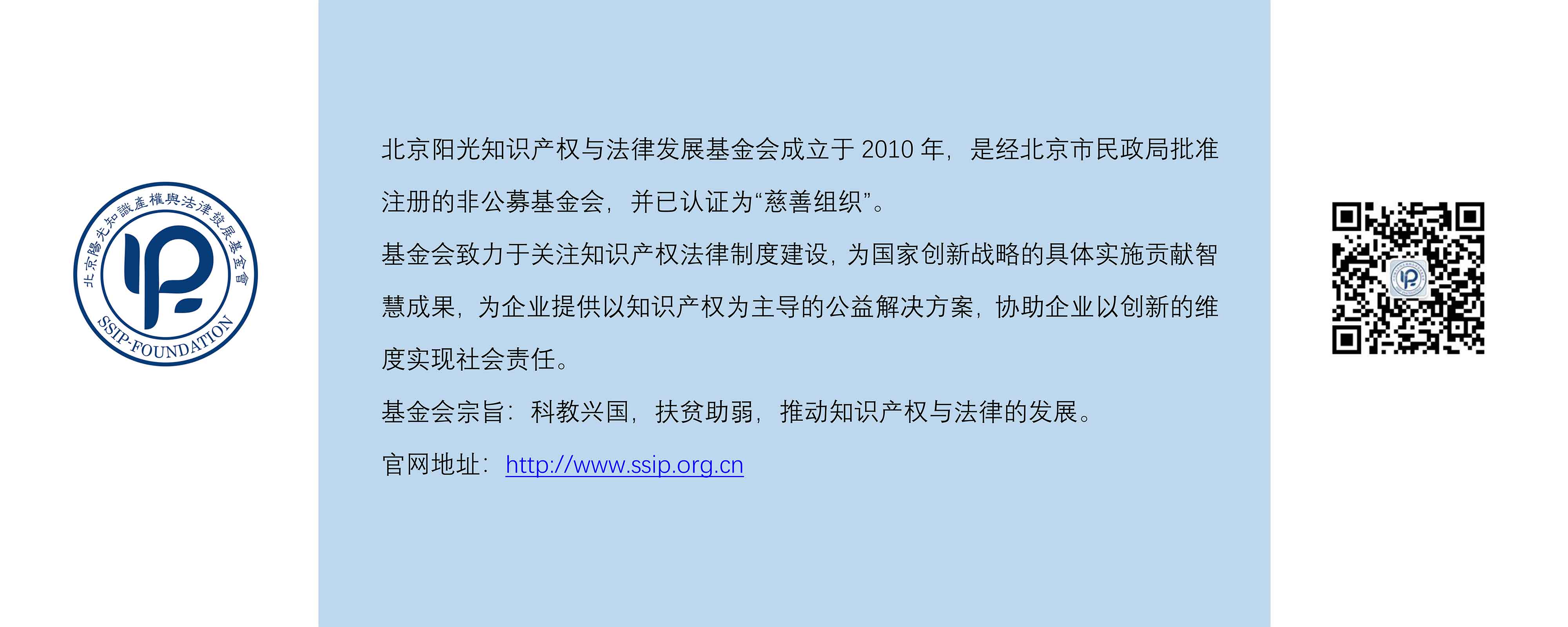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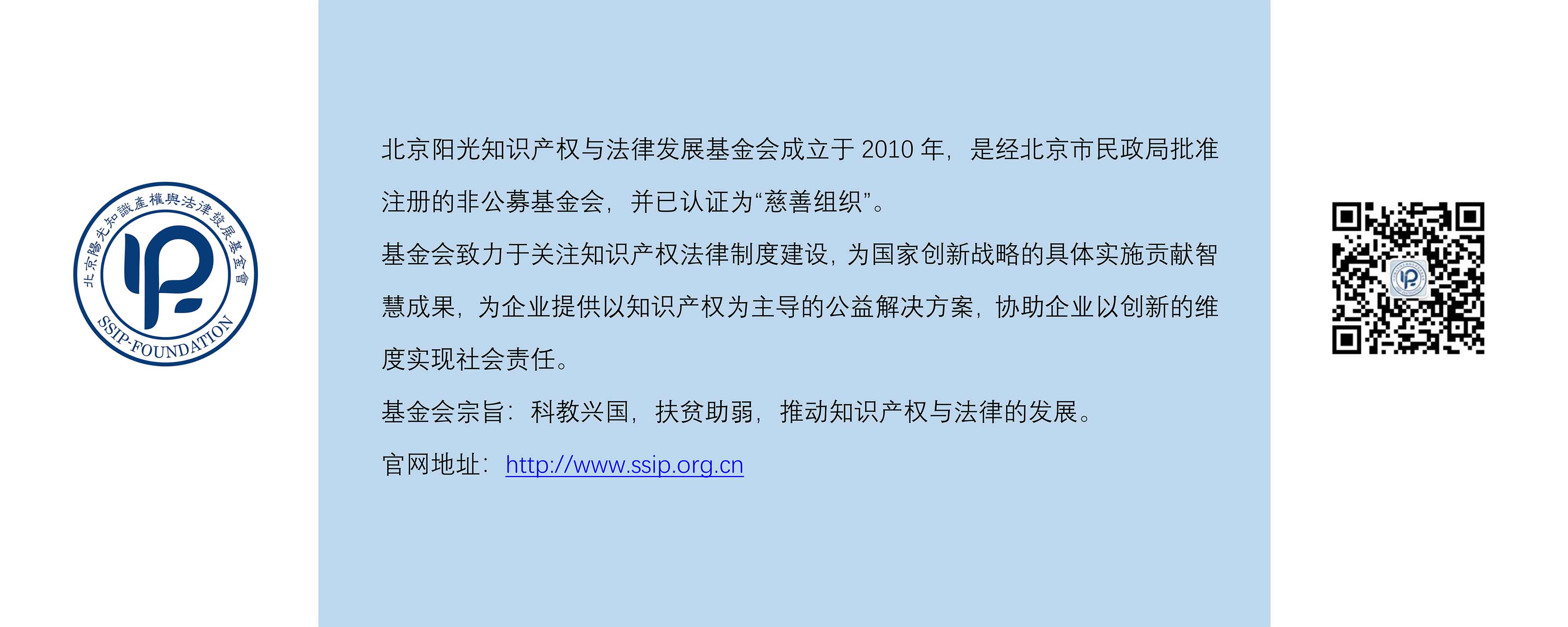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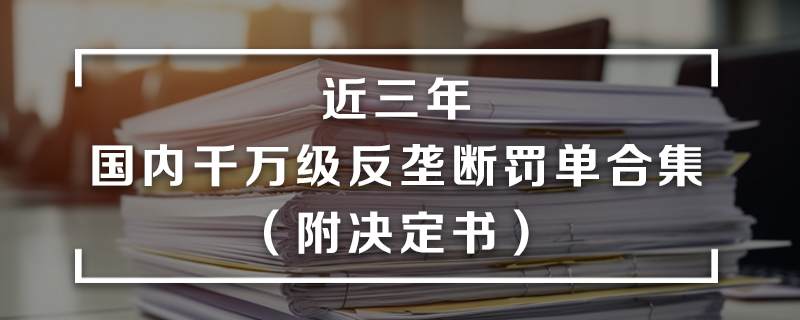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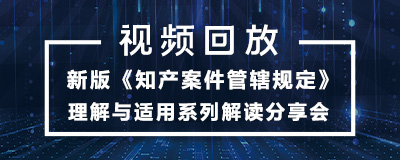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9464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946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