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 迁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郑涵睿 华东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
摘要:《率土》诉《三战》案判决中,法院创造性地将具体游戏规则认定为表达,并将电子游戏作为新作品类型保护。作为“规则”的一种,网络游戏的基础性程序性本质使其不能被归为表达。在适用视听作品保护电子游戏并无不当的情况下,不宜采用兜底条款创造新作品类型。
今年5月23日,网络游戏《率土之滨》(以下称“《率土》”)经营者诉另一网络游戏《三国志·战略版》(以下称“《三战》”)经营者著作权侵权一案在广州互联网法院宣判。[1]判决书中将《率土》游戏从现有八种法定作品类型中独立出来,认定为“符合作品特征的其他智力成果”,同时将具有“独创性”的“具体游戏规则”和“规则之间的联系所构成的游戏机制”认定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表达”。法院通过对比两款游戏涉及的121条游戏规则和之间的耦合,认定《三战》所使用的案涉79项游戏规则及游戏机制系《率土》的基本表达,故《三战》侵犯《率土》的改编权,判令对涉案游戏规则及游戏机制进行修改,并赔偿5000万元人民币。
本案判决一经公布,即引起广泛关注,主要聚焦于游戏规则能否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而纵观判决书,本文认为主要有三个关键点值得讨论。首先是“具体游戏规则”是否可构成“表达”,其次是将“游戏”整体归入新作品类型是否得当,最后是本案对电子游戏的著作权保护机制是否适当。
一、“具体游戏规则”仍属于思想
该案中,法院将电子游戏规则分为“基础游戏规则”和“具体游戏规则”,认为基础游戏规则作为划分游戏类型的依据,决定了整个电子游戏的设计方向和具体游戏规则的设计思路,属于思想范畴。而具体游戏规则是“围绕基础游戏规则展开的详尽细致的设计,具有广阔的创作表达空间”,具有独创性可成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表达。虽然法院详细论述了具体游戏规则如何构成表达,但恐怕混淆了思想/表达二分法划分的界限。纵然思想的细化和个性化展示是其具象化为表达的重要途径,但“规则”之所以被排除在表达之外,是其自身的性质决定的,再详细的规则本身也不可脱离思想范畴。
论证游戏规则是否能构成表达前,需明确游戏规则的概念。在游戏界,美国学者曾指明作为一种“系统”的游戏规则为玩家提供了基于操作进行限制或给予奖励的约束机制。[2]国内亦有学者明确电子游戏规则是指在运行游戏时玩家所遵循的法则,是现实世界中游戏现象的深层架构。[3]故本文认为游戏规则是指参与游戏的过程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规定和程序性要求。[4]而本案中法院所指“游戏机制”较“规则”更为抽象,亦具有基础性和程序性,为表述方便,本文所称游戏规则包含游戏机制。
法院分三步论证具体游戏规则可构成表达:首先论证电子游戏规则所固有的实用性技术功能作用不能阻却其成为表达;其次说明具体游戏规则具有广阔的创作表达空间,可进行独创性设计;最后认为具体游戏规则可在游戏中通过画面和文字进行呈现,让玩家感知到。但这些论证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混淆了游戏规则和游戏规则的具体呈现方式。法院以“要塞”这一游戏规则为例,配以图示和文字说明具体游戏规则能以文字、图形等形式呈现于游戏画面让玩家感知,故不是抽象的思想。然而并非能被呈现和被感知到的东西就一定是著作权法中的表达,著作权所不保护的思想也并非是仅存在于脑海中的构想,而是有别于具体表达的抽象概念,思想的外化必然意味着以一定方式“呈现”同时被接受者“感知”。那种认为游戏规则只要可“呈现”即符合《著作权法》第三条“能以一定形式表现”要求故而可构成“表达”的逻辑,混淆了“游戏规则具体呈现方式是否能受到保护”与“游戏规则本身能否受到保护”这两个问题。
由于游戏规则的本质是基础性和程序性要求,性质上属于著作权法不予保护的对象。TRIPs协定就强调了思想、程序、操作方法、数学概念等不属于版权保护的客体,[5]该原则已成为基本共识。再具体的游戏规则也只是“程序和操作方法”。例如一个技术发明的专利说明书可视为详细到让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实施该技术方案的“具体表达”,其具有独创性的说明书文本(即文字组合、遣词造句)可以构成作品,但这并不代表被文本所描述的技术方案也是作品、也能受到著作权法保护。[6]同样道理,游戏规则可以通过文字、图形或视频的方式予以呈现,具有独创性的后者可构成受保护的作品,并不代表前者也是受保护的作品,二者性质完全不同,以往直接或间接保护游戏规则的案例均陷入了此误区。[7]
其次,将“独创性”要求与“构成表达”的要求混淆。法院认为单个具体游戏规则和游戏机制的设计可体现游戏创作者的个性化选择,使其具有独创性。该逻辑与“太极熊猫”诉“花千骨”及“蓝月传奇”诉“烈焰武尊”案的判决逻辑类似,[8]均忽略了“独创性”的要求是特别针对表达而言的。思想也可具有独创性,但并不受著作权法保护。无数改变人类生活与生产方式的发明都是具备高度“独创性”的,然而发明(技术方案)本身仍然因属于“思想与表达两分法”中的思想,从著作权法的角度去考虑它们的“独创性”是没有意义的。即便是考虑游戏规则本身的独创性,法院关于规则具有“广阔的创作表达空间”这一结论也令人质疑。以法院所举“要塞”为例,该概念是古代战争下的惯常意象,修建要塞的条件和升级所需的资源无非与玩家通过扩张或采集获取的资源或声望有关,其可容纳的队伍数量考虑到游戏性也不宜设置得过高,是否可以拆除也仅有可拆或不可拆两种选项。模拟战略类SLG游戏发展至今,很多规则和机制已成为业内通用模式,且游戏规则的设计需考虑游戏背景和玩家心理,为保障逻辑性和可玩性,规则的创新空间似乎并不如判决书所称的如此“广阔”。
最后,混淆了技术本身和利用技术过程形成的文学艺术表达。判决书以乐谱、剧本和摄影作品为例,认为“任何特定的美感表达都可以被翻译为特定的操作流程”。且不论这种类比严重扩大了著作权法中“操作方法”的含义,将文学艺术表达与操作方法联系在一起,即便是遵循判决书的思路,著作权法保护的也是“特定操作流程”下形成的表达而非操作流程本身。以摄影作品为例,即便将取材、构图、配色、特效等方面的选择视为“关于操作方法的选择”,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也是感光材料等物质载体所记录的“客观物体形象”,[9]也就是具有独创性的影像效果,而非操作方法本身。一名摄影师借鉴另一名摄影师采用的摄影方法进行拍摄,只要由此形成的影像效果并不实质性相似,也不会构成侵权。即使如实用艺术品那样,一件实用品同时具有实用性与艺术性,受保护的也仅是艺术表达,而不是实用功能,且当艺术表达与实用功能在物理上和观念上都不可分离时,为防止通过著作权法垄断实用功能,相应的艺术表达也不能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
判决书希望用游戏规则的可移植性证明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和地位,同时用建筑物和设计图纸的同一性来类比游戏画面与游戏规则具有同一性,认为如建筑物是施工队严格按照设计图纸施工的结果,电子游戏是游戏开发人员严格实现策划文档(载有游戏规则)的结果。该类比是无法成立的。思想不受著作权保护不代表思想不能独立存在并具有自身的价值,比如棋牌类游戏的规则作为思想当然能独立存在并具有价值。但正因为思想不能受到保护,以通常方式对此类游戏规则的文字表述会与思想(规则)发生混同,因此即使其属于形式上的“表达”也不能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法院强调的“游戏规则只有在具体游戏中才能被理解和运用”“游戏规则和具体的游戏浑然一体,不可分割”“规则系统可以移植到具有不同素材甚至不同媒介的游戏上”,恐怕对棋牌类游戏也同样适用。建筑物的外观与建筑物外观设计图是同一作品的不同表现形式,当然都受著作权法的保护,但原因也正是在于建筑物外观设计图被公认为是思想的表达,对此并不存在争议,而依照策划文档记载的游戏规则进行游戏开发则更类似于遵循技术方案实施发明专利,发明人只能寻求专利法的保护,而不能将技术方案当作作品要求保护。
主张对游戏规则保护实质陷入了一个泛道德误区,即认为“创意”作为付出较多成本的一种智力活动结果,不应被他人随意利用。诚然游戏规则具有较高的市场价值,但这也与该智力成果能否作为作品保护无关。电子游戏规则不应仅因电子化的身份就脱离“规则”的范畴,电视节目模式和普通游戏规则一样属于“规则”。若电子游戏规则能够成为表达,是否电视节目模式、桌游规则只要足够详细亦可构成表达?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二、电子游戏不应单独类型化
自《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以来,本案第一次适用作品类型的兜底条款,将电子游戏单独作为一类作品予以保护。根据判决书的论述,创设“游戏作品”主要甚至唯一目的是将游戏规则纳入著作权保护范围,这也是为何判决书多次强调“电子游戏的独创性体现在游戏规则、游戏素材和游戏程序的具体设计、选择和编排中”,且用大量篇幅论述游戏规则独立存在的价值和重要地位。前文已经说明,游戏规则本质上仍然属于思想。既然是思想,无论在何种类型作品中都不能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为保护游戏规则这一思想而认定新类型作品,恐怕是在不适当的方向上走得更远。若排除游戏规则(当然本来也应当排除),电子游戏的代码化指令序列可作为计算机程序受到保护。游戏中的文字、音乐、图像和视频则可能分别构成文字作品、音乐作品、美术作品和视听作品,或者将这些因素有机组合而成的带伴音的整体连续画面作为视听作品提供保护。对此,《著作权法》规定的法定作品类型已经足够了。
将电子游戏整体画面作为视听作品保护不仅符合著作权法的规定,也是各国司法实践中所采用的做法。判决书认为视听作品的一般特征为“由一系列有伴音或者无伴音的画面组成”,这当然是正确的。而电子游戏整体画面显然具有这一特征。即便是在《著作权法》修订之前,法院也早已在司法实践中认定电子游戏是“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后多数法院仍然是这样认定的。[10]这是因为电子游戏的表现效果与传统电影高度相似,均属于多种元素的有机组合而成的连续画面,且将其拆分又可单独构成不同作品,此外两者的创作过程也十分相似。
纵观世界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主流国家均倾向于将电子游戏的视听部分认定为视听作品(电影作品)。例如美国和英国法院普遍认同将电子游戏归于电影作品的范畴,[11]澳大利亚法院也将电子游戏认定为电影作品。[12]欧盟虽然没有明确规定电子游戏的类型,但也认为欧盟版权指令下对于电影作品的定义足够宽泛,足以包括电子游戏的展示。[13]而在亚洲,作为电子游戏产业较为发达的日本和韩国也均将电子游戏涵盖在电影作品(视听作品)下。[14]在笔者的检索下,目前仅有印度尼西亚版权法将“电子游戏”列为电影作品之外的一种作品类型。[15]然而该法还将对作品与数据进行汇编而形成的汇编作品,与对传统文化表达(即民间文学艺术表达)进行汇编形成的汇编作品分列为两类作品,[16]而后者明显构成前者的下位概念。因此“电子游戏”是否在逻辑上属于与电影作品并列的作品,在该法中也值得讨论。
本案判决书之所以认为电子游戏不同于视听作品,在于其坚持电子游戏不同于电子游戏画面,始终意图抽象地保护画面背后的“电子游戏”。然而著作权法区分作品类型考虑的是直接表现形式,而非形式背后的抽象概念。无论画面背后的思想多具有独创性,都无法改变游戏画面所表现出的视听作品的特性。
在可认定法律已明确规定的作品类型时,不宜贸然适用兜底条款创设新的作品类型。虽然我国对作品类型采取了“列举+兜底”的模式,但并不意味着作品类型兜底条款是“万金油”。事实上正如《伯尔尼公约及其超越》指出,“未被(《伯尔尼公约》第2条第1款)列出,但理论上可能属于第2条第1款中‘文学或艺术作品’的情形,在现实中几乎不存在。”[17]实践中包括美国在内实行“作品类型开放”模式的大部分国家均对法律明文规定外的作品类型认定极其审慎。而作为成文法体系国家,判例在我国不具备立法效力,若将电子游戏单独类型化,存在未来不同法院同案不同判的隐患。国际上公认的作品类型是通过各国长期的实践及条约谈判形成的,如计算机程序在著作权法中的地位问题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出现和发展早已产生,但由于各国的意见分歧和利益纷争,直到1994年的TRIPs协定才将计算机程序定为文字作品提供保护。如果本案的判决结果得到推广,恐使我国成为世界为数极少的将电子游戏作为一类作品单独提供保护且保护其中规则的国家。
三、对电子游戏规则的利用应视个案情况判断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
近期用著作权保护游戏规则的判决时有出现,反映出试图利用法定权利加强对电子游戏保护的倾向。支持保护“具体游戏规则”应受著作权法保护的观点也多以“换皮游戏”打击游戏业创新,有损游戏产业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等来强调著作权保护的必要性。然而著作权法有其自身的逻辑和范围,许多侵害著作权的行为当然也是一种不公平利用智力成果的行为。但不能反过来认为,只要是不公平利用智力成果的行为都构成侵害著作权的行为,更不能为此将所有的智力成果都认定为作品。
事实上鉴于游戏规则在著作权法中属于思想的本质属性,用著作权法提供保护既不可行,也不合理。但这并不妨碍在个案中,法院根据相关的事实和证据,认定被告利用原告游戏规则的行为违反公认的商业道德,从而构成不正当竞争。在涉及卡牌游戏“换皮”的案件中,法院一方面认为游戏规则不能获得著作权法的保护,另一方面又根据该案的具体案情,认为被告抄袭原告游戏规则的行为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的规定,应当承担责任。[18]当然,从案件审理的角度看,一旦认定游戏规则是作品,则只要未经许可以复制等受专有权利规制的方式利用游戏规则,除非存在权利限制,就必然构成对著作权的侵害,对游戏规则的保护而言是一条“捷径”。相反,认定对游戏规则的利用构成不正当竞争必须高度依赖于个案中的事实和证据,也就是要对被告的利用行为是否达到违反公认的商业道德作出判断。不同情况下对同一游戏规则的利用可能会有不同的认定结果,这对法院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然而,对许多复杂的问题本来就不存在简单的解决方案。抗拒兜底作品类型的诱惑,不走“捷径”,坚持著作权法的基本原理和规则,是法院在审理电子游戏侵权案件中应当采取的方法和立场。
注释:
1.参见广州互联网法院(2021)粤0192民初7434号民事判决书。
2.See Bruce E. Boyden, Games and Other Uncopyrightable Systems, 18 Geo. Mason L. Rev. 455-459 (2011); See Jesper Jull, Half-real: Video Games Between Real Rules and Fictional Works, The MIT Press 58-60 (2011).
3.参见西门孟:《游戏产业概论》,学林出版社,2008年第100页.
4.刘鹏,王迁:《网络游戏规则可版权性问题分析》,载中国法院网,2019年12月30日,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9/12/id/4750526.shtml.
5.See 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rticle 9.2.
6.参见张伟君:《呈现于视听作品中的游戏规则依然是思想而并非表达——对若干游戏著作权侵权纠纷案判决的评述》,载《电子知识产权》2021年第5期,第66-76页。
7.例如“太极熊猫”诉“花千骨”游戏侵权案终审判决中,江苏高院认为“该规则中包括了具体的触发条件、道具数量、界面布局、操作流程等,已经具体细化到了一定的程度,故其可以被认定为具有独创性的受著作权法保护的‘表达。’”参见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苏民终 1054 号民事判决书。
8.参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 01 民初 3728 号民事判决书;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苏中知民初字第 00201 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苏民终 1054 号民事判决书。
9.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4条第1款第(10)项。
10.参见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021)粤73民终1245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苏民终1054号民事判决书;广州互联网法院(2019)粤0192民初38509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浙民终709号民事判决书;参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 01 民初 3728 号民事判决书;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苏民终 1054 号民事判决书。
11.Greg Lastowka, Copyright Law and Video Games: A Brief History of an Interactive Medium, (2013); Per Ginsberg J in Atari Games v Oman 979 F 2d 242 (1992); Stern Electronics, Inc. v Kaufman 669 F.2d 852 (2d Cir.1982); Atari, Inc. v. Amusement World, Inc. 547 F Supp 222 (1981);Susan Corbett, Videogames and their clones – How copyright law might address the problem, 32 Computer Law & Security Review 615 (2016).
12.Sega Enterprises Ltd v Galaxy Electronics Pty Ltd [1996] FCA 1740.
13.See F. Willem Grosheide, Herwin Roerdink & Karianne Thom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for Video Games - a View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9 JICLT 1 (2014).
14.See Masaya Uchimura, Is a Video Game a Cinematographic Work? 6(2) CASRIP Newsletter 1999; Gyooho Lee, Recent Issues on Digtal Gaming and Copyright in Kore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ransactions Law 1 (2015).
15.See Law of Republic of Indonesia Number 28 of 2014 on Copyrights, Article 40(1)r.
16.See Law of Republic of Indonesia Number 28 of 2014 on Copyrights, Article 40(1)p,q.
17.Sam Ricketson& Jane C.Ginsburg,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and Neighbouring Rights: The Berne Convention and Beyond (2n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409.
18.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沪一中民五(知)初字第22号。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知产财经立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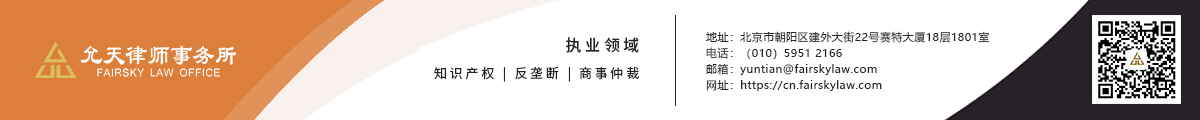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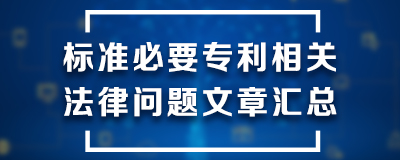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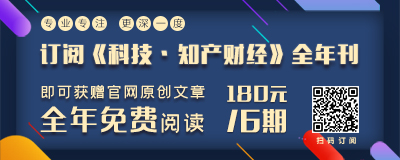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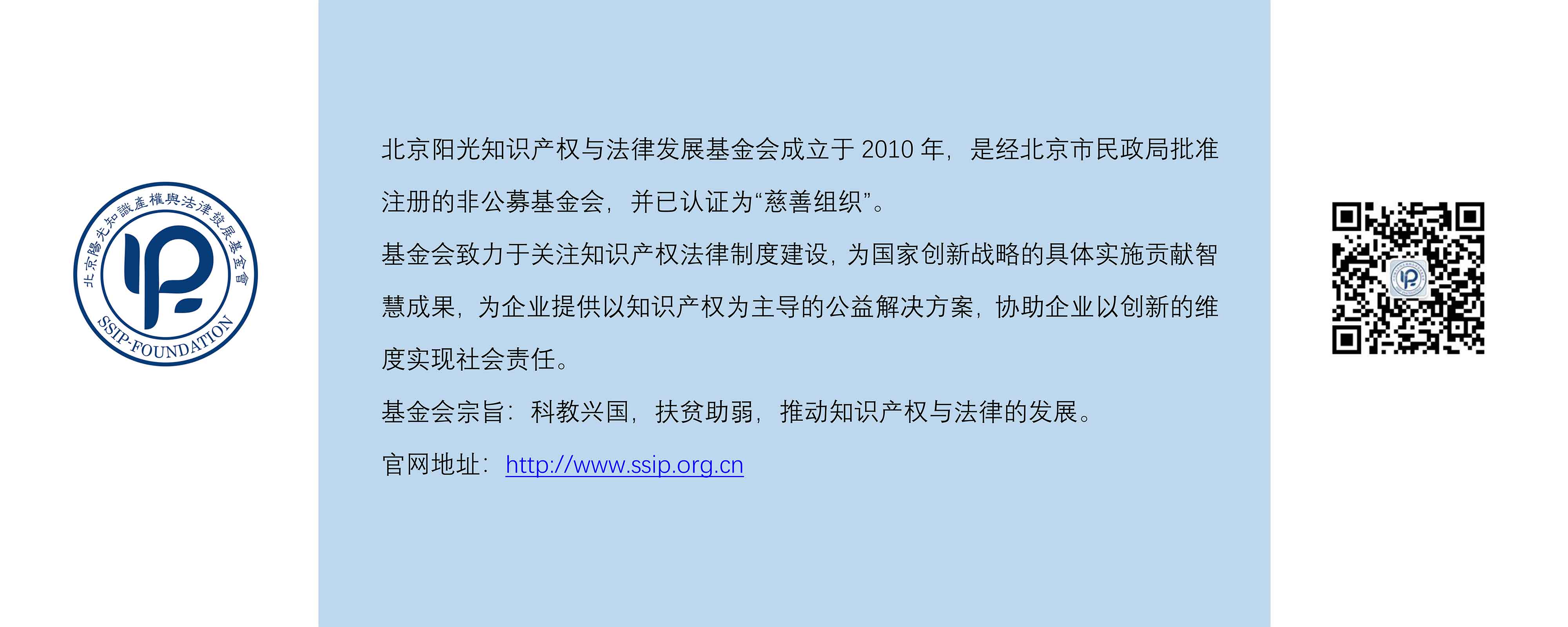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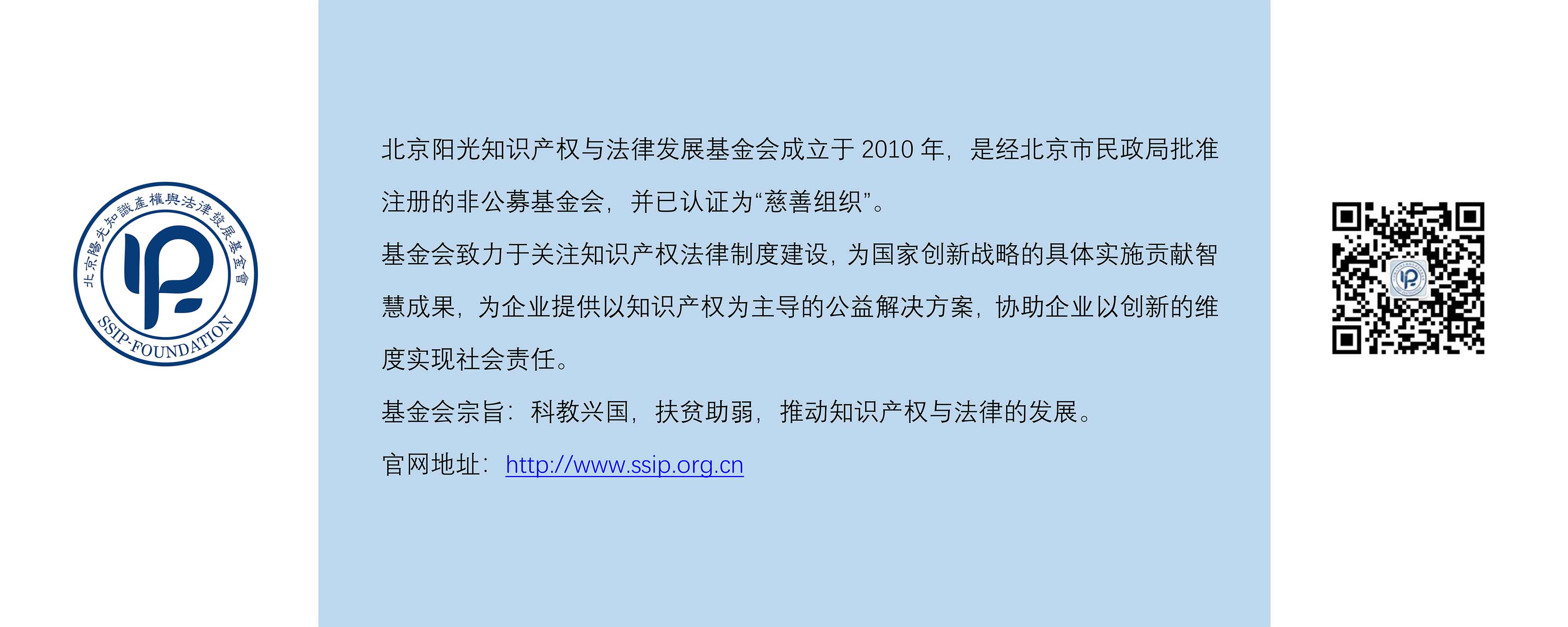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9464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946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