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法院2022年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典型案例
扫码下载判决书
一、陈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再审案
【案例索引】
一审:重庆市梁平区人民法院(2019)渝0155刑初4号
二审: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渝02刑终590号
再审: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21)渝刑再1号
【基本案情】
2016年6月,原审被告人陈某在实施项目施工过程中,因业主方另行推荐使用某品牌洁具,陈某经市场询价后,认为约定的洁具产品价格与正品价格悬殊太大,为完成施工任务,决定使用假冒某品牌洁具,遂安排工作人员帅某购买假冒某品牌的洗脸盆、龙头、小便器、蹲便器和水箱等洁具。陈某将以上假冒某品牌洁具产品安装于承建工程后交付使用,获取假冒某品牌洁具产品的对价171126.78元,违法所得17192.78元。
【裁判结果】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原审被告人陈某在履行包工包料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安装材料获取劳务报酬的行为和提供材料并交付、转移材料所有权获取对方材料价款的行为,具有可分性。陈某交付案涉洁具产品并转移所有权,同时获得结算对价,系买卖中的卖出行为,其本质属于销售商品的行为。案涉假冒洁具产品安装后其形态和质地未发生任何变化,商标的识别功能没有被阻碍,显现于公众视野中。因此,陈某在包工包料承建工程中,通过包料实际获得案涉产品的对价,其故意使用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的行为,系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所规定的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行为,遂对一审判决、二审裁定理由及法律适用予以纠正。
【典型意义】
在包工包料承揽工程中,承揽人故意使用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行为是否属于销售行为,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存有分歧,有观点认为,承揽人系面向特定对象交付定做成果,不应认定为销售行为。本案从包工包料承揽合同中行为的可分性、销售行为的实质性、被售商品的商标识别功能未被阻碍等三个方面论证,认为陈某虽履行的是承揽合同,但在该类合同中,安装材料获取劳务报酬的行为和提供材料并交付、转移材料所有权获取对方材料价款的行为,具有可分性,且获得结算对价,系买卖中的卖出行为,其本质属于销售商品的行为。同时,案涉假冒洁具产品安装后其形态和质地未发生任何变化,商标的识别功能没有被阻碍,显现于公众视野中。其行为属于商标法及刑法中的“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行为。
二、罗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案
【案例索引】
一审: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22)渝0112刑初413号
二审: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2)渝01刑终487号
【基本案情】
2012年以来,被告人罗某伙同他人成立某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并组建了售假犯罪团伙,长期通过网络平台销售国际奢侈品牌的箱包、饰品及钟表。罗某等人或直接通过快递将货物发给客户,或先将货物发往东莞仓库,由东莞发往香港,再从香港发给客户,向客户制造是海外发货的假象。2019年6月20日,公安机关在罗某等人位于重庆市渝北区的仓库内现场查获假冒未售出的箱包、饰品等货值金额1 069 259元。在东莞仓库现场查获罗某等人已经售出、发货的假冒箱包饰品,销售金额为434 636元。案发后,同案犯到案,罗某逃往境外,后于2021年6月23日投案自首。
【裁判结果】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认为,罗某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既遂金额认定为434636元,未遂金额认定为1069259元,属于销售金额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故判决被告人罗某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五十万元;对被告人罗某退出的违法所得10万元予以追缴。一审宣判后,罗某上诉认为,一审认定的既遂金额434636元应认定为未遂;本案应适用刑法修正案(十一)修订后的第214条从轻处罚。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认为,刑法修正案(十一)对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修订的目的是加大对侵害知识产权行为的惩戒,并非排除了原规定中“销售金额数额较大”以及“销售金额数额巨大”等入罪情形,该两种情形可以分别理解为新法中“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故在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时,应适用旧法。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既遂的认定,应以买卖双方就特定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达成买卖合意为标准,买卖合意达成后的货物交付及货款支付情况,不影响既遂的认定。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刑法修正案(十一)于2020年12月26日通过,自2021年3月1日起施行,其中将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由销售金额修改为违法所得数额加情节,并提高了法定刑。对于只有销售行为而尚无违法所得的情形,新法与旧法何者处罚较重,存在不同观点。有观点认为,若售假行为尚无违法所得,应属犯罪未遂,根据“从旧兼从轻”原则,应适用新法。本案从立法目的出发,通过对新法中的“严重情节”与旧法中的“销售金额”进行对照阐释,认为应当适用旧法,避免了前述认识误区,进而避免了法律适用错误,为类案提供了参考。同时,本案还属于比较典型的网络售假犯罪行为。相较于传统的售假模式,通过互联网售假过程更为复杂,形式更加多样,确定在哪一个阶段构成犯罪既遂,对于此类案件的准确量刑意义重大。本案通过对网络售假流程的分解,结合民事法律关系中买卖关系的认定,从加大对侵害知识产权行为惩戒力度的理念出发,确定了此类案件认定犯罪既遂的标准。
三、浙江安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与青岛讯极科技有限公司、讯极科技(苏州)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及商业诋毁纠纷案
【案例索引】
一审: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2021)渝0192民初8839号
二审: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2)渝01民终2190号
【基本案情】
2018年2月9日,安谐公司作为专利权人申请名为“一种远光灯持续开起的检测方法”的发明专利,2020年7月14日获得授权公告。涉案图片来自于交警部门利用安装在洛阳市周山隧道由安谐公司提供的“不按规定使用远光灯自动记录系统”拍摄视频自动生成,包括四幅画面。2019年2月13日,安谐公司微信公众号发布《“不按规定使用远光灯自动记录系统”在洛阳启动》文章,该文中使用了涉案图片。
2021年5月14日至5月16日,青岛讯极公司、讯极苏州公司共同法定代表人在“第十二届中国道路交通安全产品博览会暨公安交警警用装备展”中发表题为“科技助力滥用远光灯专项整治”演讲,其宣称:“传统视频型,使用压光找双灯筒技术,学习算法技术,只能举证占比不到64%的双灯筒车型的车辆”,同时其PPT配图与安谐公司“不按规定使用远光灯自动记录系统”自动抓拍生成的涉案四幅图片基本一致。
安谐公司认为涉案照片是其利用自有“不按规定使用远光灯自动记录系统”制作而成,属于功能性作品,依法应受著作权法保护。青岛讯极公司、讯极苏州公司在公开演讲及公众号文章中使用了安谐公司作品,侵犯了展览权、发表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安谐公司请求人民法院判令青岛讯极公司、讯极苏州公司停止侵权、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并赔偿损失。青岛讯极公司、讯极苏州公司共同辩称:涉案图片并非著作权保护的客体,不属于作品,即使构成作品也不属于原告所有,不存在侵犯原告著作权的行为。
【裁判结果】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是特定领域内具有独创性的思想表达。首先,主体维度,涉案图片系由机器设定程序进行自动拍摄产生,机器设备并不能成为作品的创作主体。安谐公司虽为机器设备的生产者及技术参数设置者,但涉案图片系交警部门在实际使用设备过程中产生。涉案图片既未体现安谐公司创作涉案图片的主观意图,也非其实际操作设备产生,安谐公司不能被认定为涉案图片作者。其次,客体维度,照片的非艺术性表达不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中摄影作品的认定范围。涉案图片内容及拍摄目的均为客观复制记载车辆违章场景,拍摄过程未体现机器使用者就艺术创造方面的人工干预、选择、判断,不具有艺术方面的独创性表达,故不宜作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进行保护。
【典型意义】
本案的价值在于,为新技术背景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所引发的著作权纠纷提供了审理思路。新技术的产生与推广将一定程度地影响人们创作的方式,进而影响着著作权保护规则。自动抓拍照片是新信息技术的产物,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创作者是谁”“自动生成内容能否构成作品”。判断自动抓拍照片是否受著作权法保护时,应当考虑主客体两方面:主体维度,以创作意图判断创作主体,进而认定其是否可能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者;客体维度,通过独立创作、个性表达要件判断自动抓拍照片是否构成著作权意义上的作品,对于仅为再现客观场景而形成的自动抓拍图片,因未体现创作者在文学、艺术、科学领域的独创性表达,故不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
四、三之三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与重庆两江新区三之三爱加丽都幼儿园著作权侵权纠纷案
【案例索引】
一审: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2020)渝0192民初11914号
二审: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1)渝 01 民终 10159 号
【基本案情】
三之三文化公司于2003年在第41类幼儿园等服务上核准注册第1984484号“”图文组合商标。2004年,上海三育教育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三育公司)受让该商标。2009年,该商标再次转让给展育企业发展(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展育公司)。展育公司受让该商标后立即授权上海三育公司使用及进行再授权。2018年展育公司申请在第41类幼儿园等服务上注册第34662513号“
”图形商标。三之三文化公司曾以第25类注册在服装外套上的第15532549号“
”图形商标以及对“
”图形具有在先著作权为由,对该商标提出异议,后被国知局驳回。
2018年,三之三文化公司作为著作权人取得两份作品登记证书,作品分别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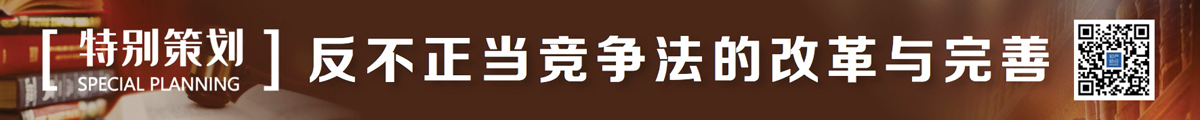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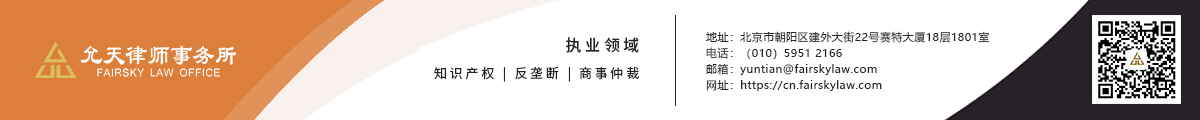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9464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946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