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案”中,原告诉称,被告在其游戏《梦塔防》宣传文案、游戏皮肤中使用原告享有著作权的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中的“哪吒”“敖丙”两个美术作品,侵犯其美术作品的著作权;被告涉案游戏宣传文案、游戏角色介绍使用了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的情节,侵害其电影作品的改编权。杭州互联网法院支持了原告关于被告行为侵犯其美术作品著作权的主张。但对于被告是否侵犯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的改编权,法院认为:对电影作品的保护,是保护其在连续图像形成中的独创性表达,在侵权判定中所要审查的是被告是否利用或复制了原告电影作品连续画面的独创性表达,并不是比对画面背后的故事情节是否一致——这是电影剧本的保护问题。
电影作品的独创性表达体现在连续画面摄制上,而不是体现在电影剧情上。虽然电影作品中也固定了电影剧情或电影故事,但电影故事情节依然属于电影剧本的独创性表达,而不是电影作品本身的独创性表达。判定电影画面是否侵犯电影作品著作权时,应当比对两个电影画面是否一样,并不是比对两个电影故事情节是否一样。对电影情节的保护,应该从电影画面中剥离出来,本质上应该还原为对文字作品的保护。原告主张依据电影作品来保护其著作权,偏离了作品分类的基本规则——将性质完全不同的独创性表达作为同一作品对待。故对原告关于被告侵犯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改编权的主张不予支持。[1]对该判决,双方当事人都没有提出上诉。
但同时,不少法院在类似案件中则是把网络游戏画面当做视听作品,并以视听作品的名义对游戏中的游戏规则、游戏玩法[2]、游戏情节、文字、角色形象、美术形象等提供保护。
此问题既涉及到视听作品著作权范围的确定,也涉及一般作品著作权范围确定的规则,有必要明确。为便于分析,本文以视听作品中的电影作品为例展开。典型的电影,除了连续画面及伴音(或者无伴音)外,还会包含有小说、剧本、美术、音乐、摄影等,与包含了游戏规则、游戏玩法、游戏情节、文字、美术形象等的网络游戏基本类似。因此,类比的问题是:电影作品著作权可以从连续画面延伸至小说、剧本、美术、音乐、摄影等电影所包含的内容吗?
不同类型作品以不同表达来划分,作品的独创性体现在该作品的表达中,并以该独创性表达确定作品的著作权范围,“哪里有独创,哪里才有著作权”,特定作品的著作权范围必须以体现该作品独创性的表达为依据。文字作品以文字形式表现,文字作品著作权依有独创性的文字编排来确定;不配词的音乐作品的基本表现手段是旋律和节奏,音乐作品的著作权限于旋律和节奏;美术作品以线条、色彩等来表达,是否侵犯美术作品著作权,依被诉侵权物是否使用了作品中的线条、色彩来评价。
电影作品的本质特征在于一系列加伴音或者无伴音的滚动的画面,[3]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指出,电影作品是指“由一系列有伴音或者无伴音的画面组成”的作品。因此,电影作品作为综合性艺术作品,虽然也包含有小说、剧本、美术、音乐、摄影等内容,但仅以连续画面为其表达,其独创性亦体现在连续画面中,而不是体现在文字、旋律和节奏、线条及色彩之中。本案判决关于“电影作品的独创性表达体现在连续画面摄制上,而不是体现在电影剧情上。虽然电影作品中当然也固定了电影剧情或电影故事,但是电影故事情节依然属于电影剧本的独创性表达,而不是电影作品本身的独创性表达。”的论述正确指出了电影作品的本质特征及独创性所在,准确区分了电影作品与包含其中的文字作品。
电影作品中的独特情节通常会带来不同的连续画面,但无论如何只有连续画面才是电影作品独创性体现所在。基于电影作品以连续画面为表达,其独创性体现在连续画面中,电影作品的著作权范围自当限于连续画面本身。有观点认为,文字作品以文字形式表现,但著作权法对文字作品不仅仅保护文字形式,还保护体现了独创性表达的情节、人物关系等,即文字作品的保护范围从文字延伸到了非文字;在美国,计算机程序的著作权保护范围,从字面代码延续及字面代码之外的结构、顺序和组织,这些现象表明,不能将作品的定义与作品的保护范围画等号,对电影作品的保护应当从连续画面延及到电影中包含的剧本、美术、音乐。这是对文字作品、计算机程序作品性质的误解。文字作品独创性既可以体现在文字的最终形式上,也可以体现在故事情节、人物关系、人物特征等方面,因此,文字作品的保护范围自然可从文字形式延及故事情节、人物关系、人物特征等内容。
计算机程序之所以被作为作品,是美国运用其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的结果,而包括美国国内法及《Trips协定》都明确规定计算机程序应作为文字作品受到保护。故从源程序、目标程序到程序的结构、顺序和组织都成为计算机程序的著作权范围也就不足为奇了。相反,一位书法家书写了他人一首诗,如果有人复制了该书法家的书法,那么书法家所能主张的只是基于美术作品的的书法线条等,而不能把诗歌内容纳入其权利范围,因为在这里书法家所贡献的只体现在线条等方面。根据同一部小说或剧本不断翻拍电视剧、电影是常见现象,比如围绕金庸的武侠小说所拍摄的电影、电视剧;八十年代八一电影制片厂与北京电影制片厂分别拍摄的电影《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均来自周克芹创作的同名小说,如果因为不同电影、电视剧的情节、人物等相同即认定电影、电视剧的连续画面相似显然是荒唐的。
电影作品的性质、电影作品著作权归属以及电影作品与其他作品的关系可以进一步说明电影作品的著作权范围。
电影通常是由小说、电影剧本、分镜头剧本、摄影、音乐、美术作者以及导演等众多创作者集体创作的综合性艺术作品,是一种复合作品,也具有合作作品的性质,但在哪些创作人员系电影作品的作者问题上,各国有不同的规定。在法国中,剧本作者、改编作者、对白作者、专门为视听作品创作的配词或未配词的乐曲作者、导演为合作完成视听作品的作者。[4]德国著作权法没有确定电影作品的法定作者,但通说认为,只有那些在拍摄工作中或者电影的剪接工作中为图像与声音的衔接作出了贡献并且体现了个人智力创作成果的人,才能取得电影作品的著作权。故属于电影作品作者的有导演、电影摄影师、剪接师、电影音响师等,不是电影作品作者的人包括那些在拍摄电影时所使用的作品的作者,如被拍摄成电影的小说或者戏剧的作者、电影剧本作者、作曲者等等。[5]
我国《著作权法》第17条第1款规定,视听作品中的电影作品、电视剧作品的著作权由制作者享有,但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等作者享有署名权。有观点认为,规定编剧、导演、作词作曲者等享有署名权意味着确认了上述作者合作作者的地位。但相反观点则认为,该条“只是规定了有限的默认的权属规则,并没有暗示一定有合作创作关系存在”“它要求制片者在视听作品中说明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的作者身份,但没有明确他们是否是视听作品的合作作者。”[6]后者有一定的道理,该规定的字面并没有足够清晰明确地表达出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等作者就是电影作品的合作作者的意思;合作作品要求合作作者之间存在共同创作的合意,但对于并非专门为拍摄电影而创作的小说、剧本、音乐、美术的作者来说,通常他们与电影制作者之间并不存在共同创作的合意,故并不符合合作作品的要件。因此,既然编剧、词曲等作者并非电影作品作者,那么电影作品的著作权自不应覆盖非电影作品作者创作的内容。
著作权法对电影作品著作权归属作了特殊规定。作者权体系国家中,德国系“法定许可”的代表。德国法规定,取得电影作品著作权的作者,有义务将电影作品、对电影作品进行翻译以及其他类型的演绎或者改编的排他性使用权许可给电影制片人。为制作电影作品而使用的如小说、剧本和电影音乐在内的作品的著作权不受影响。[7]即电影作品作者原始取得著作权,但视为依法转让给制片人,而那些在拍摄电影时所使用的作品的作者并非电影作品作者,这些作品的权利掌握在这些作者手中。法国法规定,视听作品制作者同作曲者之外的视听作品作者签订合同,即导致视听作品独占使用权转让给制作者。[8]通过推定许可的方式,制片者从剧本作者、改编作者、对白作者、导演等视听作品的合作作者那获得了剧本、对白等在视听作品中的独占使用权,故在法国,剧本等作品著作权由制片者行使,但作曲者除外。
而从我国《著作权法》第17条规定可看出:第一,在我国著作权法中,法律直接规定了电影作品著作权归制作者,因此即使认为编剧、作词、作曲等作者系电影作品的合作作者,但著作权法并没有规定编剧、作词、作曲等作者与制作者共同享有电影作品的著作权,可见,电影作品著作权归属规则与专门规定合作作品权利归属的《著作权》第14条所确定的规则完全不同;第二,电影作品中剧本、音乐等可以单独使用的作品的著作权不属于制片者,而属于剧本、音乐等作品的作者。司法实践亦如此操作,在“琼瑶诉于正案”中,法院支持剧本作者琼瑶有权主张其剧本的著作权;在“大头儿子案”中,法院认定:动画片的人物造型本身属于美术作品,其作者有权对自己创作的部分单独行使著作权。[9]在“奥特曼美术形象案”中,法院认定,迪迦奥特曼角色形象构成独立于影视作品、可以单独使用的作品。不能简单地或当然地推定这个单独作品的著作权由影视作品的著作权人享有。影视作品的著作权人应举证证明其享有奥特曼美术作品的著作权。[10]在不少涉及网络游戏著作权案件中,法院支持了著作权人单独就文字、美术、图形(地图)作品主张的相应权利。因此,不论是著作权法的规定还是司法实践都肯定了电影作品的著作权不能延伸至电影作品中可以单独使用的并由他人享有著作权的作品。
电影作品通常基于已有小说、剧本改编摄制,因而事实上属于一种演绎作品。但在我国《著作权法》中,专门规定演绎作品的第13条并没有提及电影作品,第17条也没有明确电影作品是否演绎作品。那么电影作品是否具有演绎作品的法律地位、是否适用双重权利、双重许可的规则呢?《伯尔尼公约》第14条规定,文学艺术作品的作者享有授权对其作品进行电影改编和复制,以及发行经过改编或复制成的作品的权利;由文学艺术作品派生的电影作品,如果改编成其他艺术形式,除需要经电影作品的作者授权外,还需要经原作作者授权。[11]可见,《伯尔尼公约》将基于已有作品摄制的电影作品当做了演绎作品,也确认了对电影作品的改编利用应遵循双重许可规则。《伯尔尼公约》是我国著作权法制定时重要的借鉴资料。
我国《著作权法》第17条中“视听作品中的剧本、音乐等可以单独使用的作品的作者有权单独行使其著作权”的规定,也给了做出类似《伯尔尼公约》上述解读的空间。司法实务亦采纳此观点。在“白先勇诉某公司案”中,原告许可上海电影制品厂将其小说《谪仙记》改编拍摄成电影《最后的贵族》。某公司仅经过电影制片者许可,即将电影改编为同名话剧并公开演出。法院指出:上海电影制品厂对其拍摄的电影《最后的贵族》享有著作权,但该电影属于演绎作品,将该演绎作品改编为另一种作品形式即话剧并演出,需要同时取得原作品和演绎作品著作权人许可。因此,某公司侵害了原告的著作权。[12]电影作品与已有作品属于演绎作品关系、对电影作品亦适用双重许可规则进一步说明,小说、剧本等已有作品的著作权属于小说、剧本的作者,电影作品的著作权不应侵入这些作品的权利范围。
综上,视听作品的本质在于连续画面,网络游戏具有连续画面的特征并具备视听作品的其他条件的,属于视听作品;构成视听作品的网络游戏画面与游戏规则、游戏情节、角色形象、美术形象是不同性质、不同类型作品,其权利保护期、权利的限制、权利的归属亦不同;作为视听作品的网络游戏著作权仅及于游戏画面,不宜延伸至游戏规则、游戏玩法、游戏情节、文字、角色形象等内容;把网络游戏画面当做视听作品,却又以视听作品为根据为游戏规则、游戏情节、文字、美术形象等提供保护,似乎不符合视听作品的性质,也混淆了不同作品及其权利归属的关系,应当慎重。不少学者对此早有论述。崔国斌教授指出:“在没有文字作品的情况下,将视听作品或游戏画面背后的故事情节(游戏规则)作为戏剧作品或文字作品来保护。”[13]张伟君教授认为:“对游戏规则、游戏情节的保护,本质上也应该还原为对语言文字作品的保护,这样才能准确地加以分析,才能更清楚地判断......。”[14]本案判决关于“判定电影画面是否侵犯电影作品著作权时,应当比对两个电影画面是否一样,并不是比对两个电影故事情节是否一样。对电影情节的保护,应该从电影画面中剥离出来,本质上应该还原为对文字作品的保护。原告主张依据电影作品来保护其著作权,偏离了作品分类的基本规则——将性质完全不同的独创性表达作为同一作品对待。”的论述正确区分了视听作品与视听作品中的其他作品的关系,遵循了作品独创性体现与作品著作权范围确定的基本规则和基本原理,值得称道。
注释:
1.参见杭州互联网法院(2020)浙0192民初9817号民事判决书。
2.目前对游戏规则、游戏玩法是否构成作品存在争议。同济大学张伟君教授认为,游戏玩法规则属于思想范畴,无法获得著作权法的保护。参见张伟君:《呈现于视听作品中的游戏规则依然是思想而并非表达》,《电子知识产权》,2021年第5期。
3.李明德:《关于短视频保护的几个问题》,《知产财经》总第6期。
4.参见《法国知识产权法典》L113-7条第2款。
5.【德】M雷炳德著、张恩民译:《著作权法》,法律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198、200页。
6.同注释4。
7.参见《德国著作权法》第89条第1、3款。
8.参见《法国知识产权法典》L132-24条第1款。
9.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4)三中民初字第7916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杭知终字第357号民事判决书。
10.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鄂民三终字第23号民事判决书。
11.刘波林译,《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指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第66、67页。
12.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4)沪二中民五(知)初字第83号民事判决书。
13.崔国斌:《视听作品画面与内容的二分思路》,《知识产权》2020年第5期。
14.张伟君:《从电影作品概念看电子游戏”类电影“保护》,在2019年11月18日第四届自贸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研讨会上的演讲。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知产财经立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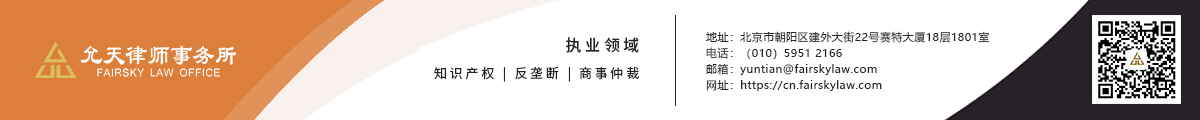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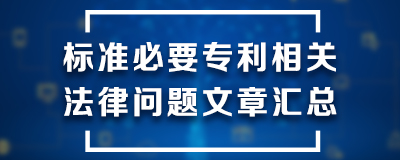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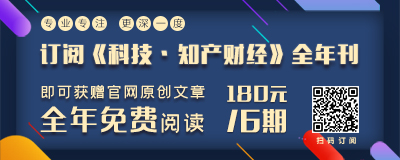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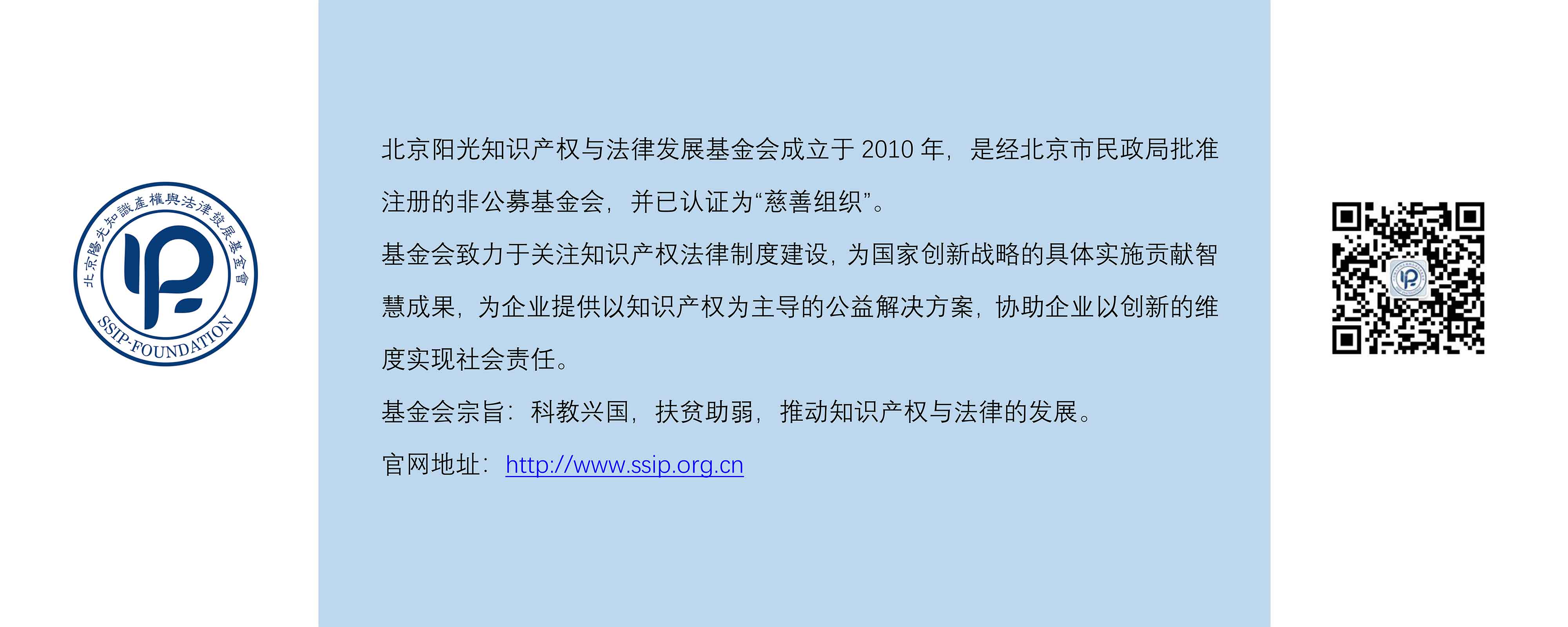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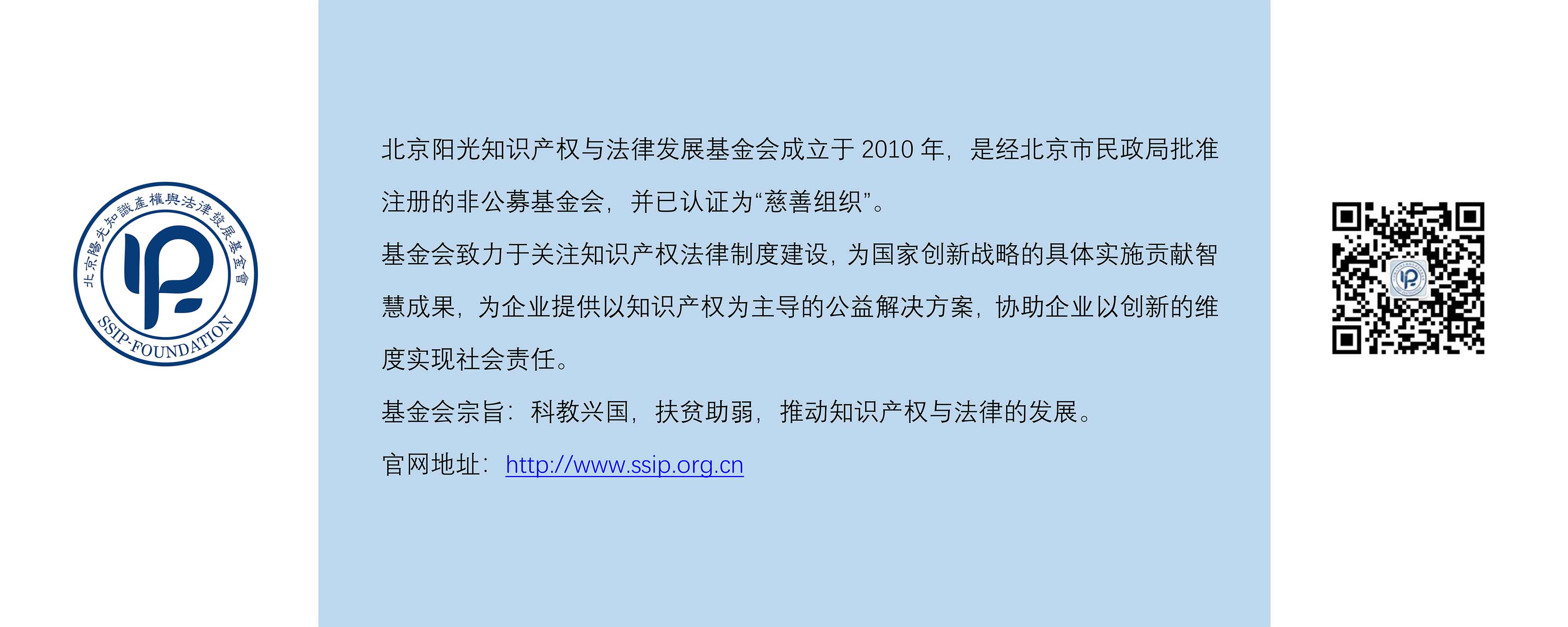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9464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946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