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暨南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在番禺校区知识产权大楼举办“电子游戏侵权判定疑难问题”学术研讨。暨南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教授徐瑄作会议总结,以下为速录内容。

徐瑄:我先总结一下技术调查官和鉴定问题,然后再对整个会议做总结。
技术查明机制在知识产权审判中是一项辅助措施。我们的技术调查官是帮助法官查明事实的。我们的司法必须建立在事实查明的基础之上,才能做价值判断。不顾事实,闭着眼睛瞎编,编一大套概念,最后大家都读不懂,这样下的判决肯定就不科学,也不规范。不仅如此,我觉得可能造成的混乱要多得多。
我们的法律一定要基于事实而作出法律责任和法律价值的分析。我的价值观是:无论做什么样的价值判断,离开事实,我们就连判断的机会都没有了。
为什么我们要组织“电子游戏侵权判定疑难问题”研讨会?大家知道我做基础理论做了很多年,我发现电子游戏领域太多问题了,就像刚才永忠教授讲的,我们看任何一个电子游戏案件判决书,什么是“换皮”、什么是“游戏规则”“游戏玩法”,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每个法官都可以有自己的见解,写得满篇都是,这个看起来,已经偏离了司法裁判的轨道。
我们的法官不是应该把纠纷发生的事实说得简洁明白,然后将责任分配清晰吗?怎么会一个判决书我读了三遍没有读完,还读不懂,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就需要我们认真地去讨论,并尽快地达成共识。所以熊教授的观点我是同意的,即法律运行成本高,大部分时候我们是没有共识的。我们连每个人说出来的法律都不一样,怎么可能让法官出一样的判决?连法官都判得不一样的判决,又怎么可能让司法统一?
现在商家特别热衷这个游戏。游戏产业迅速发展,成为数字内容产业的重要增长点。这个产业蓬勃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特别是这三年疫情给这个玩游戏提供了巨大的暴利空间,所涉及的利益规模非常大。游戏产业也是中央策划里面要求出海的一个产业,因为技术出海太难了,而游戏产业是能够走出去的。大家会觉得玩游戏这个事是没有任何可强制性的,喜欢玩游戏的人玩的不亦乐乎,不喜欢玩的就不玩,游戏是有这么一个属性的。这样一来,我们怎么规制游戏就变得很重要。
我们讨论这么多的问题,为什么最后一个环节留在游戏司法鉴定和技术查明?我发现,我们所有文章,包括司法探讨、一些研讨会其实忽视了游戏作品的生产过程。我们大部分时候把这个作品当成是一个自然人的作品,然后就用我们之前的知识产权法,甚至是积累了几百年的司法规范和严格的司法条件来思考。然而在针对一个具体的特殊情形时,例如将电子游戏作为新的作品进行保护,我们传统的著作权法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行的,在哪些程度上是不可行的,我觉得我们回到事实层面再来研究可能会更好。
事实上,只要去看任何一个大的游戏公司,了解他们公司的结构,就能明白游戏换皮对于游戏企业发展是不可行的。如果一个游戏公司仅有七八个人、三四十个人,那么这个公司做出来的游戏可能是换皮的,因为它创作不出来一款新游戏。如果一个游戏公司的经营团队超过了两百人,它绝对不会换皮,因为风险太大了,两百人的生死都在这个游戏作品里,那这个公司必然要进行创作使其游戏与其他人不同才能安全,而不是选择换皮。
我们的著作权法给每一个人模仿、学习和创新都提供了足够的机会。在了解了游戏生产创作过程后,我们可以不把游戏换皮当成是一个法律问题。这其实是产业的问题,生产能力的问题。
我希望,当我这个声音发出去之后,所有换皮的人停下来,这个行业是值得我们去长线投资的。按照目前这个行业的发展,选择做长线投资,一步一个脚印地把整个生产线建构起来,这个产业可以实现长远发展。
为什么?我告诉大家,游戏里面容纳了人类一百种的智慧。到现在为止,这个智慧用的空间是很少的。如果我们更多的人融入到这个产业里面来,我们人类彰显自己智慧的机会就多得多。娱乐时间玩游戏,在学习游戏的过程中长智慧、长技能,这个不就是未来人类生活可以预见的一个正常生活方式吗?
因此,我的结论是:游戏是个制品,是多个自然人集体创作出来、更近进集体智力创作的制品,不是普通作品,也不是普通制品。茶歇时有专家也说了,将游戏放在产品的角度,用制品的方法去规制游戏产业的发展可能更好。这跟我们目前讨论的AI定义这一问题很像,即AI是制品还是怎么来定义有待探讨。我个人认为,一个游戏如果是由这么多人集体创作出来,那么它就是一个作品,因为整个游戏团队要像自然人一样,投入特别多的智力、时间和承受特别多的精神压力才能把它创作出来的集体智力制品。
然后,不要以为游戏从创作到完成这个程序代码的数据包,拿着数据包去进行版权登记就完成了。游戏真正的风险是当它上线的时候。不要以为今天这些赚了钱的游戏大厂,有多少玩家玩它的游戏让它赚的盆满钵满。实际上,创作出来的游戏作品,上了线如棉花丢到大海的比比皆是。所以我们必须考虑产业的发展,考虑维护一个正常的竞争环境,必须给创作者给予足够的尊重和保护。这就是我们著作权法有史以来到现在还要坚持的人类最伟大的价值观。谢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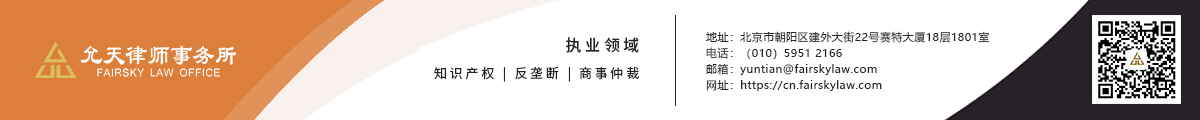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9464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946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