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闫伟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副庭长
近年来,知识产权领域恶意诉讼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数据显示,全国法院受理的因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一审案件数量从2022年的74件增加到2023年的152件,同比增长105.41%。知识产权领域的恶意诉讼属于较为严重的不诚信行为,造成诸多不良影响。基于此,湖南省法学会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和知产财经于3月30日在长沙举办“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司法规制”研讨会,共同探讨和研究企业遭遇的知识产权恶意诉讼困境及解决之道,以期为行业良性有序发展贡献力量。会上,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副庭长闫伟围绕“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司法程序性制裁”话题进行主题演讲,知产财经对其主讲内容进行了整理,以飨读者。
非常高兴能跟各位实务界的同志、专家教授、同行一起交流“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热点问题的相关思考。我的发言主题是“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司法程序性制裁”,涉及到对于知识产权恶意诉讼案件法院能否施以民事制裁的问题。
前面的学者专家发言都比较集中在恶意诉讼的构成,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也是讨论能否施以司法程序性制裁的前提问题。要施以制裁,前提必然是法院已经认定构成恶意诉讼。如果我们认定知识产权恶意诉讼存在,法院能够在什么程度上进一步发挥司法能动性?如何在法律框架下推进司法政策,包括最高法院提出的有力规制知识产权恶意诉讼、虚假诉讼?实际上,在目前,采取司法程序性制裁还处于一个探索阶段。
刚才实务界代表提出的实例里提到,有些权利人起诉时甚至连权利本身都没有,他维权的基本权利基础来源时间远远早于权利实际获得授予的时间。这种虚假诉讼在当前知识产权诉讼和民事诉讼的法律框架下是有明确规定的。我今天想和大家汇报在这种情形之外的,另外一种比较狭义的恶意诉讼,也就是原告明知自己提起诉讼的权利基础是具有不正当性的。以长沙中院判决的“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长某新贸易有限公司诉长某新科技股份公司商标侵权案”为例,原告在起诉时有商标权,但是在诉讼过程中,商标被认定无效,后面很多环节,包括复审或行政诉讼,都还没有进行。法院在这个案件中认定原告提起诉讼时应当知道他申请这些商标权时的主观意图就是不正当的,包括原告提起诉讼的目的是不正当的。这种情况下,除了通过民事诉讼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分析和认定之外,法院还能不能够、有没有必要以及有没有依据进一步施以程序性制裁?我从三方面来讲这个问题:
一、司法程序性制裁的必要性?
关于必要性的问题,罚款是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一种方式。采取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情形,主要是针对当事人在民事诉讼期间,诉讼行为妨害民事诉讼秩序。价值在于维护诉讼秩序,促进诉讼诚信、公平、效率。有一些质疑观点认为,狭义的恶意诉讼中,受到损害的是被告的权益,而不是直接对诉讼程序进行妨害。“恶意”诉讼针对对方当事人,侵害他人的实体权利,似与妨害诉讼秩序本身的关联性不够紧密?对此,我个人的认识是以下三方面:
一是原告提起这种类型的恶意诉讼时,实际是对诉讼权利和诉讼程序的滥用。因为他明知道自己本身不具有正当的合法权利、实体权利基础,但是认为法律赋予了原告去起诉,去要求法院保护自己的权利。这种浪费诉讼权利,进而滥用诉讼程序的行为,与民事诉讼法的诚实信用基本原则相悖,损害了诉讼程序正义、诉讼诚信的基本价值。
二是虚假诉讼与恶意诉讼,均表现为利用正当的诉讼程序获得不正当利益,对诉讼秩序的破坏无实质区别。法律规定明确的是可以对虚假诉讼行为人施以民事强制措施制裁,甚至可以入罪。所以,从类比的角度来说,可以参考虚假诉讼。
三是进一步结合司法政策的考虑,相对于普通民事诉讼领域,知识产权恶意诉讼在国家创新战略层面具有更大危害性,损害了知识产权的秩序。无论是从政策的、国家的还是从诉讼的程序正当的价值层面来说,我认为还是有必要在一些能够准确认定的案件中去积极发挥司法的能动性,实施司法制裁。因为司法制裁基于其强制性,其效率、震慑力更为明显,有必要发挥司法程序性制裁的价值功能。
基于上述考量,对于长沙中院采取了罚款这样一个民事制裁的的司法处理思路,我个人认为是可以的。
二、司法程序性制裁的依据
目前司法政策一般是把虚假诉讼和恶意诉讼并列的,努力采取多种举措规制恶意诉讼、虚假诉讼。在这个层面上,可以直接引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五条,这一条最近的两个版本有一点区别,最新的版本(2023年修正,2024年1月1日实施版本)明确列举了两种情形:一是“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二是“当事人单方捏造基本事实”。这两者之外的其他诉讼能否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专家学者的大部分观点是比较一致的,认为这两种情形更多是“虚假诉讼”类,未明确指向狭义的“恶意诉讼”情形。恶意诉讼情形能否适用这条法律作为依据?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商标法》第六十八条第四款规定“对恶意申请商标注册的,根据情节给予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对恶意提起商标诉讼的,由人民法院依法给予处罚。”这一款对行政处罚的规定非常清楚,但对人民法院的处罚规定比较模糊,没有明确规定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处罚,具体的处罚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我个人认为,这里的处罚是一种惩罚性措施,并不是民事领域的一种民事责任,民事责任是平等的主体之间的责任,没有处罚的问题。第三个问题,《民事诉讼法》中没有民事处罚的概念,这个处罚是什么?我只找到一个依据,可能对应的是《民事诉讼法》第十章“妨害民事诉讼的民事强制措施”,这样的强制措施本身也包含惩罚的价值。《商标法》并没有明确指向应该处以什么样的处罚,从商标法的立法价值和目的来看,主要关注商标的法律秩序、法律制度问题,没有涉及对诉讼程序的适用问题。所以我认为,如果单独适用《商标法》第六十八条第四款,也不是那么完整。
三、探索、思考和建议
当前法律并没有针对适用于比较狭义的恶意诉讼的规定,那么,应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需要去找依据。依据怎么去找?仍然要从相关法律制度中寻找。我个人目前是倾向于结合《商标法》第六十八条第四款、《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以及《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相关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是一个原则性的条款,是关于民事诉讼的诚实信用原则的条款,没有具体的法律后果。我的思路是,恶意提起商标诉讼是一种违背民事诉讼的诚信原则、妨害民事诉讼程序的行为,人民法院依法有权予以处罚,也就是把两个法条的内容交叉结合,最后采取民事强制措施。
谈一下我在这个问题中的一些思考:
第一,司法制裁在恶意诉讼的规制机制中是补充位置。人民法院维护被告的权益给予赔偿之外,是否还要做一点什么事情,这是人民法院的主动行为。司法制裁行为不是根据当事人的主张或申请而提起的,而是法院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有必要去行使自己的公权力。
第二,对恶意诉讼的规制更多应当遵从制止民事侵权的基本思路,因为对于被告来说,其需求是消除恶意诉讼对其影响,若恶意诉讼导致损失,则予以救济,而不是法院必须要采取措施去制裁。
第三,适用恶意诉讼的制裁措施,应当秉承谦抑、审慎的态度。充分考虑与应保护知识产权强度比例相适,避免将民事侵权事项异化为公权力实施。除了在认定是否恶意时要谦抑和审慎外,即便认定了是恶意诉讼,是否施以民事制裁,仍然应当保持这样的态度。并不是说一旦认定这个行为是恶意诉讼就一定要施以民事制裁,还是要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去进行认定和处理。我认为,有必要考虑具体案件中的知识产权有多大的保护强度,如果保护强度足够大,可能需要通过对原告施以司法制裁来彰显法院的司法态度,要避免把民事侵权的问题异化为公权力的问题。
最后,探索运用成本杠杆的制裁方式来规制恶意诉讼。恶意诉讼当事人如认识到败诉风险,拟申请撤诉或者通过减少诉讼标的额的,不予准许。提出这个观点是因为有些案件中,恶意诉讼的原告考虑到自己不太容易受到保护,可能会败诉,就提出要把诉讼请求的标的额大幅降低,从1000万元降低到100万元。这个降低的过程对原告来说就是一个减少诉讼成本的过程。能否允许原告降低诉讼成本?我个人认为,如果当事人申请撤诉或者通过减少诉讼标的额来降低诉讼成本,可以不予准许。当然,这同样建立在认定这个案子具有非常大的主观恶意并有惩戒需要的基础上。
基于上述思考,我有以下几个建议:
第一,完善民事诉讼法关于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的规定,将滥用诉讼权利、滥用诉讼程序的“恶意诉讼”纳入“妨害民事诉讼行为”,明确对恶意诉讼原告采取民事强制措施的具体法律规范。个人认为,当前法条规定仍然存在很多没有明确的问题,可能更多的是通过司法政策的驱动,但是真正要得到有力支持还是要制定更加明确的法律规范。
第二,完善民事诉讼法对于恶意诉讼可以不准许撤诉或不准许减少诉讼标的额的法律规范。目前,民事诉讼法有规定,原告申请撤诉,人民法院可以审查是否准许。但是当事人认为允许撤诉是处分原则的体现,当事人有诉讼权利,这种权利是可以处分的,法院不准许撤诉就是违反了基本的处分原则。所以需要进一步明确这个问题,对法院的司法提供更为清晰的导向。
第三,是知识产权诉讼特别程序法的起草。从民事诉讼法的角度去解决这个问题的难度是比较大的,因为知识产权的恶意诉讼相对普通的民事恶意诉讼具有独特性,这一问题亟待解决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如果能够灵活通过知识产权诉讼专门法律解决问题,可能是一个更加快速的渠道。
以上是我与大家分享的内容,感谢大家!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知产财经立场)
查看更多知识产权精彩内容,请浏览知产财经官网:www.ipeconomy.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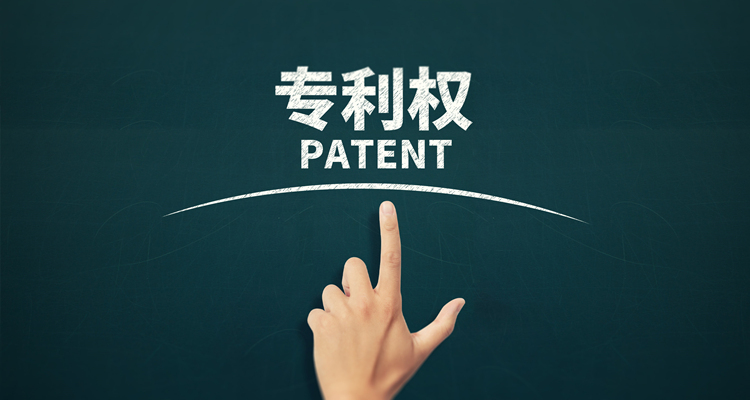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9464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946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