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陈兵 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 南开大学竞争法研究中心主任
7月17日,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的指导下,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联合知产财经全媒体在上海举办了“互联网不正当竞争原则条款适用实务论坛”,来自知识产权领域学术、司法、产业界近200位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共同探讨相关法律和实务问题。南开大学法学院陈兵教授围绕“互联网竞争行为正当性分析框架检视——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下数据爬取行为适法性为例”进行了主题演讲,知产财经对其演讲内容进行了整理,以飨读者。
如今,数据已经成为互联网经济下半场的重要原料,中共中央以及全国各地,都围绕数据产业的发展以及数据要素如何构建市场出台了许多文件。那么,如何将这些文件落到实处就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
一、竞争法下如何看待数据爬取
目前,“数据爬取”这个概念是非常火爆的,笔者个人认为数据爬取是以网络爬虫(Web Crawler)为核心技术,基于一定的规则,从其他网站自动抓取符合其要求的数据,这是一个技术中立的概念。数据爬取技术具有竞争中性的一面,使用该技术并不必然构成违法。
实际上,在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是比较维护数据持有者的利益的,因为从原始数据到派生或者衍生数据,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那么如何看待这样一个商业数据,尤其是经过数据企业的抓取分析之后,它的利益应当如何保护是需要进一步考虑的。
但是,目前围绕数据爬取竞争法司法适用是存在不同的做法的,不仅在国内如此,在国外也是如此。比如近期发生的两个案件,一个是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其是支持被爬取方的,法院一审判决字节跳动利用技术手段抓取新浪微博内容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另外一个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其是支持爬取方的,人民法院认定百度通过robots协议限制360搜索引擎抓取网页内容构成不正当竞争。其实,国外目前也是如此,比如,hiQ这个案子目前还没有终结,只不过法院发了一个禁令,支持了数据爬取方hiQ,理由是hiQ抓取的为领英公开数据,而领英未能证明hiQ侵犯隐私。
目前,围绕这类案件主要存在一个逻辑,首先,要看这个权利是否存在,无论这个权利是动态的还是静态的,是以权利的形式,还是以权益这样的应急性的形式来存在。今年有的地方高院草拟了《关于互联网领域新类型竞争审判指引(征求意见稿)》,目前尚未正式颁行,在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过程中,有学者和实务专家提出,法院所出的指引不应该对流量进行确权,也不应该对数据进行确权,因为司法机关没有这样的权利,要确权也应该是通过立法,如此一来,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在遵循立法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逐渐改善甚或创新相应具体立法的现象,特别是在现行立法就互联网领域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新产业等规范缺乏的场景下,司法的守正与创新就显得格外重要。目前,有的法院在审理涉数据爬取行为的竞争纠纷案件时,正在从权利本位逐渐转化为行为本位,尤其在数据领域格外明显。数据的生命在于流通,我们现在所谓的数据封锁、数据孤岛、信息茧房等等,都在威胁着数据要素的流通与发展,在数据爬取领域,竞争法是存在适用的空间的(这里的竞争法不仅仅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也包括反垄断法),那么如何通过竞争法的适用对此问题进行规制尚有待明晰。
二、涉数据爬取行为竞争法适用现状
我们筛选出32份判决书,其中有12例案件涉及两审,即24份判决书,余8份判决书,各涉及8起案件,即共20例案件涉及数据爬取纠纷,均为反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其中:(1)3例案件同时适用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和第12条,具体包括2例案件适用的是第2条及第12条第2款第4项,1例适用了第2条、第12条第1款以及第12条第2款第4项;(2)1例案件仅适用了第12条第2款第4项;(3)16例案件,均仅适用了第2条。 数据爬取方行为被判定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案件17例 ,认定不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有2例,1例因原告(数据被爬取方)举证不能,法院未支持其主张。
由此可见,在整个适用过程中,实际上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也就是一般条款的适用是居多数的,专条的适用是比较少的,笔者跟一些法官就此问题进行过交流,之所以存在目前的适用现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的适用性非常强,如果适用第十二条等,由于对“技术”本身的解释,以及相关具体行为的认定要件,比如,“恶意”、“不兼容”、“破坏”、“妨碍”等都需进一步细化。
目前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其实存在三种不同的分析思路:
第一种模式是比较简单的,就是考察行为和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实际上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民事裁判的思维。
第二种模式实际上与第一种模式差不多,只不过是首要去比对一下我们现行的互联网专条是否对此类竞争行为作出特别规定,如果没有,再回到第一种适用模式。在这一过程中,受案法院还会依据比例原则,考虑多益的平衡问题,但是总体思路仍然是私法审理的逻辑,坚持“行为—法益”及其因果关系的考察。
第三种模式是我们希望能推动的,即我们先把互联网产品上的竞争关系抽出来,
实际上我们发现,在整个法院审理过程中,法院都会去分析竞争关系,无论是直接的竞争关系,还是间接的竞争关系,那为什么要寻找这个关系呢?如果法院不找这个关系,他就无法锁定权利或权益的主体以及权利或者权益的存在,那么也就无法认定涉案行为是否是正当的。
笔者认为,对行为正当性的判断实际上应当是对竞争损害的判断,所以说目前第一种模式是民事裁判的思维方式,第二种模式虽然加入了比例原则,但是也仍然是保持了一种司法的克制主义。第三种模式则是将司法往前推动。目前在反垄断法的修订草案中,就有学者想把鼓励创新写到反垄断法的第一条,当然也有学者反对,因为现行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已经涵盖了公平竞争、经济运行效率、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这些内容已经非常丰富,如果再要把鼓励创新放进去,将导致内容过多了。
实际上,知识产权法要鼓励创新,要保护创新,要进行授权,要进行赋权,那么,竞争法应该是什么样的?它应该是一种行为法,就是说我不对你赋权,但是我要对你的行为产生的损害进行规制。
在实践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关于商业道德的判断,实际上现在很多法院都在聚焦于如何解释商业道德,商业道德往往实际上是在位的平台企业通过很长时间的实践,进而形成的一个商业道路,当然也涵盖整个行业所公认的道德,但商业道德是在不断变化的。有时候商业道德也面临挑战,有的中小企业提出,如果维护商业道德,那么创新发展怎么办?这个时候就引发了关于数据爬取的问题,数据到底能不能爬取,能爬取到什么程度?
三、数据爬取行为的竞争法法理解析
如果说采取严格保护,那么对于中小企业而言,他们获取数据的渠道会越来越窄,有人提出,放任企业对数据进行爬取,爬取之后再寻求判罚,但是判罚的金额,可能跟企业爬取所获得的利益之间根本不成正比,这个也是需要进行博弈的。所以可以考虑从行为的角度来判断可责性的问题,那么如何来判断行为的可责性,其实就涉及到比例的问题。
关于比例问题,笔者认为,就像主播跳槽这类问题,其实可以通过市场的自我调节,进而寻求竞争秩序的恢复。至少不需要我们想方设法去介入它,可以通过合同法,甚至通过其他法律也是可行的。
目前数据爬取行为对市场竞争的影响存在负面影响与正向激励两种,但是我们更多是关注负面效应,比如侵犯隐私权、财产权、知识产权等以及搭便车行为,但是对于正向激励,可能考虑的比较少。
2020年7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突破性判决将可能对数据如何进行市场化竞争的判别带来影响。
谈及数据爬取可能涉及的垄断问题,主要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就是实施爬取,如谷歌对新闻出版商提出要求,新闻出版商必须接受让谷歌爬取数据,且要求是免费的,这其实是以“自愿”为表象,实则是一种强制、限定交易的行为。第二类就是拒绝爬取,如领英和HiQ数据之争中,HiQ是一个数据分析公司,它就希望使用领英的公开数据,但领英采用技术措施限制HiQ获取其公开数据。此时,领英可能构成了一个必需设施,而对于HiQ而言,公司要进行发展,要创新,就必须要获得这些数据,当然这只是从理论上的一种分析,能不能构成必需设施,仍需进一步判别。。
四、对数据爬取行为的竞争法适用框架
对于数据爬取行为的竞争法适用框架完善的问题,笔者指出,首先应提高创新要素在竞争法分析中的地位,一方面,可将创新损害视为一种衡量数据爬取行为竞争损害的标准。另一方面,创新效益也可成为一种可抗辩数据爬取竞争损害的积极效果,行为正当性表现。
其次,应构建多元多维度的利益权衡机制。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把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放在前面,接下来是其他经营者或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笔者认为这样的立法顺位是非常清晰的,但是在现在的思维框架下,我们通常会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法更多强调对竞争者利益的保护,反垄断法则更多强调对市场竞争秩序的保护,但是我们现在正在转向,就是把创新效率作为一种抗辩,如果爬取行为能够增进创新,创新效率可以作为一种动态效应,那么对于这种行为就需要进行审慎的评价。
在未来的审理过程中,我们可以考虑什么?笔者认为,不妨考虑引入经济学的分析,将判决做得更加具有前瞻性。因为一个好的判决,它可能带动一个产业,但是一个不好的判决可能会遏制整个产业的发展,所以这个是需要我们意识到,产业、行业跟市场不是同一个概念,市场不是工业概念。在司法实践中,可以考虑去分析一下,如果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那么对于正当性的判断,应当构建一个多元的状态。不少人提出引入比例原则,比例原则其实是考量行为的适当性、必要性以及进行相应的利益衡量,换言之,就是判断行为是不是适当的,是不是一定要通过爬取,才能够获取特定的创新成果等等。
结语
面对数字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业态、新技术、新应用及新模式,司法机构和执法机构需保持审慎的态度,避免对市场竞争和创新行为造成不当干预。数据爬取行为对市场竞争秩序和消费者利益也可能具有积极效果,并不是所有的数据爬取行为都应当被视为违法。只有进行多元多维度的价值权衡,才能在正确评估数据爬取行为合法性的同时,让真正对竞争秩序、技术创新以及消费者有利的行为在市场中得到健康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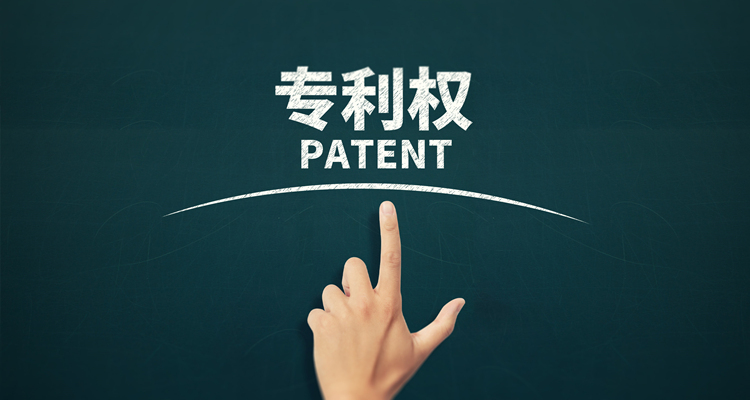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9464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946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