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武汉到印度新德里,再到如今的德国慕尼黑,小米与交互数字之间就标准必要费率的纠纷愈演愈烈。慕尼黑第一法院针对小米禁诉令(ASI)做出了反禁诉令(AASI)裁决。本裁决在论述管辖权等程序问题外,主要从执行期间、首次侵害危险的判断等方面说明了禁令救济何以必要,这在标准必要专利费率裁决诉讼全球化的背景下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本裁定由中国政法大学李扬教授指导即将于今年九月攻读其硕士研究生的四位同学翻译,授权知产财经发布。本译文仍有许多不成熟之处,如有错误,望各位读者不吝赐教、批评指正。(同译文附上裁定原文,供读者参考)
本文由中国政法大学谭梦溪-骆任佳-胡迪菲-陈天佑翻译。
慕尼黑第一地方法院2021年1月28日判决
执行部分
2020年11月9日慕尼黑第一地方法院的临时禁令得到确认。
[…]
事实部分
该禁令的第一原告是一家电信服务研发公司,其公司注册地位于美国特拉华州的威明顿。它是交互数字集团(下简称“IDC”)的一部分(目前与IDC旗下的任一具体公司都没有关联),其母公司为交互数字股份有限公司(和该电信服务研发公司的注册地相同)。它在德国(Exhibit AR1)和世界范围内拥有大量知识产权,特别是在第二代(GSM)、第三代(UMTS)、第四代(LTE)和第五代(5G)移动通信领域(Exhibits AR1和AR2)。根据该公司的声明,它以FRAND条件授予所有感兴趣的公司使用这些专利的许可。它实质性地参与了相应的移动通信标准的制定。
该禁令的第二原告同样位于美国特拉华州的威明顿,也属于IDC,同时也在德国拥有众多此类知识产权(Annex AR 17)。
禁令的被告均属于X.集团(目前其不隶属于X.集团下的任一公司)。X.集团是一家中国电子产品制造商,自2020年初以来,它一直是全球第三大智能手机制造商。第一至第三被告均在中国注册公司,其中第二被告注册在武汉,它们均是注册地在开曼群岛的第四被告的间接全资子公司。第四被告还通过X.科技德国股份有限公司在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和贝尔特海姆(Beltheim)设有分公司。此外,第四被告还有两个在中国的送达地址(北京和香港)。
据禁令原告称,IDC七年来一直试图与X.就其关于3G和4G技术的标准必要专利组合达成FRAND许可协议,但始终无果。最近一次是在2020年2月,IDC提供了许可报价,但未能成功达成许可协议。
随后,发生了以下事件:
2020年6月9日
X.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针对IDC提起诉讼,要求裁决一个适当的全球标准必要专利包费率,[…]。
[…]
2020年7月29日
IDC在印度新德里高等法院针对X.提起专利侵权诉讼,并申请了禁令救济,以迅速限制其所指称的持续专利侵权行为[…]。
[…]
2020年8月4日
鉴于IDC的上述行为,X.针对IDC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行为保全(禁诉令=ASI)。
[…]
2020年9月23日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颁发如下禁诉令[…]。
[…]
2020年9月29日
IDC向新德里高等法院申请了针对X.的反禁诉令(AASI),内容如下[…]。
[…]
2020年10月30日
禁令的第一原告向慕尼黑第一地方法院申请授予以下临时禁令(BI.1/30):
由于剥夺了专利权人的法定救济权利,被告不得申请执行于2020年9月23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获得的禁诉令((2020)鄂01知民初169号之一)或采取其他司法或行政措施,以图直接或间接禁止申请人或ID集团的其他关联公司就其德国标准必要专利在德国提起侵权诉讼,这一禁令特别包括[…]。
[…]
2020年11月9日
慕尼黑第一地方法院在被申请人没有事先听证的情况下,以命令的方式颁发了以下临时禁令(BI.56/62):
1.被告若违反临时禁令,将面临最高25万欧元的罚款或最高6个月的拘留(若罚款无法缴清,被告仍会面临监禁),拘留或替代拘留由每起案件的每个侵权行为之各自被告的授权代表承担。
禁止被申请人执行于2020年9月23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获得的禁诉令((2020)鄂01知民初169号之一)或采取其他司法或行政措施,以图直接或间接禁止申请人或IDC的其他关联公司就其德国标准必要专利在联邦德国提起侵权诉讼,
因此,停止并终止的义务也特别包括:
在本禁止令生效后的24小时内撤回于2020年8月4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的禁诉令申请((2020)鄂01知民初169号之一),或采取其他合适的程序性方式终局性撤销该禁诉令的涉德部分。
禁止继续进行在武汉申请的禁诉令程序,除非该程序是为了撤回禁诉令申请或做出任何其他为了终局性撤销该禁诉令涉德部分的声明。
禁止通过直接阻碍本程序的法院或者行政命令以间接性地阻止申请人在德国基于其德国标准必要专利提起专利侵权诉讼[…]。
[…]
2020年12月4日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IDC的复议申请作出答复,维持针对IDC签发的禁诉令 (Annex AR ZV 7)。
[…]
2020年12月22日至23日
第四被告对2020年11月9日的临时禁令提出异议(BI.109/133),并申请暂停执行(BI.149/151;BI.8/13 QM booklet)。
[…]
2021年1月21日
第一至第三被告也对2020年11月9日的临时禁令提出了异议(BI.194/218)。
[…]
裁判理由
这一临时禁令应当被维持,因为临时禁令之理由与禁令救济之请求权已得基本证明成立。在印度和中国的未决诉讼既不阻碍对另一项未决判决的驳回,也不影响对法律保护之必要性的确认。临时禁令也已及时对所有四名被告生效。
[…]
A. 具有管辖权
慕尼黑第一地方法院具有国际管辖权、地方管辖权和标的物管辖权。因此,专利诉讼庭有权作出裁决。
[…]
B. 符合执行期间规定
所有四名被告的禁令执行期限都符合《德国民事诉讼法》第936条、第928条以及第929条第2款的规定。
C. 存在法律保护的必要性且其他地方无相关未决案件
I.对原告而言,申请临时禁令获得法律保护是必要的。作为诉前措施的临时禁令法律保护之所以必要,通常是因为原告提出的主张未得实现。倘若原告能以更简单、廉价的方式实现其法律保护目标或已实现其法律保护目标,禁令救济法律保护则不再必要。
1.根据慕尼黑高等地方法院2020年12月12日的判决(GRUR 2020, 379, paras. 51, 68 et seq.),X.在印度诉讼中提出、而未在德国诉讼中提出“IDC只能在中国法复议框架下对禁诉令提起抗议,不具备在他国起诉以求法律保护之必要性”之主张,并非慕尼黑高等地方法院认可的理由(Annex AR 26, p. 28, point 24)。而在目前的诉讼中,同样无法预期,禁令原告对其专利所享有的受到基本权利保护的财产性权利,以及原告在授权国基于指称的侵权行为发起侵权诉讼的可能性,能够受到中国法院的有效保护。虽然从德国法角度来看——这也是本案唯一相关的法律——武汉签发的禁诉令属于德国允许的程序手段,但它也构成了对专利权人法律地位的一种非法干涉,因为专利权享有类似于所有权保护的地位(cf.OLG Munich GRUR 2020,379 marginal nos.5-7)。诚然,存在“签发禁诉令的法院脱离其法律制度之基,以其国内法律补救措施审查和纠正”的情况,但是,在德国诉前禁令程序中考虑外国法院或其上级法院纠正问题的可能性,不仅会给寻求正义的专利权人造成相当大的法律上的不确定性,还需要高难度的预判:因为在国外,每个具体案件的上诉,成败皆是未知数。
针对禁诉令提出之上诉在签发国还悬而未决这一事实既不会排除对禁令原告进行法律保护的必要性,也不会导致其他诉讼悬而不决。显然,武汉的复议申请和慕尼黑的禁诉令指向相同的法律保护目标,只不过是通过不同的路径。在德国看来,诉讼系属冲突既已产生,其风险无法通过武汉法院撤销禁诉令消灭。而要根除此种已成现实之风险,唯一的办法是申请带有惩罚性条款的禁令。除此之外,想禁止禁诉令申请人申请新的禁诉令(以防范诉讼系属冲突之风险),别无他法。
除上述以外,根据1983年10月26日联邦法院判决理由中所言(NJW 1983,1246),考虑到有效法律保护的必要性,也应当允许受禁诉令影响的专利权人享有例外:原因在于专利权人若不自己在国外引起签发禁诉令的诉讼,则将在法律保护上遭受不合理损害。
2.更何况,此种法律保护的必要性并不因在中国的主诉讼而消失。在中国的主诉讼只解决全球标准必要专利包FRAND许可费的司法确定问题。但即使X.在中国的主诉讼中胜诉,X.与IDC也无法达成授予许可之协议,作为禁令被告的X.仍然一如从前。也就是说,X.在德国境内多次侵犯禁令原告所拥有之专利的持续非法状况——也即本判决的出发点——将无法得到改善。而中国的判决也可能无法在德国得到承认,这是因为,在德国法视野下,由于被告IDC的居所地均在美国,只要他们不无异议地在武汉出庭,中国法院就显然对X.针对被告IDC提起的确权之诉缺乏国际管辖权。(《德国民事诉讼法》第328条第1款第1项)。
3.法律保护的必要性亦不受较早启动的签发反禁诉令的印度诉讼之影响。
a. […]
b. 印度的诉讼——至少在2021年1月28日口头诉讼终结之时——仅涉及针对中国禁诉令的防御措施,且该反禁诉令效力仅限于印度领土。对此,禁令原告已经通过在2021年1月28日前提交的关于禁诉令效力的明确后续声明基本证明。暂且不论这两位私人专家之间就关于撤回申请之规则是否适用印度程序法,以及如果适用,现在是否仍有可能取得法庭许可撤回诉讼的争议(see Annex AR 2,para.3.14),IDC在印度已尽一切可能避免印度法院针对中国禁诉令颁布的防御性措施具有涉德效力(AnnexAR 29,para.4.24)是显而易见的。在仍然必须要采取司法措施才能最终撤回申请的情况下,无法撤回申请不能归咎于禁令原告。在此方面,原告私人专家(private expert)的陈述——被认为是当事人的辩护意见——并未遭到禁令被告私人专家(private expert)任何实质性的反驳。因此,这些辩护意见应被视为无可争议的。(《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138条第3款和第4款)。是故,根据在印度诉讼中的陈述,对于中国禁诉令的涉德部分,IDC无法在印度继续申请签发或维持相应的反禁诉令。
[…]
II. 由上可得,印度诉讼中也不存在双重未决诉讼。由于外国诉讼的封锁作用,法律保护将对禁令原告造成不合理损害(Federal Court of Justice NJW 1983,1269),因此,本案中他国未决诉讼是否不例外地排除在德诉讼,并非需要考虑的问题。
III. 正如慕尼黑州高等法院所阐明的(GRUR 2020,379),禁令被告也无疑适用程序特权原则(para.67),因为依据《德国民法典》第227条第1款,申请临时反制措施符合正当防卫原则,是完全正当的(para.75)。且在本案中,如前所释,禁令原告可在德提起专利侵权诉讼这一利益,无法得到武汉法院的有效保护(para.76)。无论是国际法(para.82)还是欧洲法(para.83 f.)均不排除反禁诉令的签发。
D. 禁令救济之请求权成立
禁令原告也提出了初步证据,其对所有禁令被告的禁令救济请求权成立。
I. 依据《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和第1004条第1款第1项,为防止专利侵权禁令在德实施,向美国法院提出禁诉令申请,将构成对专利权人财产性法律地位的损害(OLG Munich GRUR 2020, 379; LG Munich I BeckRS 2019, 25536 marginal no. 52; Werner in: Busse/Keukenschrijver, PatG, 9th edition 2020, Vor § 139 Rn. 4, 85)。向中国法院申请维持和执行禁诉令,或是申请反反禁诉令的判决,也同样适用这一点。根据《德国民法典》第227条第1款规定的正当防卫权,禁令原告的要求同样应得支持(OLG Munich GRUR 2020,379 marginal no.75; Werner in:Busse / Keukenschrijver,PatG,9th edition 2020,Vor§139 (Rn。4,85)。
II. 两名禁令原告都合理地表明,他们分别是德国境内受中国禁诉令影响的3G和4G技术相关专利的所有人。据两名禁令原告的内容和理由,中国禁诉令的效力范围不仅限于中国,还覆盖全世界。即使不直接遭受强制措施的威胁,第一与第二禁令原告也受到中国禁诉令第1-5段中“及其关联公司”的影响。鉴于禁诉令对该禁令原告的关联公司构成威胁,作为ID集团中诉争之标准必要专利的享有者,禁令原告在诉讼自由上也受到了中国禁诉令的限制。
[…]
E. 临时禁令之理由成立
禁令原告已基本证明临时禁令之理由成立:一方面,存在时间意义上的紧迫性,另一方面,存在普遍意义上的紧迫性,即原告将这一事项提交主诉讼处理不具有期待可能性。
I.申请临时禁令的原告已基本证明,让他们将这一事项提交实体诉讼是不现实的。这是依据申请人提出的、旨在直接反对另一法院已签发或将要签发的禁诉令案件的性质而得出的。禁令救济是独占性权利(例如专利)的基本特征,也是专利权人最锋利的武器。倘若专利权人失去了借助国家垄断权力,通过普通法院诉讼的形式来保护其独占性权利的可能,那么专利权便在事实上失去了价值(Keukenschrijver in Busse/Keukenschrijver, PatG, 9th ed., § 9, marginal no. 26)。不过,专利权人仅在专利有效期内享有禁令救济权。因此,若最终判决涉及另一法院签发的禁诉令,该判决便无法有效保障禁令救济权。不管怎么说,在一项胜诉一审判决得到初步执行之前,专利权人的禁令救济权在事实上是被剥夺的。如前所释,即使由于违反公共秩序,外国法院签发的禁诉令在德国不予认可。但是,外国法院通过威胁措施或国家强制措施,仍然可以对专利权人确立和维持强制性状况,这将在事实上阻止专利的有效实施。
对于尚未由另一法院签发的禁诉令而言,情况更是如此。特别地,这也适用于禁止申请保护性措施(反反禁诉令)的命令遭遇争议的情形,正如本案。
II.临时禁令之原告亦已基本证明,在已知侵权行为和侵权人的情况下,他们已符合慕尼黑高等法院在工业产权保护领域所适用的一个月的期限要求,而目前该具体个案的诉讼程序恰恰符合该期限要求所适用的情形。[…]
1. […]
2. […]
a. […]
b. […]合议庭因此认为,一个月期限应得适用。但是,由于时间紧迫而造成的特殊困难可以通过以下措施得到有效解决。
3.
a.在适用一个月期限的情况下,如果临时禁令申请针对的是重复侵害危险,期间计算始于专利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禁诉令签发时。[…]
b.如果临时禁令申请针对的是首次侵害危险,期间计算始于专利权人知道或应该知道存在禁诉令申请或者具有提出禁诉令申请的现实风险时,比如另一方当事人威胁要提出此种申请。根据慕尼黑高等地区法院的判例法,提交签发一项禁诉令的申请构成《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和第1004条第1款所指的对一项绝对权利的首次侵害危险(OLG Munich GRUR 2020, 379 marginal no. 55 f.)。不过,(面对对方提出禁诉令申请的情况)专利权人也可以选择先等待并观察首次侵害危险是否会现实化,比如相关法院是否签发了申请人所要求的禁诉令。若禁诉令被签发,则可适用上述关于重复侵害危险的期间计算规则。
c. 首次侵害危险的期间计算规则也适用于以下情形:专利实施者申请禁诉令是为了令专利权人在目前诉讼和请求未决的情况下无法在全球范围内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的确,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护其同样以法律诉讼行使专利权的可能性,专利权人不得不须在短时间内准备并向大量不同的司法管辖区域提交合适的反制措施(反禁诉令)申请。但是,到目前为止,只有在全球专利包所有人就标准必要专利与全球专利实施者之间发生的世界性纠纷中,人们才会看到禁诉令申请。此类专利所有人应当意识到其许可请求的全球性,以及专利实施者在全球范围散布个别反制措施的风险,比如异议、无效诉讼、消极确认之诉、诉诸个别反垄断机构或法院等。除此之外,专利权人还应当意识到,个别专利实施者可能会利用外国司法管辖权提供的可能性来申请禁诉令。鉴于此,他们还应当考虑到,正如本案,外国法院可能会在没有特别说理的情况下根据请求在除印度外的全球范围内全面禁止诉讼。
d. 在这方面,专利权人可以提出任何要求:
aa.理由在于,专利权人可自主决定是否在前期基于对方先提出的禁令威胁(the threat of first instance)提请适当的反制措施。这一反制措施,不是说或不限于反禁诉令,即针对预期签发或已经签发的禁诉令的禁令,可能还包括反反反禁诉令,即禁止专利实施者在国外提起的为阻止专利权人申请反禁诉令的临时禁令(反反禁诉令)的禁令。今后,如果存在下列情形之一,慕尼黑第一地方法院将在上述已被讨论过的已知情形之外,始终推定存在首次侵害危险:
-专利实施者威胁要申请禁诉令。
-专利实施者已经提出禁诉令申请。
-专利实施者已在通常会授予禁诉令的司法管辖区提起或威胁提起授予许可或确定合理费用的主诉讼。
-专利实施者曾威胁或申请对其他专利权人发出禁诉令,而且没有迹象表明其今后会有不同的行为。
-专利实施者未在专利权人规定的短期期限内(例如首次侵权告知时)以书面形式声明不提出禁诉令申请。
bb.属于同一集团的公司一般被同视为专利权人或专利实施者。
cc.在此方面,在请求和签发全球禁诉令的风险中确定首次侵害危险的判例法有待进一步发展:
(1)根据联邦法院以前的判例法,要推定首次侵权风险(risk of first infringement)之存在,首先需要有紧急且切实的迹象表明被告将在不久的将来采取不法行为。而首次侵害危险(risk of first occurrence)必须与具体侵权行为有关。要确定首次侵权行为风险(frist risk of commission)产生,就必须表明即将发生的侵权行为处于一种具体的状态,即这一行为已经具备了法条所规定的全部要件,而不论专利权人是否意识到侵权行为。由于首次侵权行为风险是禁令救济请求权的事实前提,举证责任由申请人承担(既存判例法;cf.BGH judgement of 20 December 2020 -I ZR 133/17 marginal no.50 mwN-Neuausgabe)。相反,被申请人依据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享有提出禁诉令的权利,但这项权利的存在并不能切实表明其将会主张该项权利,因为权利的存在至多为被申请人提出主张创设了理论上的可能性,但这不足以表明,被申请人会提出主张并对权利人构成风险。此外,被申请人必须要存在引起“可能在不久之将来即将发生的具体侵权行为”的经常性行为,如果被申请人援引了这项权利(申请禁诉令的权利),则能够被视为这种经常性行为(see BGH judgement 20.2020.20 -I ZR 133/17 marginalno.53-Neuausgabe)。再者,仅通过表明其法律地位并不足以维持未来发生相应行为的可能性,所以,在评判本案具体情况时,被申请人提出禁诉令的声明还必须表明其会立刻或在近期采取行动(BGH judgement 20.2020.20-I ZR 133/17 marginal no.53 mwN-Reissue)。
(2)仅存在预期签发的禁诉令,不足以被认定其存在首次侵害危险,在其签发时未具体提及专利权人将采取司法措施的情况下,尤其如此。诚然,若其后当真发生首次侵害危险,具有全球许可意愿的全球专利包所有者便可利用和专利实施者首次磋商前的这段时间,准备在所有相关司法管辖区内申请适当的反制措施(反禁诉令)。然而,按判例法,当案件存在大量专利实施者时,若无具体迹象表明是否存在某个专利实施者会向某个国家提交禁诉令申请,专利权人要在全球范围内预防首次侵害危险,其将面临不成比例的巨额成本。例如,在华为诉中兴判决(ECJ GRUR 2015,764)中,将接到侵权人通知作为时间点是一项强制性规定。更何况,在专利权人的诉讼或申请正处于或很可能将处于悬而未决的领土外——正如本案——禁诉令是否会被签发并在世界范围内发挥效力,目前也是不清楚的。因此,只有在时间上适当提前首次侵害危险的认定时间点,才能保证专利权人获得有效的法律保护。鉴于以上列举的——挂一漏万——产生首次侵害危险的情况都建立在专利实施者(或其关联公司)发起诉讼的基础上,专利实施者就必然要考虑如何免遭高代价临时禁令以预防恼人的禁诉令申请。因此,专利实施者及其关联公司会亲自把关,将首次侵害危险扼杀在摇篮,或者通过做出适当的声明来消除已经存在的风险。我们完全可以期待专利实施者会这么做,鉴于目前所知的,禁诉令申请之所以得到支持,皆是出于保护在签发禁诉令国未决主诉讼之必要。这些主诉讼或旨在解决FRAND许可协议的签订,或旨在脱离协议的具体签订,对FRAND许可条件做出抽象确定。不过,这两种类型的诉讼在论证上具有共同之处:专利实施者愿意获得许可,而许可协议之所以无法达成,导致世界范围内已实施的和正在持续的使用行为陷于不法,皆归咎于专利权人。可是,倘若这些专利实施者真心实意希望获得许可,在已实施和正在进行的使用行为以外,他们还应停止对专利权人受保护的财产性法律地位的进一步非法干涉。或者,换言之,根据欧盟法院和联邦法院判例法精神,若专利实施者已申请禁诉令或威胁要如此,通常不能被认为有接受许可的充分意愿(cf. ECJ GRUR 2015,764- Huawei v. ZTE;BGH GRUR 2020,961-FRAND-Einwand;judgement of 24.11.2020 -KRZ 35/17-FRAND- Einwand II; e.g. LGMünchenI GRUR-RS 2020,22577;21 0 13026/19 at juris)。因此,专利实施者不仅应在受到侵权通知后表明其合格的被许可意愿,还应明示其不会提起禁诉令申请。
dd.如果人们希望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这一问题,欧盟法院的协商程序必须得到根本性变革。侵权通知和随后的诉前程序必须删除,如此,根据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橙皮书标准案(GRUR 2009,694),“寻求获得许可的专利实施者必须在协商过程中首先行动”的局面将会恢复。
ee.此外,只有当专利权人同样可以不受限制地在法庭上提出在其看来是现实存在的侵权索赔——作为对专利实施者不受限制地攻击专利组合的补偿——双方当事人才能共同在平等基础上维护自己的利益,进而依照欧洲法院的协商机制,以公平的方式进行协商。倘若从一开始就排除了因禁诉令而产生的侵权索赔的司法主张,这种法律保护可能的同一性便无法再维持。支撑这一点的另一理由是,禁诉令还直接且立即地排除了诉诸法院的权利(诉权),而此项权利不仅为《欧盟基本权利宪章》第47条第1款所保障,还可从《德国基本法》第2条第1款、第101条第1款第2项、第103条第1款以及《人权公约》第6条结合《德国基本法》第20条第3款下的法治一般原则推导而来。在解释程序规则时必须考虑给予当事人司法公正的权利(Thomas / Putzo,ZPO,41st ed. 2020, Einl I marginal no. 29; cf. also Z?ller!Vollkommer, 33rd ed. 2019, Einleitung, marginal no. 33, 34)。除此之外,对于可能直接影响程序性法律保护的实质性标准(比如首次侵害危险问题)的判断,没有任何其他的衡量因素。因此,享有司法保护权也要求适当提前转移首次侵害危险——正如本案——以避免禁诉令从一开始就实际排除法院的管辖权。最后,在上述案件中,如此处所提倡的那样,只有通过提前转移首次出庭的风险(the risk of frist apperance),才能确保拥有诉诸法院的机会。
ff.如果协商机制维持原样,不将确定首次侵权风险的时间提前,那么专利权人就会遭遇颁布禁诉令(作为对侵权人通知的回应)的威胁,如前所释,这将在事实上阻止专利权人在大量案件的审理中根据专利法成功申请禁令救济,哪怕这一申请针对的是那些毫无疑问不愿意在专利有效期内获得许可的专利实施者。然而,这一结果将与《执行指令》(指令2004/48/EC)第9-11条和欧盟法院判例法的价值相悖。
因此,慕尼黑第一地方法院认为,如果上述任一情况可得基本证明,则应假定有首次侵权风险。
4.
a.在本案中,禁令申请人合理地表明,他们于2020年9月25日至26日期间首次知晓武汉法院签发禁诉令。[…]
b.就本案特殊情况而言,原告(反禁诉令的申请人)可破例等待武汉复议程序的结果,至少至武汉法院确定维持禁诉令。[…]
aa. […]
bb. 出于以下原因,鉴于本案特殊情况,被告(禁诉令的被申请人)可破例等待武汉复议程序得出结果。
(1)毋庸置疑,作为专利权人,他们第一次面临该局面:在专利权人未采取具体行动或请求,且未有具体迹象表明其将在某些地区采取该行动或请求的情况下,中国法院应原告申请,针对被告签发了除印度外覆盖全球的禁诉令。(见Yang Yu教授和Jorge L. Contrerars教授:Will China's New Anti-Suit injunctions shift the balance of global FRAND litigation? on patentlyo.com of 30.10.2020, Annex AR 14 p. 9)。 因此,他们自然尚未知晓法院的上述裁决——在这种情形下,复议程序既不会排除针对禁诉令的临时禁令的可能性,也不会影响紧急截止日期的确定(即确定首次侵害危险的最后日期)——也不知晓慕尼黑第一地方法院针对这一事态发展会采取何种进一步行动。
(2)[…]
另一方面,在得知中国法院之裁决及本判决意见后,其后的专利权人有充足的时间建立法律团队,协调准备提交相应申请。此外,与本案禁令原告不同的是,在他们的国际法律团队准备申请反禁诉令时,他们可能通过适当的预先诉讼带来优先取舍的风险(a risk of frist refusal)。
[…]
cc. […]
dd. […]
III.双方利益的必要权衡支持临时禁令的签发。
1.即使中国的禁诉令由于违反德国关于国际管辖的规定及德国的公共秩序而无法在德国获得承认和执行(《德国民事诉讼法》第328条),只要中国的禁诉令继续存在,在一段难以预估的时间内,禁令原告事实上就无法在德国境内行使其专利权,否则就将遭受巨额罚款,自己或同集团企业或许也会在中国面临报复。合议庭意识到,中国法院也许会认为该反禁诉令以及在此基础之上施加的行政罚款同样违反中国的公共政策,因此不应在中国获得承认和执行。但是,如果撤销该临时禁令,禁令原告便连以另一个生效判决对中国禁诉令提出抗议的机会都将失去,而在德国法看来,中国的禁诉令并不合法。进一步说,我们应当认识到,法律既不需要也不可能向不公正低头。
2.依德国法,若临时禁令确认签发,则禁令被告有义务撤回禁诉令,但撤回禁诉令并不会影响中国只涉及确定全球FRAND许可费的主诉讼。临时禁令确认签发后,禁令原告可能会在德国继续提起侵权诉讼。届时,这些诉讼将由专利诉讼庭依法按照两造当事人诉讼程序进行审查。未来诉讼的被告尤其可能提出不侵权抗辩,并基于对相关专利提起无效或异议而申请中止诉讼。而未来被告提出的FRAND异议很可能不会得到法院支持,原因如前所释,法院会倾向认为本案中禁令被告的行为不能表明其愿意接受FRAND许可谈判。所以,德国侵权法院很可能甚至不会对FRAND异议进行实质性审查。从而,德国侵权法院也不会从实质上去处理全球许可费确定的问题。是故,签发临时禁令与在中国进行的主诉讼不会发生任何冲突。
3.这也不构成对未来侵权诉讼的被告的司法不公。对于未来的被告,他们通过向武汉法院提起在中国的主诉讼——这在原则上既是允许的,也是不招致反对的——确定了在全世界范围内对全球许可费确定问题拥有唯一管辖权的法院,那么就必须令自己在这方面受到约束。即便由于违反德国的国际管辖权,中国未来的裁判在德国不被认可,这一结果也不会改变。对此,未来的被告只能自负其责。
4.德国不考虑FRAND异议抗辩与中国主诉讼的诉讼标的的双重未决。抗辩方提交的材料并没有对争议标的进行界定,根据争议标的二分支说,仅结合所寻求的救济对所寻求救济之标的进行了界定。(BGH GRUR 2012,485-Rohrreinigungsduse II, para. 23; Zigann/Werner in Cepl/ Voss, Prozesskommentar zum gewerblichen Rechtsschutz, 2nd ed., § 253 para. 53 et seq.)。
5.禁令被告希望在中国主诉讼结束前免受德国专利侵权诉讼之累——此种利益并不值得保护。作为从事大型生产和进出口的公司,被申请人本就应当经常检视专利的相关情况(BGH X ZR 30/14 marginal 133 – Glasfasern II),并在开始使用前获得必要许可(比较 ECJ GRUR 2015, 764 marginal 58 – Huawei v. ZTE),而在本案中,禁令被告在未获许可的情况下——使用前获得必要许可被认为是现有程序的目的——已在世界范围内使用禁令原告的相关专利长达七年之久。在这样的背景下,不能期望禁令原告再坐以待毙。
F.法律后果
I.根据《德国民法典》第1004条,由于非法干涉原告在禁令中受财产保护的法律地位,应命令禁令被告停止进一步干涉,并对后果进行补救。
在这点上,应采取的补救措施包括申请撤回禁诉令。虽然主要事项(2020年8月4日的禁诉令申请)已经得到了类似于执行令的终局性解决,但从有效保护两名禁令原告的角度来看,撤回禁诉令仍有必要。因为只有撤回涉德禁诉令,二禁令原告才能在法律上保障自己及其子公司不会因其在德的后续诉讼而面临来自中国的大量罚款。
第四被告关于禁令执行部分所命令的行为对其而言不可能的抗辩不能成立。随合同提交的个人行为(The individual acts listed with the indents),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23日所发布的禁诉令((2020)鄂01知民初169 之一)适用范围之广的仅有例证,又意在通过任何其他司法或行政措施直接或间接地禁止申请人在德国提起与其标准必要专利有关的专利侵权诉讼。如上所述,被告作为该集团的母公司,在申请和维持禁诉令方面是同谋和受益者。因此,它很容易按照禁令的执行部分行事,并在此方面影响禁令中根据集团法则从属于它的其他被告。在这方面,申请禁令以及在理由中提到申请的临时禁令,都应该按照第四被告的方向来理解和解释。
第四禁令被告的信件显示,截至2020年11月18日,该义务未被履行或被部分履行(HL ZV 2a),上文已经对此作了解释。
Ⅱ.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第97条第1款,禁令被告还必须承担禁令程序的进一步费用
Ⅲ.暂时中止执行的申请因此在2021年1月28日已被驳回。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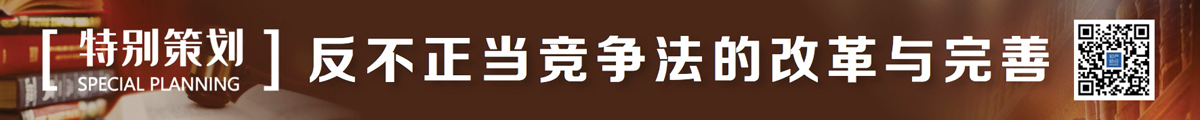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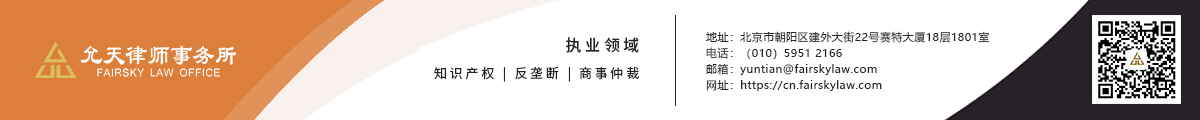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9464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946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