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黎 叶 广东华进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
杨泽洲 广东华进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助理
商业诋毁行为,又称商业诽谤行为,具体表现为通过编造、散布虚假信息或误导性信息,损害他人商誉。大部分关于商业诋毁的案例可以归入以下几类:对比广告、律师函或侵权声明、同行监督或商业评论。商业诋毁脱胎于一般民事侵权及诽谤,由于其与商业竞争的紧密联系,逐渐被反不正当竞争法所吸纳,如今已成为一种由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调整的典型的不正当竞争形式。
商业诋毁的认定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一条规定,经营者不得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从该条款的适用来看,司法政策是从侵害知识产权的角度,并采“补充保护说”对商业诋毁行为进行规制的。司法实践中商业诋毁行为的判定,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主体要件、主观方面、客观行为、结果要件。
(一)主体是竞争关系中的经营者
根据商业诋毁条款的规定,诋毁言论必须是经营者针对竞争对手所发表的。这一规定蕴含了两个要件,即经营者要件与竞争关系要件。
对于经营者要件,《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本法所称的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或者提供服务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对于不符合上述情形的,即为非经营者,对于非经营者实施的诋毁行为,则以名誉权保护的方式进行救济。
在“罗定市某丰兆业房地产开发公司与名誉权纠纷案”[1]中,某丰公司是小区的房地产开发商,被告等人是小区业主,法院认为,上诉人未能证明被告等人是从事房地产开发的经营者,双方不存在竞争关系,因此本案仅属一般性质的名誉权纠纷。
但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非经营者的诋毁行为以商业诋毁的方式进行救济的情形。在“凉山州某森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王某商业诋毁纠纷案”[2]中,法院认为不论行为人是否具有经营资格,只要在从事或者参与经济活动中损害了竞争秩序,其行为就要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制。案件中王某虽然不是经营者,但其是被告法定代表人的妻子,基于夫妻关系,二者有共同的利害关系,与某森公司构成竞争关系,可以共同成为商业诋毁的主体。
在上海某衍贸易有限公司与雷某商业诋毁纠纷上诉案[3]中,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同样认为对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经营者不能作狭义的理解。雷某是被告圣某凯威公司的副总经理,负责企业的日常经营和管理,直接参与了该公司的经营活动。从雷某在圣某凯威公司的任职情况来看,其可以视为原告的同业经营者。而且,雷某在陈述虚伪事实时使用了“我有一家竞争对手......”这样的表述,可见雷某在实施上述行为时也是从原告竞争者的角度出发的。因此,雷某符合商业诋毁的主体要件。
从上述三个案件中可以发现,无论主体是否为经营者,认定商业诋毁都离不开“竞争关系”这一要件。一般情况下,同行业的经营者具有天然的竞争关系,也被称为狭义的竞争关系,这点无需赘述。但不同行业经营者存在竞争关系的情形也时有发生,为了克服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中竞争关系的瓶颈,司法机关又提出了广义竞争关系理论,即经营业务虽不相同,但其行为违背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的竞争原则,也可以认定具有竞争关系。
在“北京某升汇杰餐饮公司与北京某客互动公司商业诋毁纠纷案”[4]中,法院认为某升汇杰公司是阿文蟹黄汤包的经营者,某客互动公司的经营业务为在抖音、微博等平台上为商家进行商业推广。尽管双方并非同行业经营者,但某客互动公司与多家餐饮经营者具有商业合作关系,其服务对象与某升汇杰公司之间系同行业经营者,故其实质上已经间接参与了与餐饮相关的业务,在争夺消费者方面与某升汇杰公司存在商业利益冲突,并具有竞争关系,符合商业诋毁的主体构成要件。
综上,商业诋毁作为反法的规制对象,“竞争关系”是其核心要件。不具有“(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要件,则不构成商业诋毁;但不具有“经营者”要件,却可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具有“竞争关系”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的经营者之外的主体纳入商业诋毁的调整范围。
(二)主观方面为故意
关于商业诋毁的主观要件,《反不正当竞争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大部分判决中法院认为,商业诋毁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必须为故意,不包括过失。认为商业诋毁行为人的主观目的是损害他人商誉,这种故意是明显而确定的。过失也可能对商誉造成损害,但应当构成名誉权侵权而不是商业诋毁。在“深圳某诺杰公司诉彭某不正当竞争纠纷案”[5]中,法院认为经营者实施商业诋毁行为的目的,是为了故意削弱竞争对手的市场竞争能力,并谋求壮大自己的竞争优势,从主观心理状态来看,是故意实施商业诋毁行为。
在某亿恒远(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某世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6]中,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解释称,认定商业诋毁成立必须要有明显的主观恶意,该恶意情节的认定要有充分的论证基础,不能以可能出现负面结果进行推论。因此即使商业评价中出现了“差评”,也不能就此认定该等评价损害了被评价方的商业信誉,是否构成商业诋毁还是得基于商业评价所依据的数据是否真实、客观,评价体系是否完整,评价人是否具有不正当竞争的主观恶意等进行判断。
但也有部分法院认为商业诋毁的主观要件包括过失。在“湖南省某洁家纺公司与陈某等商业诋毁纠纷案”[7]中,法院认为商业诋毁作为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本质上属于侵权行为,认定被告的行为是否构成商业诋毁,需要判断经营者主观上是否有侵权的故意或过失。
尽管我国并未对权利和利益进行区分,但对二者的区分实质上是权益保障与行为自由的权衡。侵害“权利”的行为人主观上可以是故意或过失,但侵害“利益”的行为人主观上更倾向于故意。[8]
(三)客观行为表现为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误导性信息
商誉的损害不仅来源于编造、传播虚假信息,也可能来源于编造、传播误导性信息和不公正的评论。《反不正当竞争法》并未对虚假信息以及误导性信息进行定义,法院在审判实践中一般认为没有根据、无中生有的或虽有但已然被歪曲的信息属于虚假信息,既包括捏造不存在的信息,也包括对真实信息的篡改。“误导性信息”是2017年反法修订后新加入的商业诋毁形式,对完善商誉的保护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缺少对有诋毁意图的不公正评论的规定。
在“奇虎360诉腾讯案”[9]中,法官就“误导性信息”和“不公正评论”是否属于商业诋毁应规制的范围进行了说理。
对于“误导性信息”,法官认为“即使某一事实是真实的,但由于对其进行了片面的引人误解的宣传,仍会对竞争者的商业信誉或者商品声誉造成损害”,因此亦属商业诋毁行为。这种“误导性”的根源在于歪曲,如果言论客观、真实、公允,那么即便该言论会降低相关经营者的社会评价,仍不构成商业诋毁。
对于“不公正评论”,法官认为经营者以竞争目的对他人进行商业评论或者批评,应当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奇虎公司“以自己的标准对QQ软件进行评判并宣传QQ存在严重的健康问题,造成了用户对QQ软件及其服务的恐慌及负面评价。”这种评论已超出正当商业评论的范畴,因而也属于商业诋毁。
(四)结果要件是对竞争对手商誉造成一定的损害后果
按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一条的规定,对于商业诋毁行为的认定必须具备损害后果要件,即行为人的行为对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造成损害。
至于损害后果,是商业言论针对对象的利益与商业言论者的利益、公众知情权之间的冲突。因此,如果商业言论并未造成商誉的损害,则两者之间的冲突也就不存在。但在司法实践中,要求权利人充分证明损害后果的存在较为困难,因为商业诋毁的损害事实包括商业信誉毁损和利益损失,这两者并非当然同时发生,不能因为利益损失的不存在而否认商业信誉毁损的存在。有学者提出,商业信誉损害事实并不要求损害结果的发生,存在损害的危险性即可。
判断经营者的商业信誉是否受到损害,应当依据社会的客观标准而非行为人或受害人的主观感受。
在“深圳市某纳斯婚纱摄影公司与深圳市某兰新娘文化公司等商业诋毁纠纷案”[10]中,法院认为双方作为同业竞争者,若以良好商业言论的标准衡量,被告部分措辞或许带有同行相轻之意,但结合发生地点、发生原因、表达方式、影响形式、影响范围等多种因素进行综合判断,并不足以造成达到行业内一般理解的损害商誉的结果。
在“深圳市某邦仪器公司诉深圳某瑞电子公司商业诋毁纠纷案”[11]中,最高人民法院也指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需要以法律观念和标准进行衡量,若仅仅是基于个人喜好、情感、价值判断等而进行一般性的商业评价,按照行业内的一般理解尚不足以造成事实上确能贬低他人商誉的具体损害后果的,并不构成商业诋毁行为,仍属于商业性言论自由的范围。
总结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种新的经济关系不断出现,商业诋毁行为也越来越复杂。尽管《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订对商业诋毁行为的客观表现、民事责任、行政责任进行了完善,但这种完善仍是在竞争法框架下的修补,在司法实践中显得左支右绌。如上文中谈到的竞争关系、经营者与非经营者、故意与过失、损害后果等,这些问题均指向竞争法与权利法的立法选择。
在今后的立法中,建议厘清商业诋毁的权利属性,搭建好立法框架,进而对具体问题予以规范,以期更好地解决司法实践中对商业诋毁的认定及处理。
注释:
[1]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粤民终1455号民事裁定书。
[2]参见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川知民终614号民事判决书。
[3]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1)沪一中民五(知)终字第229号民事判决书。
[4]参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9868号民事判决书。
[5]参见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深中法知民终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
[6]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知)初字第32295号民事判决书。
[7]参见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湘01民终1394号民事裁定书。
[8]如德国民法典第823、826条、王泽鉴《侵权行为法》等均有类似阐述。
[9]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三终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
[10]参见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3民终8319号民事判决书。
[1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191号民事裁定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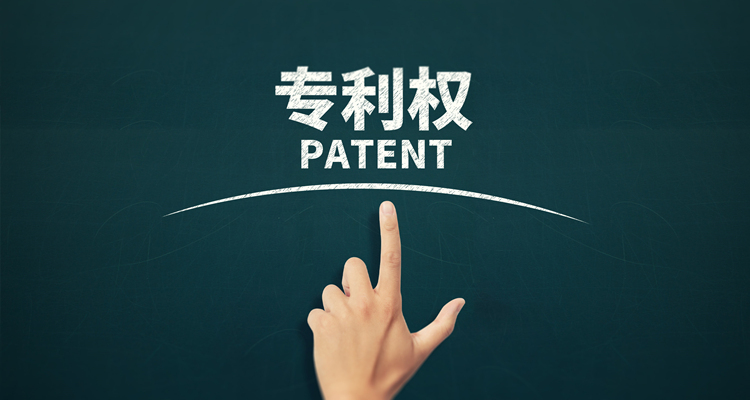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9464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946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