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研究院于2021年6月16日揭牌以来,结合数据法学的研究方向,遴选若干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课题,设立相应的课题组,由研究院给予条件支持,开展工作。基于平台经济的规范与发展、知识产权战略及司法保护多维一体的考量,研究院选定了“互联网领域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数据分析”这一课题,经过课题组近2个月的辛勤工作,在确保数据真实、准确的前提下,运用科学计量方法及工具,进行客观分析和描述,形成本报告。期待研究院陆续发布的课题成果能够对相关理论研究和实务工作有所裨益。
一、引言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作为知识产权保护法治化中的重要一环,严格而全面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能够充分保护企业创新创造的智力成果,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激励企业进一步投资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管理和保护,推动产业的升级和新旧动能转化,实现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1]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国互联网行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模仿到自主创新、从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尤其是海外主流市场的发展历程。这充分表明,日趋的严格而全面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不仅为我国互联网企业的创新发展营造了生存和发展的硬环境,而且提升了我国互联网企业在开拓国际市场中应对更为复杂、更为严苛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能力。
与此同时,企业重视和投资知识产权的创新创造以及随之而来的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对知识产权的司法审判不断提出新的挑战,例如,知识产权专业性强、新型疑难案件多、刑民行诉讼交叉叠加、审判力量相对不足,等等。对这些挑战的应对,成为了我国知识产权司法裁判水平的提升、裁判标准的统一和司法审判体制的改革创新的重要动因。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贺荣在2021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高层论坛所指出的,“40多年来,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
二、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逐步强化的发展历程
为服务于改革开放与法治建设需求,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至少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其中,第一阶段从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1978-2001);第二阶段始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历经《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实施,直至知识产权司法审判改革前(2001-2014);目前处于第三阶段,始于知识产权司法审判改革期(2014-)。
(一)第一阶段: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法治的积极探索
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进入初创阶段。知识产权立法是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知识产权司法同步建立,我国仍然重视知识产权司法审判的专业性,北京市高、中级人民法院在1993年率先成立知识产权审判庭,拉开了我国知识产权审判专门化的序幕。在1994年和1995年先后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设立基层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最高人民法院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1996年11月正式成立知识产权审判庭。
这一阶段,知识产权案件量较少,所依据的知识产权法也仅为我国首部《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司法实践经验还不够丰富。[2]不过,当时的法院也要面对新型的网络知识产权案件。例如,在1995年的王蒙等诉世纪互联公司侵害其在网络上享有的著作权纠纷案,由于信息网络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尚不完善,该案在当时面临“无法可依”的局面,最后海淀法院知识产权庭将互联网上传播他人作品认定为使用作品的一种方式,并判定被告侵权。
(二)第二阶段:中期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持续加强
进入21世纪,我国知识产权司法审判主要工作是探索如何与WTO规则接轨,并结合前期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以来知识产权司法实际面对的问题,重点解决知识产权案件审理的审限过长、透明度差、审判标准不统一和审理程序不完备等问题。[3]我国由此在2000到2001年前后开展了《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的首次修订工作,从立法层面回应了前述问题,形成了相对规范、完整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
在司法层面,最高人民法院除发布二十多项知识产权司法解释补充解决上述问题之外,还在2005年指定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承担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刑事诉讼程序衔接方面的课题调研。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又在2006年确定广州市天河区、深圳市南山区和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三个基层法院作为知识产权刑事、民事、行政审判“三审合一”审判方式改革试点法院。后续,“三审合一”审判方式在全国法院知识产权法庭中得到逐步推广。与此同时,我国在2006年通过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为四类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了避风港规则,为我国互联网知识产权司法审判提供了重要指引。[4]
在政策层面,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我国在2008年发布《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明确提出要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为贯彻纲要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在2011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审判职能作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促进经济自主协调发展若干问题的意见》首次提出“加强保护、分门别类、宽严适度”的知识产权司法政策。
其中,加强保护是解决当前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主要矛盾所要实现的目标,分门别类强调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要注意适应各类知识产权的属性和特点、要符合各类不同知识产权的功能和保护需求,宽严适度则强调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要更加适应我国所处的国际国内发展环境、更加符合我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新的阶段性特征、更加符合我国文化发展和科技创新的新要求。以其中的分门别类政策为例,深度链接问题凸显了这一时期的知识产权司法审判矛盾,知识产权民事审判法院在标准上较为保守、多以服务器标准确定深度链接并不侵权,但刑事审判对深度链接已经不再采取这种保守的做法,而是结合其社会危害性直接认定其构成著作权犯罪。[5]
(三)第三阶段:知识产权司法制度的改革不断深化
为贯彻十八大报告关于“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精神与要求,2013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在此之前,知识产权保护已积累了二十余年的实践经验,但也出现了新的课题和难点,主要集中在知识产权司法审判周期仍然较长、维权成本高、赔偿额低、案件类型增加且案情新颖复杂化、同案不同判等问题,其中一个重点是要解决“企业赢了官司输了市场”的问题。为此,中共中央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司法审判体系的改革,旨在统一知识产权司法审判标准和水平、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运行的效率、提高赔偿标准。
2014年6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方案》,提出“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将来条件成熟时,再考虑在其他地区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及知识产权高级法院”。此后,经全国人大常委会2014年决定,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在上述三家知识产权法院成功运行三年之后,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在2018年12月3日设立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审理专利等技术类二审案件。在202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还批准设立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此外,为统一各地方知识产权司法审判标准和优化案件管辖,[6]最高人民法院还批准设立了24家地方知识产权法庭。值得注意的是,为了解决杭州、北京和广州等地区日益增多的网络著作权案件和其他互联网案件,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17年和2018年先后批准在杭州、北京和广州设立互联网法院,全面而充分地利用一站式诉讼服务平台、区块链等互联网技术在线审理这些涉互联网一审案件,[7]在审理周期上比传统审理模式要缩短二分之一的时间,为广大参加诉讼的企业和个人创造了便利。[8]
知识产权法院和互联网法院,集中管辖所在市辖区内的著作权纠纷、专利权纠纷、商标权纠纷、网络服务合同纠纷、网络侵权纠纷、网络著作权纠纷等案件。截至 2019 年 10 月 31 日,杭州、北京、广州互联网法院共受理互联网案件118764 件,审结 88401 件,在线庭审平均用时 45 分钟,案件平均审理周期约 38 天,比传统审理模式分别节约时间约五分之三和二分之一,一审服判息诉率达 98.0%,审判质量、效率和效果呈现良好态势。
各地知识产权和互联网审判庭、合议庭针对辖区内案件的不同特点,积极整合线上线下资源,探索具有地域特色的发展途径,不断丰富知识产权司法的实践样本。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互联网审判庭针对辖区内互联网服务型企业众多、纠纷批量化类型化等特点,从个案审判出发,以司法建议的形式向互联网平台企业提出合规警示,先后推动互联网企业修改完善平台管理和自治规则 12 批次, 有效推动互联网纠纷诉源治理。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法院互联网审判庭针对辖区内文创园区和项目众多的情况,加大对知识产权和创新保护力度,上线司法区块链平台,推动文创作品进行链上新技术存证,解决电子证据取证难、认证率低的问题。贵州省黔南州惠水县人民法院设立专门审判庭,跨区域集中管辖全州范围内涉及互联网数据保护、互联网交易和网络侵权等案件,利用集中化、专业化审理优势公正高效处理互联网纠纷。
由此,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形成了以最高人民法院为龙头,以北京、上海、广州、海南自贸港知识产权法院为示范,以24家地方法院知识产权法庭为重点,以杭州、北京、广州互联网法院为特色,以高、中级法院和部分基层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为支撑的审判格局。[9]在此格局基础之上,最高人民法院在2020年4月出台《关于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旨在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三、全国知识产权诉讼整体情况
民事审判是知识产权司法救济的重要渠道,对知识产权诉讼情况进行整体考察,有助于分析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整体发展情况。本报告参考了最高院及部分地方法院公布的年度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白皮书,[10]从法院知识产权案件收案情况、案件审结情况两大方面总结梳理得出部分结论,以期客观展现中国知识产权诉讼的整体状况和特点。
(一)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收案量逐年攀升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各年度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白皮书(2013-2020年)的公开数据,本报告总结了这八年的总体收案情况(表一)。总体而言,全国地方法院知识产权案件一审与二审新收案件量均呈现逐年递增趋势,其中一审新收案件量从2013年的88583件,增长至2020年的443326件,增长约4倍;二审新收案件量从2013年的11957件,增长至2020年的42975件,增长约2.6倍。此外,一审案件数量增幅明显大于二审案件数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一审案件审判质效逐步提高,多数知识产权案件在一审阶段得到解决。
表一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各年度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白皮书(2013-2020年)公布的著作权案件、商标案件、专利案件、技术合同案件、不正当竞争案件统计数据,可以发现知识产权各类型案的变化趋势(表二),即各类案件均呈现逐年递增趋势,其中著作权增幅最大、不正当竞争案件次之,这一现象与2013-2020年互联网内容产业与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相吻合,以互联网企业为诉讼主体的案件集中于著作权案件与不正当竞争案件,推动相关案件数量大幅增加,也反映出司法保护成为互联网企业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手段。此外,2013年著作权案件占知识产权案件整体的比例59.66%,2020年的比例为73.21%,可以说著作权案件已成为知识产权诉讼的重点案件类型。
表二
(二)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审结率逐年提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各年度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白皮书(2013-2020年)公布的全国地方法院知识产权案件一审案件数和结案数,计算得出全国地方法院知识产权案件一审结案率(表三)。
表三
知识产权案件一审结案率整体上呈现逐年递增趋势,其中2016年后结案率均保持在95%以上,2020年则达到峰值(99.86%),直观反映了我国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效率不断提高,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民事审判改革的成效。例如,2016年结案率的爬升跟2015年员额制改革的整体成效不无关系。
四、中国知识产权司法审判专业化水平全面提升
(一)专门法院的设立提升知识产权案件办理效率
1、专门法院收案量情况分析
知识产权及互联网相关专门法院的设立对于缓解其他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压力、解决知识产权案件收案难问题具有重要作用。报告统计了2018-2020年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简称北知)、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简称广知)、上海知识产权法院(简称上知)、北京互联网法院(简称北互)、杭州互联网法院(简称杭互)、广州互联网法院(简称广互)共6家专门法院逐年的知识产权一审裁判文书数量(即判决书、裁定书),并得到2018-2020年与知识产权及互联网相关专门法院知识产权一审裁判文书数量表(表四)。
表四
从整体趋势上看,6个专门法院中除广知外均呈现上升趋势;三大互联法院裁判文书的总数量整体高于三大知识产权法院。其中,北互、广互从2018-2020年数据呈现一个快速攀升的趋势,北互的裁判文书数量从1310上升到9927,广互的裁判文书数量从68上升到4489。
各专门法院裁判文书数量的大幅增长也体现出相关案件集中办理的优势,一方面有助于类案快速、高效、专业化办理和集中管辖,另一方面也方便了诉讼当事人,提高了知识产权案件维权效率。
2、专门法院的设立与知识产权案件审结率的交叉分析
在设立时间上,知识产权专门法院要早于互联网专门法院,6家专门法院的设立时间如表五。
表五
以当年存在的知识产权审判相关专门法院数量为基准,基于SPSS[11]软件分析知识产权和互联网专门法院的数量与一审知识产权案件结案率的相关性,可以得到表六的分析结果。
表六
利用SPSS将知识产权和互联网专门法院数量与全国地方法院知识产权审结率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出皮尔森相关性系数[12]为0.740(见表七),反映了知识产权和互联网专门法院的数量与全国地方法院知识产权审结率之间具有极强的相关性。
表七
一方面,知识产权和互联网专门法院的设立有助于专案专办。通过抽调具有知识产权和互联网审判经验的法官,这些专门法院能够更加高效地解决知识产权和互联网案件。另一方面,通过跨区域集中管辖涉知识产权与互联网案件,专门法院的建立有助于统一相关裁判尺度,并对全国相关司法实践起到了示范作用。
(二)知产审判队伍专业化提高权利人的维权预期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加大统筹协调和对下指导力度,推动各地法院制定知识产权审判专门人才培养和储备规划,建立形式多样的人员交流机制。各地法院以提升司法能力为重点,充分运用专题培训、专题研讨、在职培养、交流挂职、庭审观摩等形式,打造学习型审判队伍,适应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新形势、新要求,队伍专业化、职业化水平不断提升。[13]例如,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利用“知识产权审判特色人才高地”“北京法院知识产权审判人才培养基地”和北京市委政法委“政法人才发展体制机制综合改革试点”三大平台优势,以专家型法官带队的方式建设专业化审判团队。[14]
此外,技术调查官参审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也为知产案件的专业化审理注入了新的动力。根据不同类型的知产案件,指派技术调查官全方位参与诉讼活动,协助法庭完成技术事实查明工作。同样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为例,至2020年底,技术调查官共参与了2489件案件的技术事实查明工作,其中涉及保全勘验110件,提交技术调查意见1674份。与此同时,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技术类案件审判质效得到明显提升,2020年技术类案件结案率同比上升47%。[15]
在以往的知识产权民事案件中,由于专业技术门槛较高、辅助机制缺失,法院往往需要调动大量司法资源完成案件事实的查明工作,同时也耗费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大量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权利人的维权积极性。相比较而言,知识产权审判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有效提高了案件事实查明工作的效率,提高了权利人维权预期,有利于保障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三)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专项制度进一步提高权利受保护程度
自2018年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涉知识产权民事案件司法解释类文件超20部,其中包括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简称《知产证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查知识产权纠纷行为保全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一系列与知识产权民事审判直接相关的司法解释。这些专项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为知识产权民事审判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提高了知识产权民事审判专业化程度,有力加强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
在知识产权民事审判领域,我国已经形成了以司法解释、司法政策、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的知识产权审判指导体系,加之专业法官会议制度、类案和新类型案件检索制度。这些举措极大强化了知识产权法律的统一司法适用,并将有效推进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得到依法平等保护,为知识产权权利人提供一个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其中,《知产证据规定》立足知识产权审判实际,加大了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力度,完善证据保全制度,以妨害民事诉讼强制措施为保障,进一步完善了证据提交、证明妨碍、证据保全和司法鉴定等重要制度,适当减轻了权利人举证负担,有效降低了权利人维权和救济的成本。
五、司法创新鼓励知识产权人进行司法维权
在四十多年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历程中,我国法院不断进行知识产权司法审判程序制度和侵权损害赔偿等实体制度上的改革和创新。这些创新,一方面提高知识产权案件审判程序的规范性和完备性,提升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另一方面也方便和鼓励知识产权人的积极维权。
(一)对网络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管辖的影响[16]
2010年7月1日实施的《侵权责任法》第36条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对于网络侵权的定性上,全国人大法工委指出,“网络侵权是指发生在互联网上的各种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它不是指侵害某种特定权利(权益)的具体侵权行为,也不属于在构成要件方面具有某种特殊性的特殊侵权行为,而是指一切发生于互联网空间的侵权行为。”[17]因此,网络知识产权案件其实就指的是发生在互联网空间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这些案件要在选择在哪个法院起诉自然也是互联网企业所关心的对象。
一般而言,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8条规定,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的地域管辖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2015年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司法解释》)第25条规定,“信息网络侵权行为实施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计算机等信息设备所在地,侵权结果发生地包括被侵权人住所地。”结合全国人大法工委前述对网络侵权案件的解释,这里的“信息网络侵权行为”显然并不限于著作权中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行为,还包括了其他所有的网络侵权案件。不过,因缺乏对“实施被诉侵权行为”“计算机等信息设备所在地”“侵权结果发生地”等概念的进一步解释,该解释导致实践中涉网络知识产权侵权案件地域管辖标准的不统一问题。[18]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在2020年修订《民诉法司法解释》时,并无意对上述概念作出更进一步解释,而是将2015年上述司法解释完全保留下来。[19]
具体到网络知识产权侵权案件,包括互联网企业在内的知识产权权利人除了可以选择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进行诉讼之外,还可以选择被诉侵权行为的计算机等信息设备所在地和侵权结果发生地等侵权行为地人民法院进行诉讼。很显然,这就导致互联网企业等知识产权人基本上可以选择全国各地的法院进行起诉。此外,在级别管辖上,我国知识产权司法改革后,互联网法院作为基层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院作为中级人民法院、最高院知识产权法庭作为高级人民法院级别的知识产权案件(侧重于技术类和竞争类二审案件)管辖格局也基本形成。因此,互联网企业等知识产权当事人除了选择原有的基层法院、中级法院起诉网络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之外,还可以选择在三家互联网法院和三家知识产权法院起诉。
(二)对行为保全措施的影响
在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施行之前,行为保全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规定的海事强制令外,主要体现在知识产权领域的诉前责令停止有关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措施。然而,受制于知识产权行为保全规则的不完备,知识产权人申请行为保全的积极性并不高,相应地知识产权行为保全案件数量长期以来处于偏少的状况。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2018年,全国法院分别受理知识产权诉前停止侵权和诉中停止侵权案件157件和75件,裁定支持率分别为98.5%和64.8%。[20]
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在2018年12月12日发布《关于审查知识产权纠纷行为保全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行为保全规定》),进一步明确知识产权行为保护的规则。相应地,各地法院积极适用行为保全,逐步加大对权利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一方面,各地法院纷纷制定行为保全适用细化文件,如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制定了《关于全面加强诉讼禁令(行为保全)措施适用意见》《关于审查知识产权纠纷行为保全案件工作指引(试行)》。另一方面,知识产权行为保全案件数量和支持率呈上升趋势,以浙江为例,行为保全案件总量由2019年的29件上升到2020年的226件,其中在审结的申请诉前临时措施案件中,申请诉前行为保全的案件6件,5件得到支持,裁定支持率为83.3%;申请诉中行为保全的案件220件,74件得到支持,裁定支持率为33.6%。[21]
(三)对知识产权侵权赔偿额的影响
我国知识产权侵权长期存在“重侵权归责认定,轻损害赔偿计算”现象,导致包括互联网企业在内的知识产权人的侵权获赔数额较低,常常出现“赢了官司、丢了市场”的结果。[22]其中,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分析结果来自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0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设立执法调研组对《专利法》进行执法检查后得出“‘维权成本高,侵权成本低’,有的‘法律上赢了,经济上输了’的结论。[23]到2014年,该调研组对《专利法》进行执法检查后得出的仍然是这些问题,“专利维权存在‘时间长、举证难、成本高、赔偿低’、‘赢了官司、丢了市场’”。[24]
在更具体的赔偿额支持数额的分析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吴汉东研究发现,我国97%以上的专利、商标侵权和79%以上的著作权侵权案,基本采用法定赔偿标准,平均赔偿额分别为8万、7万和1.5万,诉求比例不到35%,低于企业同等专利授权费、培育商标知名度的广告费或同类作品平均稿酬。[25]另外,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蒋胜华曾以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015—2016年度审结的案件统计来分析民营企业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情况,并对一审专利、商标和著作权三类知识产权案件赔偿数额得出类似结论,“一审专利案件法院判决支持的赔偿额平均为3万元,法定赔偿额使用率占96%;二审商标案件法院判决支持的赔偿额平均为4.9万元,法定赔偿额适用率占97%;著作权案件法院判决支持的赔偿额平均为0.75万元,法定赔偿额适用率占80%;这三类案件的赔偿额不超过权利人请求赔偿额的30%。”[26]
对此,我国高度重视通过知识产权司法创新和改革来改变知识产权司法赔偿数额偏低的问题。其中,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规定“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6月6日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上审议通过《关于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方案》,其中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目的之一就是提高知识产权侵权赔偿数额,其中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就主推加强知识产权市场化研究,即探索按照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来判赔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数额。[27]例如,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年发布《广东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白皮书》披露,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018年一审判赔金额超1000万元的案件有3件,在法定赔偿限额以上酌定赔偿的案件达38件,最高赔偿金额达5000万,创下国内商标权纠纷赔偿额之最。[28]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进一步明确了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标准,对惩治、威慑严重侵害知识产权行为、进一步提高权利人司法保障力度具有重要意义。由此可见,我国法院高度重视通过知识产权司法创新和制度改革来提高知识产权侵权的赔偿额。
总的而言,这些知识产权司法审判创新和制度改革在整体上已初步取得成效,司法审判标准在逐步统一、审判周期在逐步缩短、[29]诉讼便利性在逐步提高、损害赔偿标准在逐步提高,整体上逐步改变“企业赢了官司输了市场”的局面。
六、互联网企业积极进行知识产权司法维权
随着我国知识产权司法审判专业化水平的逐步提高、诉讼程序的不断完善、审判标准的日益统一、侵权赔偿标准的稳步提升,包括互联网企业在内的知识产权人越来越积极地选择司法渠道进行知识产权维权。因此,分析互联网企业的知识产权司法维权情况和特点,有利于进一步反映我国知识产权司法改革的成效。
(一)研究方法
1、数据库的选取
本报告选取商业数据库Alpha(网址:https://alphalawyer.cn/home)进行互联网企业知识产权民事案件判决书的分析。选取该数据库有两大原因:一是中国裁判文书网部分裁判文书虽然可查询条目到但无法展开阅读或者下载,相比之下Alpha数据库的司法裁判文书相对全面且可以全部下载;二是Alpha数据库本身提供了比较实用的检索工具,并提供可视化的分析结果,方便进行统计分析。
2、研究对象的选取
在代表性互联网企业的选择上,本报告主要参考中国互联网协会和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中心联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企业100强》。其中,中国互联网协会和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中心自2013年来每年发布中国互联网企业综合实力排行榜,因此统计单位和统计方法都比较可靠。2020年的该榜单显示,中国前十的互联网企业分别是阿里巴巴、腾讯、美团、百度、京东、网易、拼多多、小桔、字节跳动和腾讯娱乐。然而,这十家互联网企业中,美团、京东、拼多多和小桔业务都相对单一,很少涉及著作权案件,因此未将这几家互联网企业纳入分析。为了加大分析的案件数量,本报告在分析时还把在该榜单中靠后但主要涉及著作权案件的子公司知识产权案件计入母公司案件量中,即将优酷纳入阿里巴巴名下、将爱奇艺纳入百度名下、将腾讯娱乐纳入腾讯名下。此外,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统计数据,中国已成为世界专利申请数量最多的国家[30],其中华为、中兴作为中国科技企业代表,专利申请数量连续三年居全国前五。[31]因此,尽管华为、中兴不属于互联网企业的范畴,但考虑其在考察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时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本报告亦将它们作为研究对象。由此,本报告最终选取的代表性企业为阿里巴巴(含优酷)、腾讯、字节跳动、百度(含爱奇艺)、网易、华为、中兴等7家。
3、研究内容
本报告主要选择分析这7家代表性企业一审主诉案件(即作为原告提起的知识产权诉讼)的胜诉率来观察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情况。其中,为了观察知识产权司法改革的成效,本报告选取上述主体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家知识产权法院和北京、杭州、广州三家互联网法院的主诉案件的胜诉率;同时为了分析地域差别,基于企业所在地的分布情况,即杭州市(阿里巴巴所在地)、深圳市(华为、中兴、腾讯所在地)、北京市(百度和字节所在地)、广州市(网易所在地),以及样本数量情况,本报告选取了上述主体在北京地区、杭州地区、深圳地区所有法院的胜诉率,据此分析国内不同地区对于互联网企业的司法裁判是否存在地域差别。
在案件胜诉率的计算标准上,考虑到互联网企业主诉的案件如果得到法院支持,不论是全部支持还是部分支持,都计为胜诉,但其中案件的撤诉原因多种多样不适宜纳入胜诉案件的基数,因此本报告将法院在一审知识产权案件中全部和部分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作为胜诉案件的总数,将撤诉之外的总案件数作为胜诉案件的基数,二者的比率即为胜诉率。
(二)互联网企业知识产权案件胜诉率概览
2013-2020年7家代表性互联网企业总体胜诉率统计数据(表八)显示,2013年互联网企业总体的知识产权案件胜诉率为56.67%,2020年增长至为87.33%,且自2017年起均保持在80%以上,胜诉率亦呈现出整体上升趋势。自2017年开始,胜诉率整体趋于稳定,波动性较小。这一变化体现出国家不断强化互联网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表八
(三)各互联网企业知识产权案件胜诉率比较
鉴于企业成立时间与样本量的关联性,本报告选取了2018-2020年三个年度各互联网企业案件知识产权案件胜诉率数据。应当注意的是,中兴公司在2018-2020年期间知识产权主诉案件分别为0、1、0,因此属于本次统计的异常值。
若将该异常值排除,可以发现互联网企业知识产权整体胜诉率(表九)普遍较高(均高于70%),且各互联网企业主诉案件涉及知识产权的案例胜诉率随主体变化不大,各企业胜诉率集中于80%-90%这一区间内,在每年的平均胜诉率上下波动,不存在某一企业存在持续的畸高或畸低的胜诉率。
表九
其中,华为知识产权案件胜诉率从2018年的87.50%上升到2020年的95.24%,呈现连续上升的趋势。阿里巴巴知识产权案件胜诉率从2018年的96.55%下降到2020年的79.87%,呈现连续下降的趋势。腾讯、字节跳动、网易从2018-2020年的胜诉率均体现为2019年为峰值,相反百度该年度胜诉率则为最低值。字节公司在企业知识产权案件胜诉率上是唯一一家在2018年-2020年三个年度均在90%以上的企业。
从上述数据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种判断,即我国法院在处理互联网企业知识产权案件中整体裁判尺度均衡统一,坚持司法中立性,不存在特殊地域、企业或产业类型的保护现象。
(四)互联网企业胜诉率地域性分析
如前文所述,本报告基于企业所在地的分布情况,即杭州市(阿里巴巴所在地)、深圳市(华为、中兴、腾讯所在地)、北京市(百度和字节所在地)、广州市(网易所在地),以及样本数量情况,选取了北京地区、杭州地区、深圳地区作为地域变量,对2018-2020年互联网企业在北京地区、杭州地区、深圳地区所有法院知识产权案件的胜诉率进行了统计,并据此分析国内不同地区对于互联网企业的司法裁判是否存在地域差别。为了增加数据参照,提高分析结论的可信度,本报告还将持有著作权数量较多、维权意识及能力较强的集体管理组织和公司纳入到考察范围内,包括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音集协)、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音著协)和视觉中国。
1、互联网企业在北京地区知识产权案件胜诉率情况
整体来看,各互联网企业、著作权集体组织在北京地区知识产权案件胜诉率(表十)大体持平,且处于80%-100%这一区间内,胜诉率较高。
表十
其中,华为、中兴、音集协在北京地区胜诉率为100%,但由于这三个主体的案件样本量分别为2、1、7,均为胜诉案件,因此统计样本过小在一定程度上使胜诉率偏高。
除这三个主体外,在北京地区知识产权案件胜诉率靠前的主体包括网易、字节跳动和阿里巴巴,胜诉率分别为97.44%、95.16%和88.61%。百度的胜诉率在各主体中排名靠后,为77.71%;但该主体样本量最大,共有951份,比样本量排名第二的阿里巴巴多出512份。综合上述结果可见,北京地区法院在审理涉及不同所在地企业知识产权案件时坚持统一的裁判尺度,不存在地方司法保护现象。
2、互联网企业在杭州地区知识产权案件胜诉率情况
整体来看,各互联网企业、著作权集体组织在杭州地区知识产权案件胜诉率(表十一)已呈现出数值偏高且大体持平的结果。其中,字节跳动、腾讯、百度、网易、华为、音著协、视觉中国在杭州地区胜诉率均为100%,但由于这七个主体的样本量分别为2、5、7、8、2、9和5,均为胜诉案件,因此统计样本过小在一定程度上使胜诉率偏高。剩余的音集协和阿里巴巴的胜诉率则分别为96.10%和75.61%。这一结果表明,互联网企业在所在地区法院相较于其他市场主体并不存在优势。
表十一
3、互联网企业在深圳地区知识产权案件胜诉率情况
在该统计维度下,字节跳动、网易、中兴、音著协在深圳地区的知识产权一审主诉案件均为零,因此无法统计其胜诉率。除上述主体外,统计结果(表十二)显示,与北京地区类似,各互联网企业、著作权集体组织在深圳地区知识产权案件胜诉率同样处于80%-100%这一区间,胜诉率均较高。
表十二
其中,阿里巴巴、百度、视觉中国在深圳地区胜诉率均为100%(阿里样本量为1,属于异常值),其他主体即音集协、腾讯、华为胜诉率分别为98.11%、94.64%和80%。上述分析结果表明,各互联网企业、集体管理组织在深圳地区民事案件胜诉率大体持平,反映出深圳地区法院在面对不同所在地企业时坚持统一的裁判尺度,不存在地方司法保护现象。
4、分析结论
上述三份互联网企业在不同地区的胜诉率表格比较直观的显示,北京、杭州和深圳三地法院在面对互联网企业的相关知识产权案件时均能统一、中立地对待各互联网企业,并不因互联网企业的住所地不同而存在明显差异,也从侧面说明我国法院在处理互联网企业案件时不存在所谓的“主客场”,能够坚持“以事实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不存在地方保护主义。这样的分析结论,与此前相关学者的分析也有所印证。例如,徐剑教授在2017年对网络著作权案件胜诉率的分析结果显示,“原告与法院同属一地的样本有 872 件,原告胜诉率为 85. 6% ;原告为外地的样本有 2132 件,原告胜诉率为 87. 9%。和以往研究的预期相反,异地原告胜诉率更高,从中无法看出法院的地方司法保护倾向。”[32]该分析结论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人民法院在“统一裁判标准、实现知识产权案件审理专业化、提高审判质量效率”方面取得的重要成果,也反映了我国各地知识产权司法审判的专业化水平普遍较高,知识产权整体司法保护水平进入比较高水平的发展阶段。[33]
七、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促进互联网行业创新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过去长达十年以全球各经济体的知识产权市场化水平、企业风险投资水平、企业众筹水平等指标统计并发布每年的全球创新指数。[34]其中,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GII)》报告中指出,“顶尖水平的创新指数专属于高收入国家。但中国是唯一例外,连续两年排名第14位,并仍然是唯一进入GII前30名的中等收入经济体。”[35]按照《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要求,知识产权市场化保护水平的主要体现之一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此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GII)》中也指出各经济体创新能力主要体现在科技与技术集群数量上,其中美国在2020年拥有25个这样的集群,中国则排在第二,拥有17个;而且,深圳-香港-广州和北京两个集群的全球GII排名分别是第2和第4。[36]众所周知,这两个集群也是我国互联网企业最多、创新最强的地方。[37]
由此可见,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和包括互联网企业在内的科技创新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得到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认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对互联网行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有所体现。
(一)促进科技创新成果转化
不断提升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促进了互联网行业对科技创新的投入。早在2017年,互联网企业发明专利排行中前三名的腾讯、360、百度的当年发明授权专利数量分别达到了963件、758件和722件。[38]调查显示,中国互联网前百家企业的 2019 年研发投入达 1772 亿元,较去年的前百家企业增长 15.2%,高于我国 R&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研究与实验)经费投入 12.5%的整体增速,平均研发投入占比达 9.8%,与去年基本持平。企业专利数量有了明显增长,前百家企业专利总数达到 11 万, 同比增长达 39%,其中发明专利总数 8 万,同比增长 33%,发明专利占比达到 72.4%。[39]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发挥着促进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带动技术产业升级的作用。而互联网行业与 5G、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关键核心技术联系紧密,提高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有助于企业在该类关键核心技术、新兴产业、重点领域取得突破。工信部发布的《2020人工智能中国专利技术分析报告》显示,中国人工智能专利申请主体中,百度、腾讯、阿里巴巴等互联网企业无论在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中都名列前茅,其中,百度公司分别以9364件专利申请和2682件专利授权排名第一。[40]
在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总体加强的背景下,企业对科技创新方面的投资也保持乐观态度。调查显示,38.2%的企业专利权人预计未来一年专利实施收益将有所增长,35.1%预计收益基本不变,仅 3.8%预计收益将有所下降,选择“不清楚”的比例为 22.9%。我国企业专利权人总体看好未来专利实施收益增长,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对企业创新的激励作用。[41]
(二)推动版权产业繁荣发展
为保障内容产业快速健康发展,法院通过依法裁判有效打击侵权盗版,明确内容版权行业发展的法律边界。随着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不断提升,互联网领域相关著作权保护规则更加完善,根据不同领域、不同类型作品特点确定了相适应的保护力度,促进网络版权产业发展与繁荣。
2020年,中国网络版权产业市场规模达11847.3 亿元,首次突破一万亿元大关,同比增长23.6%,相当于同年GDP(101.6 万亿元)的 0.984%。相比2016年的5003.9 亿元,“十三五”期间我国网络版权产业市场规模增长超过一倍,年复合增长率近25%。[42]其中,长视频平台内容版权投入上耗资不菲。爱奇艺财报则显示,2018年至2020年,爱奇艺在内容成本上的支出分别为211亿元、222亿元和209亿元,占公司运营成本的70%以上。企鹅影视CEO孙忠怀2020年10月表示,过去三年间,腾讯视频约投入500亿元内容开发成本,接下来的三年,拟投入1000亿元内容开发成本。
良好的司法保护环境促进互联网新业态出现。2020年短视频平台“直播带货”爆发,形成“短视频+直播”新型电商模式,并将对未来消费市场的发展方向产生深刻影响。5G 网络提升视频直播流畅体验的同时,云游戏平台等新的产品形态和应用场景不断涌现。
网易诉华多案就很好地体现了司法保护对“游戏直播”这类新兴版权产业的促进作用。本案中法院认为“梦幻西游”网络游戏连续动态画面整体构成“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应获得著作权法保护。华多公司未经许可组织主播人员直播涉案游戏,并从直播业务中抽成获利,并非单纯提供网络技术服务,直接侵害了网易公司依法享有的著作权利,应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法院根据侵权期间的毛利润、侵权业务营业收入占比、播放热度等因素估算侵权获利,最终确认赔偿金额为2000万元。[43]
(三)提升企业品牌价值
数字经济的发展提升了互联网企业品牌价值,也促进了新兴互联网企业的品牌培育。加强商标领域的司法保护有利于在复杂的互联网环境中区分商品和服务来源,提升企业竞争力。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通过打击恶意抢注、商标囤积等行为,从而恢复商标应有的识别来源的作用,让品牌权益不被恶意侵犯。例如,在山寨“天猫”一案中,浙江高院审理认为,涉案天猫商标已被相关公众所熟知,可以被认定为驰名商标,被告广东天猫公司及旗下企业和周某注册、使用带有天猫文字的企业名称,并在企业经营和广告宣传中使用的行为构成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判赔150万元。[44]类似地,在“山东腾讯”一案中,济南中院认为“腾讯”商标经过长期使用,达到为相关公众所广为知悉的程度,构成驰名商标。被告山东腾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使用“腾讯传媒"、“腾讯百事通"等标识构成商标侵权,使用“腾讯"企业字号构成不正当竞争,最终被判赔30万元。[45]
在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下,互联网行业的品牌价值逐步提升,市场调查机构的报告显示,过去十年全球增速最快品牌前十名中,阿里巴巴、网易和腾讯分别位列第1、第3和第4,品牌价值提升幅度分别为4029%、2995%和2310%。[46]抖音、拼多多、快手等新诞生的互联网企业,在咨询公司提供的品牌价值排名中也名列前茅。[47]
(四)促进平台经济公平竞争
相比传统行业,互联网行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不正当竞争行为较为普遍,中国法院进一步细化明确垄断和不正当行为的认定标准和规则,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公平参与竞争。[48]
一方面,法院通过一个个典型判例逐步探索网络平台责任体系,在个人信息保护、数据权属、流量劫持等网络知识产权难题上见招拆招,逐步确立互联网企业的权利边界和行为规则,打造有序的互联网竞争秩序。例如通过“3Q大战”[49],工信部发布了《规范互联网信息服务市场秩序若干规定》,要求互联网产品在用户终端上进行软件下载、安装、运行、升级、卸载等操作的,应当事先征得用户同意并提供明确完整的软件功能等信息,禁止欺骗、误导或者强迫用户安装、运行软件;通过“新浪诉脉脉”案,法院确立了个人信息授权的“三重授权”原则[50];通过“大众点评诉百度”案,法院明确数据抓取和数据利用不得“实质替代”原服务[51]等。通过这些判例,各互联网企业逐渐重视个人信息及数据合规,更加合规地开展平台竞争和平台合作。
另一方面,司法机关完善平台经济反垄断裁判规则,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推动平台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早在2008年,唐山市人人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就起诉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被称为我国“网络领域反垄断第一案” [52]。 2017年11月28日,京东向北京高院针对天猫、阿里巴巴提起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诉讼,主张阿里滥用网上零售平台市场的支配地位,实施“二选一”的限定交易行为,被称为“二选一”第一案[53]。面对国内不断加强的反垄断监管态势,互联网企业积极采取行动,2021年7月13日下午,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华为、百度、京东、科大讯飞等33家互联网企业在2021中国互联网大会上《互联网平台经营者反垄断自律公约》,倡议各互联网企业积极推进行业自律,共同创造良好行业竞争环境[54]。
未来,法院可能配合执法机关,依法规范互联网市场主体经营行为,通过司法裁判,促进互联网领域形成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体系,为推动互联网经济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五)保护商业模式创新
中国法院着力通过司法裁判明确网络环境下新类型知识产权的权利属性、保护范围和追责机制,加大司法保护和救济力度,完善知识产权领域治理规则,有效保护和鼓励互联网创新。[55]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2020》白皮书显示,人民法院加大对涉及关键核心技术、重点领域、新兴产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保护激励创新创造。其中,包括从提高侵权赔偿数额、着力降低当事人维权成本等方面,不断提升知识产权民事案件审判质效。例如,越来越多的知识产权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广东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白皮书指出,2020年,广东审结专利案件平均判赔数额63.3万元,同比增长33%,超过1000万判赔的有23件,比三年前翻了一番。
此外,法院采取行为保全、证据保全、惩罚性赔偿、制裁诉讼妨害行为等措施,及时有效阻遏侵权行为,切实降低维权成本,切实保障市场参与主体的合法权益,改善企业营商环境。在“中国好声音”诉前行为保全案中,法院及时采取保全措施,有效避免了有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遭受难以弥补等损害,充分发挥了诉前行为保全的预防救济功能。该案裁定明确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中采取行为保全应考虑因素。[56]
最后,司法保护对互联网行业创新的促进还体现在保护经营者活动和商业模式。作为全国首例社交网络平台不正当竞争纠纷案,“脉脉”非法抓取使用微博用户信息不正当竞争纠纷案,这也是将消费者权益保护作为判断经营者行为正当性依据的典型案件。用户信息是互联网经营者重要的经营资源,如何展现这些用户信息是经营活动的重要内容。保护社交网络平台上的各类用户信息,不仅是互联网经营者开展经营活动、维持并提升用户活跃度、保持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也是广大用户权益的尊重和保障。[57]
[1] 在国外经常被提到的例子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80年的一个判决中认定生物组织产品具有可专利性,随后美国生物技术工业有200多家生物技术公司成立。参见夏道虎:《最严格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理念与实践——基于江苏创新经济发展与司法保护的思考》,《人民司法》2019年第16期,第36-37页。
[2] 参见罗东川:《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背景下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法律适用》2006年第4期,第2页。
[3] 同上,第5页;林广海:《“三审合一”———知识产权案件司法保护新机制述评》,《河北法学》2007年第2期,第182-183页。
[4] 参见王迁:《发达国家网络版权司法保护的现状与趋势》,《法律适用》2009年第59页。
[5] 参见孔祥俊:《当前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几个问题的探讨——关于知识产权司法政策及其走向的再思考》,《知识产权》2005年第2期,第6-7页。
[6]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2018年)》白皮书,第11页。
[7] 参见易继明:《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现状和方向》,《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51页。
[8] 参见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19年中国网络版权保护年度报告》,第12页。
[9] 参见贺荣:《努力开创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新局面》,http://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289751.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1年8月3日 。值得注意的是,贺荣法官并未将三家互联网法院纳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格局当中。
[10] 包括2013-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2020年浙江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分析报告》。
[11] SPSS(Statistical Product and Service Solutions),是统计学中常用的软件,用于统计学分析运算、数据挖掘、预测分析和决策支持任务等。
[12] Pearson相关系数(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是用来衡量两个数据集合是否在一条线上面,它用来衡量定距变量间的线性关系。pearson相关系数衡量的是线性相关关系。若r=0,只能说x与y之间无线性相关关系,不能说无相关关系。相关系数的绝对值越大,相关性越强:相关系数越接近于1或-1,相关度越强,相关系数越接近于0,相关度越弱。通常情况下通过以下取值范围判断变量的相关强度:相关系数 0.8-1.0 极强相关,0.6-0.8 强相关,0.4-0.6 中等程度相关,0.2-0.4 弱相关0.0-0.2 极弱相关或无相关。
[13]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2019年)》。
[14] 《优化创新法治环境 服务科技自立自强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技术类案件审判工作概览》,参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官网:http://bjzcfy.chinacourt.gov.cn/article/detail/2021/05/id/6023896.shtml。
[15] 同上。
[16] 对于非网络知识产权案件的管辖优化问题上,我国最高人民法院还设立了24家跨区知识产权法庭。
[17] 参见王胜明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释义》,法律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79 页。
[18] 参见寇颖娇、吴献雅:《涉网络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的地域管辖问题研究——以<民诉法司法解释>第25条为中心》,《法律适用》2018年第5期,第115页。
[19]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0年12月23日修订)第25条。
[20]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查知识产权纠纷行为保全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新闻发布会发布稿》
[21] 浙江高级人民法院《2020年浙江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分析报告》。
[22] 当然,出现这种结果部分原因也在于我国知识产权案件尤其是涉及行政和刑事程序的案件的诉讼审理程序的不统一。参见参见肖海棠:《关于知识产权审理模式的探析与思考——以广东知识产权审判为视角》,《电子知识产权》2006年第9期,第46-47页。
[23] 《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情况的报告》,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2006-07/25/content_5350729.htm ,最后访问时间2021年8月3日。
[24] 《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情况的报告》,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2014-08/22/content_1879714.htm ,最后访问时间2021年8月3日。
[25] 参见邢丙银:《破解“赢了官司丢了市场”,专家建议知识产权案依市场价值赔》,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4/23/c_128924486.htm 。
[26] 参见蒋华胜:《民营企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中的关键性问题探析——基于G法院的实证数据分析》,《河北法学》2017年第11期,第187-189页。
[27]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2016年)》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7/04/id/2825053.shtml ,最后访问时间2021年8月3日。
[28] 参见《广东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白皮书(2018)》。
[29] 有学者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白皮书发现,在2017-2019年三年的知识产权一审案件数量年均增长40%以上,而法院每年的审结率也在40%左右,由此反映了司法是我国知识产权纠纷的主要解决渠道,而且我国法院的司法审判水平比较高。参见夏存霞、陈华:《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研究》,《科技传播》2020年第11期,第45页。
[30] 参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官网:https://www.wipo.int/pressroom/en/articles/2020/article_0005.html。
[31] 参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官网关于中国专利申请数量的统计报告:https://www.wipo.int/ipstats/en/statistics/country_profile/profile.jsp?code=CN。
[32] 参见徐剑:《网络版权侵权诉讼中的地方司法保护实证分析》,《现代传播》2017年第1期,第113页。
[33]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
[34] See WIPO,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20, p. vii.
[35] Id, p. xxiii.
[36] Id, p. xxvi.
[37] 艾媒咨询发布的《2020中国独角兽企业T100榜单》显示,北京、上海、深圳分别是独角兽城市分布的第一梯队,在TOP100独角兽中占74%,这些独角兽企业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互联网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领域。参见艾媒网:《2020中国TOP100独角兽企业发展现状、机遇与挑战分析》,https://www.iimedia.cn/c1020/70518.html ,最后访问时间2021年8月3日。
[38] 参见中国知识产权:《中国互联网100强企业发明专利排行榜发布》,载http://www.chinaipmagazine.com/journal-show.asp?3028.html,最后访问于2021年8月5日。
[39] 参见中国互联网协会《中国互联网企业综合实力研究报告(2020)》。
[40] 参见科学网:《《2020人工智能中国专利技术分析报告》发布》,载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20/11/448513.shtm,最后访问于2021年8月5日。
[41] 参见国家知识产权局《2020中国专利调查报告》。
[42] 参见《中国网络版权产业发展报告(2020)》。
[43] 参见(2018)粤民终137号民事判决书。
[44] 参见人民网:《男子注册17家山寨“天猫公司” 二审判赔150万元》,载http://ip.people.com.cn/n1/2019/0411/c179663-31024703.html,最后访问于2021年8月4日。
[45] 参见(2018)鲁01民初2104号民事判决书。
[46] 参见《Brand Finance 2020年中国品牌价值500强》。
[47] 参见《2020年BrandZ最具价值中国品牌100强排行榜》。
[48]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法院的互联网司法白》白皮书。
[49] 参见(2013)民三终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
[50] 参见(2016)京73民终588号民事判决书。
[51] 参见(2016)沪73民终242号民事判决书。
[52] 参见董慧娟:《对我国网络领域反垄断第一案的再思考》,载《河北法学》2011年第1期。
[53] 参见澎湃网:《京东诉天猫及阿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二选一”第一案将开庭》,载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0152878,最后访问于2021年8月4日。
[54] 参见新浪网:《33家互联网平台签署行业反垄断自律公约,阿里腾讯字节在列》,载https://www.sohu.com/a/477448990_161795,最后访问于2021年8月4日。
[55]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法院的互联网司法白》白皮书。
[56] 参见2016年度北京市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典型案例,载http://bjgy.chinacourt.gov.cn/article/detail/2017/04/id/2820793.shtml。
[57] 参见2016年度北京市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典型案例,载http://bjgy.chinacourt.gov.cn/article/detail/2017/04/id/2820793.s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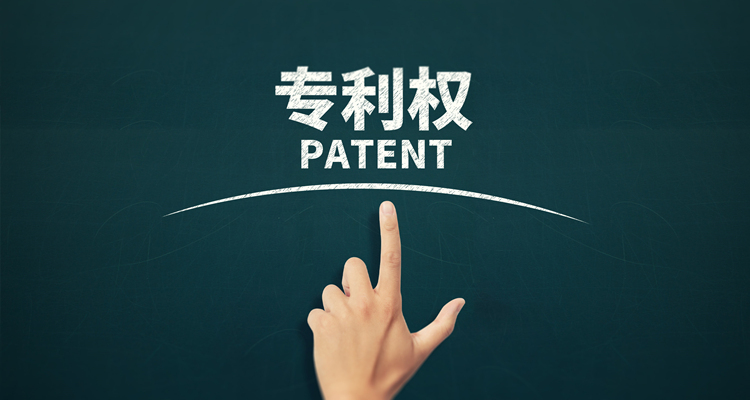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9464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946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