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 乐[1] 法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涉外法治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内容摘要:涉外标准必要专利全球许可费率裁决的管辖权争议涉及我国法院对于案件本身是否具有管辖权以及在此基础上能否裁决全球许可费率两个层面的问题。标准必要专利许可模式的全球性除了让全球许可费率具有合理性,也使得纠纷呈现出与多法域的关联性,由此造成平行诉讼频发。伴随法院对严格地域管辖的突破,不同法域之间的管辖权冲突进而加剧。这种对诉讼优选地的争夺体现了标准必要专利纠纷关涉利益的复杂性和重要性。中国法院一方面通过典型案例确立法院对标准必要专利全球许可费率裁决具有管辖权,另一方面通过《民事诉讼法》涉外编的修订为法院在此类案件中行使积极的管辖权创设了更为多元的依据和灵活的空间。
关键词:标准必要专利;全球许可费率;管辖权
标准必要专利(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简称SEPs)许可纠纷是典型的涉外法治问题。其不仅关涉FRAND(Fair, Re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性质及内涵认定、禁令授予、市场支配地位滥用等实体法问题,而且涉及法院管辖权确定、禁诉令签发等程序法问题。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的依据和视角涵摄两对关系:内国法与外国法,国内法与国际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企业作为SEPs纠纷的主要当事方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与此相关的中国立法和司法也逐渐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不仅是观照上述问题的背景,更需要成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向和路径。特别是全球许可费率的管辖权争议,对这个问题的深入分析和妥善解决不但是我国涉外SEPs纠纷裁判规则的必要组成,而且是我国在涉外知识产权领域打造积极灵活的程序规则从而型构全球诉讼优选地的当然要求。
一、SEPs全球许可费率裁决中的管辖权争议
全球许可费率裁判所引发的争议不仅关涉法院对FRAND承诺及其实现的解释,而且涉及法院对该事项具有管辖权的正当性证成。通过“无线星球诉华为”案[2]和“康文森诉华为与中兴”案[3],英国法院确立了其裁判SEPs全球许可条件的可能性、必要性以及正当性。然而,英国法院对全球许可费率裁决的确立也引发了关于其打造“事实上的国际或者全球电信许可法庭”的争议。就在英国最高法院就裁判全球许可条件作出肯定性终审判决后不久,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OPPO诉夏普”案[4]的上诉审中作出终审判决,肯定了中国法院裁决SEPs全球许可费率的管辖权及其正当性。在此前后,美国、法国、荷兰等SEPs纠纷的主要司法管辖区法院也在相关案件中表明其对于全球许可费率管辖权的态度。例如,美国在“PanOptis诉华为”案[5]和“TCL诉爱立信”案[6]中强调当事人达成管辖合意是裁决SEPs全球许可费率的前提。美国法院由此也被认为在行使全球许可费率管辖权上态度较为保守。[7]法国法院与荷兰法院则分别通过“TCL诉飞利浦”案[8]和“Vestel诉飞利浦”案[9],以属地管辖原则确认其有权行使管辖权。相较而言,英国和中国这两个司法管辖区对于行使全球许可费率的管辖权态度更为积极。而这种积极也导致管辖权争议不再仅仅关涉某个特定法院在行使管辖权时是否具有充分的正当性,开始涉及不同国家或地区法院之间在行使管辖权时的冲突。OPPO与诺基亚之间的纠纷就体现了这样的冲突。
近年来,OPPO与诺基亚因就SEPs许可谈判未能达成一致在全球各地发起诉讼,并分别于中国、英国提起全球许可费率之诉。2021年7月1日,诺基亚在双方于2018年签订的许可协议到期后率先向英国英格兰与威尔士高等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认定其报价符合FRAND原则,而后于2022年变更诉讼请求为英国法院确认涉案SEPs全球许可费率。同月12日,OPPO向中国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就其所需获得的全部SEPs确定符合FRAND原则的全球许可使用费率,[10]诺基亚就此提出管辖权异议。同年8月,OPPO以英国高等法院非案件审理的方便法院为由提出管辖权异议,并请求英国法院中止审理,待中国法院作出判决后再行审理。由此,英国法院和中国法院谁来行使管辖权便出现争议。
本案中,OPPO提出,相较于“无线星球与华为”案,中国法院已经作出其具有全球许可费率的管辖权裁定,且欧盟法律不再适用英国,国际背景已然发生变化。且根据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管辖规则,本案中审理全球许可费率的方便法院应为中国法院。但英国法院认为诺基亚在本案中的主张与“康文森诉华为”案、“中兴诉康文森”案的主张及案件争议定性方式完全相同。由于本案中的争议以同样的方式被恰当定性[11],英国法院并不认可案件背景发生变化。英国法院认为其为审理该案件的方便法院,据此驳回管辖权异议与中止审理的请求。[12]同样,诺基亚的管辖权异议最终也被我国最高人民法院裁定驳回。[13]该案中,面对当事人的请求,两国法院均援引不方便法院原则确立其管辖权。不方便法院原则的一项重要功能是限制原告任意挑选法院造成被告不便及浪费司法资源的滥用诉权行为,从而有效地协调国际民商事管辖权冲突。[14]但在本案中,两国法院对这一原则的解读显然不同,而这也是引发管辖权冲突的重要原因。
此外,SEPs全球许可费率管辖权争议可能还会因为当事人申请签发禁诉令而进一步激化。在“小米诉交互数字公司”案[15]中,小米公司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裁定其与交互数字公司涉案SEPs全球许可费率诉请同时又提出行为保全请求,法院据此签发禁诉令,裁定交互数字公司在其审理期间不得向其他国家和地区法院提起与小米公司之间的SEPs许可费率诉讼或执行相关裁决。这一禁诉令裁决随后引发德国和印度法院作出反禁诉令裁决予以回应。与之相关的一系列禁诉令裁决也引发欧盟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对中国做法是否符合《TRIPS协定》及入世承诺的挑战。[16]由此,今天我们看到,SEPs全球费率的裁决及其相关争端已经不再仅仅是国内民事诉讼法范畴的问题,而是涉及外国法(实体法与程序法)与国际法(包括国际公法意义上的一般法律原则的违反,国际私法意义上的管辖权冲突、国际礼让与司法协助,国际经济法意义上的《TRIPS协定》一致性)的争议话题。
二、SEPs全球许可费率裁决缘何引发管辖权争议
有别于一般的涉外民商事案件的管辖权争议,SEPs全球许可费率裁决的管辖权争议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案件的涉外因素带来的管辖权问题,另一个是全球许可费率裁决的管辖权,即当法院在第一个问题上确认管辖权后需要证成其可以裁决涉案SEPs在全球范围内的许可费率,而不是在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费率。对于第一个问题而言,问题的解决取决于法院适用什么样的管辖权依据。在“康文森诉LG”案[17]中,面对康文森确定涉案SEPs组合包全球许可费率的请求,法国法院认为并无必要确定该案的FRAND全球许可费率。包括荷兰在内,这些国家的法院之所以在相关案件中拒绝对缺乏当事人合意的全球许可费率进行裁决主要缘于其所依据的属地管辖原则。所谓属地管辖,是以涉外民商事案件与某一国地域上或者空间上的联系作为确定管辖权的依据。与各国通行做法一致,我国《民事诉讼法》将被告住所地作为最基本管辖根据,即“原告就被告”的一般地域管辖原则,于第22条规定:“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18]这种管辖权的属地性是国家主权权力的具体体现,它们拥有一个共同的逻辑起点:所有类型的管辖权都是属地的,首先及于本国境内的人、行为和财产,若无国际法上的特别理由,国家不可以行使域外管辖权。只不过在实践中,各国立法管辖和司法管辖均不同程度地超越了属地原则。[19]随着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 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得到普遍承认,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打破知识产权的严格地域性管辖。[20]在SEPs领域,随着英国法院就“无线星球诉华为”案积极裁决全球许可费率,严格地域性管辖也随之开始松动。
超越属地原则积极行使管辖权在确定SEPs全球许可费率这一特殊诉请上会进一步加剧争议的复杂性。众所周知,知识产权作为一国法律承认和保护的相关权利,其效力只限于本国境内,具有严格的地域性或称领土性。[21]作为一国行使公权力,基于国家行为所赋予认可的专利,其空间效力范围也限于所授予权利国家的领土范围。似乎属地管辖与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存在天然的一致性。而许可模式的全球性打破了这种逻辑上的关联。全球许可费率裁决之所以造成管辖权问题是因为全球许可模式增加了纠纷跟不同地域之间联系的因素。问题在于,全球许可在实践中很普遍。在“圣劳伦斯诉沃达丰”案[22]中,原告作为证据提交的55份许可协议中有53份是全球许可协议。德国杜塞尔多夫地区法院对此采信并认为,全球许可符合商业惯例,标准实施者在全球范围内经营,并总是签订全球许可协议。特别是在电信行业,签订全球许可协议是通常做法。如果SEP权利人最终被迫只签订一国的许可协议,这将与上述全球许可的商业惯例相悖。德国联邦法院于2020年在“西斯福诉海尔”案[23]中也曾指出,全球专利组合许可谈判是普遍性做法,从效率角度也有利于被许可人。[24]这种许可模式的全球性使得案件争议与多国发生联系,由此也制造了多元连接点,如许可协议磋商地、专利授予地、当事人住所地等,这使得不同国家或地区法院能够找到行使管辖权的依据。
除了立法规定和司法考量上的差异性,SEPs纠纷解决对于经济、科技乃至国家利益的意义也是管辖权争议背后的重要因素。美国一贯奉行积极的司法管辖原则,并发展出成熟的涉外管辖体系。这背后当然有利益本位的考虑。即使像英国这样的国家,尽管其并非拥有强大SEPs实力的科技巨头母国,但是打造全球争议解决中心背后的国家利益考量不能不说是英国法院在相关案件中积极作为的重要动力。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SEPs权利人或标准实施者而言,在本国诉讼都是其首要选择。除了争议解决成本上的考虑,费率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其经济利润以及在相关市场的竞争力。从这个意义上说,SEPs全球许可费率的管辖权除了具有个案意义,更带有这个特殊领域深刻而复杂的利益属性。因此,当国际知识产权争端越来越成为企业乃至国家之间科技竞争没有硝烟的战场,涉外知识产权民事诉讼领域对纠纷管辖权的争夺也愈加激烈。[25]
三、SEPs全球许可费率裁决管辖权争议的中国因应
面对SEPs全球许可费率裁决管辖权争议,中国在相关案件中形成与其他司法管辖区相比兼具共性和特性的裁判规则,并在此基础上推进相关立法做出调整,由此形成较为完备的因应体系。作为全球许可费率裁决方面颇具影响力的判例,英国法院在“无线星球诉华为”案采取了不同于美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管辖权进路,并提出相应裁判理由。法院认为:ETSI的知识产权政策赋予了其裁决全球许可费率的权利;SEPs许可本身属于合同问题,而英国法院对该合同具有管辖权;英国法院并没有剥夺当事人寻求外国法院裁决涉及外国专利有效性、必要性以及其中侵权问题的机会;法院行使管辖权对全球许可费率进行裁判符合商业惯例;根据中国法律规定与司法实践,并不能确定中国法院对SEPs全球许可费率具有管辖权。基于上述考虑,英国法院认为其有权确定SEPs全球许可费率,且为审理的方便法院,而后延续此案所确定的管辖。
相比而言,中国法院则确立了自身关于裁决全球许可费率具有管辖权的裁判规则。2020年开始,中国法院陆续通过“OPPO诉夏普”案、“OPPO诉交互数字公司”案[26]以及“OPPO诉诺基亚”案[27]等形成了其关于管辖权的裁判规则。首先,中国法院就针对案件本身是否具备管辖权进行分析。此类案件纠纷作为特殊的合同纠纷,在判断时应当考虑被告所在地、代表机构所在地、专利授予地、专利实施地、专利许可合同签订地或专利许可磋商地、可合理预见的缔约后专利许可合同履行地、可供扣押或可供执行财产所在地等。若任意择一在中国域内,即认定案件与中国存在适当联系,中国法院对该案件本身具有管辖权。其次,中国法院需判断是否适宜对涉案SEPs在全球范围内许可条件作出裁决。在当事人具备达成全球许可的意愿且纠纷与中国具有更密切联系时,中国法院可以裁决全球许可费率。即便当事人未达成管辖合意,中国法院仍有权依一方当事人的申请,对涉案SEPs全球许可条件进行裁决。若专利持有人与标准实施者的谈判内容包含了SEPs在全球范围内的许可条件,则说明双方磋商时就SEPs许可的意愿范围为在全球范围内。法院同时提出,对更密切联系规则则应综合判断,考虑:SEPs授予国及其分布比例、标准实施者的主要实施地、主要营业地或者主要营收来源地、专利许可磋商地或专利许可合同签订地、可供扣押或可供执行财产所在地等因素,认定其与中国法院是否具有更密切的联系。在中国法院对该案件具有管辖权的基础上,法院进而认定有权对涉案SEPs在全球范围内的许可条件作出裁决。
除了在司法上积极行使管辖权,通过修订《民事诉讼法》涉外编的规定,我国立法通过进一步明确处理涉外案件的程序规则也为法院行使管辖权提供了依据。新《民事诉讼法》通过调整涉外管辖案件原有的连接点,适度扩大了对涉外民事纠纷的管辖权。在原有的连接点基础上,立法新增“存在其他适当联系”的案件连接点。“适当联系”原则是一种谦抑性的保护性管辖,其强调实施管辖的必要性、适度性与合理性,采取“特定依据+兜底条款”的模式。[28]这一兜底条款使得我国法院未来可以突破合同签订地、履行地、诉讼标的物所在地、可供扣押财产所在地、侵权行为地、代表机构住所地等六项连接点,在其他联系与前述连接点之间具有相当性的前提下行使管辖权。这对于法院审理涉外SEPs许可纠纷无异于创设了更加积极灵活的管辖依据。与此同时,新《民事诉讼法》在第279条第2项增列“因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审查授予的知识产权的有效性有关的纠纷提起的诉讼”为专属管辖事项。这被认为进一步丰富了民事诉讼的专属管辖制度,更加有效地适应知识产权领域的新情况、新要求。[29]未来不排除涉外SEPs许可纠纷当事人因提出涉案专利有效性而导致中国法院对此行使专属管辖权的可能。
除扩大法定管辖的范围,新《民事诉讼法》还就协调管辖权国际冲突和减少平行诉讼作出专门规定。新《民事诉讼法》在吸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22〕11号)第531条以及《第二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0条关于平行诉讼规定的基础上新增第280条,规定:“当事人之间的同一纠纷,一方当事人向外国法院起诉,另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一方当事人既向外国法院起诉,又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依照本法有管辖权的,可以受理。当事人订立排他性管辖协议选择外国法院管辖且不违反本法对专属管辖的规定,不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安全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 换言之,对于当事人之间的同一纠纷,无论是重复诉讼还是对抗诉讼,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有管辖权的,即可予以受理,并不受当事人是否已向外国法院提起诉讼的影响。由于涉外SEPs纠纷极易引发平行诉讼,这一规定为我国法院就当事人请求裁定全球许可费率的案件行使管辖权提供了更加明确的依据。与此同时,为体现司法礼让原则,新《民事诉讼法》又规定了平行诉讼中的中止诉讼制度,即法院行使管辖权后,可以考虑外国法院受理在先之平行诉讼等因素,裁定中止诉讼。当然,对于是否中止,法院享有自由裁量权。另外,如果当事人之间存在选择我国法院管辖的协议、纠纷属于我国法院专属管辖或者纠纷与我国具有密切联系等因素,由我国法院审理更加方便的,人民法院则不应裁定中止诉讼。[30]综合来看,上述规定还是体现了对涉外案件积极行使管辖权的立场和导向。可以预见,未来法院在裁定是否受理涉外SEPs纠纷时将拥有更加灵活的空间和更为多元的管辖权依据。这有助于减少法院在行使管辖权时因缺乏明确的立法依据而受到的质疑。
结 论
总之,妥善应对涉外SEPs全球许可费率裁决的管辖权争议具有必要性和重要性。一方面,对管辖权争议的司法回应并进而确立法院的管辖权既是在个案意义上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的基本前提,也是我国维护主权和发展利益的根本要求。另一方面,对管辖权争议的处理是我国SEPs纠纷裁判规则的组成部分。在确立管辖权的前提下,我国法院才能在FRAND费率确定、禁令授予、滥用认定等实体法问题上形成日臻完善的裁判规则,并由此确立SEPs纠纷的全球诉讼优选地。积极的管辖制度既是我国展现法治自信的应有之意,也是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必然要求。
注释:
1.本文是作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标准必要专利国际平行诉讼中的禁诉令问题与中国对策研究”(23YJC820023)阶段性成果。
2.See Unwired Planet v. Huawei, [2018] EWCA Civ 2344.
3.See Conversant v. Huawei & ZTE, [2019] EWCA Civ 38.
4.参见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粤03民初字第689号民事裁定书。
5.See Optis Wireless Tech., LLC. v. Huawei Device Co., Ltd., 2018 WL 476054 (E.D. Tex. 2019).
6.See TCL v. Ericsson, the U.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Central District of California, CV 15-2370 JVS (DFMx).
7.参见宁立志、龚涛:《标准必要专利全球费率裁判:实践、争议与对策》,《北方法学》2022年第3期。
8.See TCL v. Philips, Case No. RG 19/02085.
9.See Vestel Germany GmbH v. Koninklijke Philips N.V, Case No. C/09/604737/ HA ZA 20-1236.
10.参见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1)渝01民初1232号民事判决书。
11.祝建军:《英国法院重申SEP全球许可条件管辖规则——评诺基亚诉OPPO案》,载《知产财经》2021年11月29日。
12.See Nokia v. OPPO, [2021]EWHC 2952(Pat).
13.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知民辖终167号民事裁定书。
14.参见沈红雨:《我国法的域外适用法律体系构建与涉外民商事诉讼管辖权制度的改革——兼论不方便法院原则和禁诉令机制的构建》,《中国应用法学》2020年第5期。
15.参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粤01知民初169号之一民事裁定书。
16.See WT/DS611/5, China-Enforc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9 December 2022.
17.See Core Wireless v. LG, Case No. 14/14124.
18.参见沈红雨:《我国法的域外适用法律体系构建与涉外民商事诉讼管辖权制度的改革——兼论不方便法院原则和禁诉令机制的构建》,《中国应用法学》2020年第5期。
19.参见宋晓:《域外管辖的体系构造:立法管辖与司法管辖之界分》,《法学研究》2021年第3期。
20.See William Cornish, David Llewelyn & Tanya Apl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Patents, Copyrights, Trademarks and Allied Rights, Sweet & Maxwell, 2010, p. 28.
21.吴汉东:《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25页。
22.See St Lawrence v. Vodafone, 4a O 73/14 (2016).
23.See Sisvel v. Haier, KZR 36/17 (2020).
24.参见马乐、孔晓婷:《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商业惯例的司法意涵与功能实现》,《科技与法律(中英文)》2023年第1期。
25.仲春:《标准必要专利全球费率裁判思辨》,载《知识产权》2020年第10期。
26.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3)最高法知民辖终282号民事裁定书。
27.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知民辖终167号民事裁定书。
28.参见沈红雨、郭载宇:《<民事诉讼法>涉外编修改条款之述评与解读》,《中国法律评论》2023年第6期。
29.同上。
30.同注释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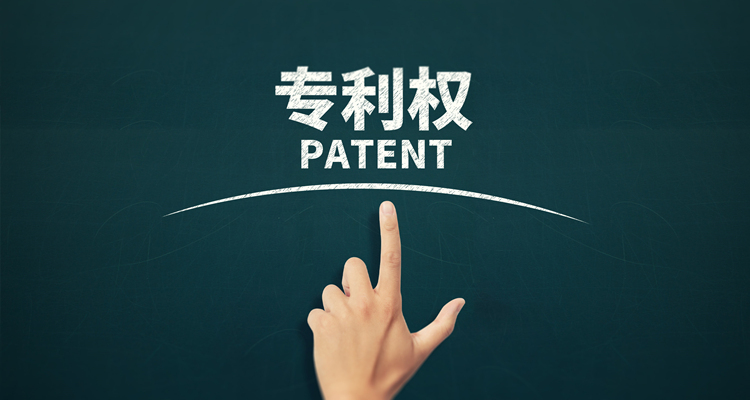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9464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946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