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 明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摘 要:
主张采用拆分保护路径是近年来在网络游戏著作权保护问题上的多数派观点。但是,该主张并不能消除一直以来围绕网络游戏著作权保护所产生的争议,诸如作品类型例示究竟应为开放式抑或封闭式、游戏规则能否获得著作权保护等,同时拆分保护路径也缺乏必要性与适用空间,还会导致司法效率的降低。所以,有必要回到著作权赋权的基本原理,以之为基础构建恰当的认知作品及作品类型的著作权客体理论,藉此认识网络游戏在著作权客体体系中的独立存在具有正当性和必要性。与之相应地,网络游戏在现行法下可按照《著作权法》第3条(九)项“符合作品特征的其他智力成果”来定性。进而可知,作品构成要件尤其是独创性要件的分析框架足以支撑网络游戏著作权采取整体保护的路径。整体保护观有利于法官正确理解相关规则、选择恰当的裁判逻辑,在涉网络游戏的著作权侵权案件中有效解决“公与私”“此权与彼权”的界分,很好地回应“游戏规则能否在网络游戏著作权之下得到保护”等引发激烈争议的问题。
一、网络游戏著作权侵权纠纷引发的争议及反思
在近些年著作权法的司法实践中,恐怕没有什么能比网络游戏的著作权侵权纠纷更加吸引各界关注与引发激烈争论了。综观诸多争议,网络游戏著作权侵权纠纷映射出人们在两个问题上的分歧,一是对网络游戏的基本认知,另一是网络游戏著作权的保护路径;前者属于著作权客体理论范畴的问题,后者则是以前者为前提的,不同的客体认知观对应着不同的网络游戏著作权保护路径。透过作为分析对象的网络游戏,前述争议实际上反映出各界对“是否构成作品与作品类型之间是否有对应关系”“作品类型与著作权保护模式之间有何逻辑关联”等问题存在不同观点。
对作品类型的执着在我国著作权法领域不只是体现在学术争论和司法实践之中,历次修法时该议题也都是讨论的重点。直至2020年我国第三次修订《著作权法》,第3条第(九)项之规定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调整为“符合作品特征的其他智力成果”,似乎为之前的争议画上了句号。表面上看,《著作权法》的“作品类型条款”真正地成为了开放式规定,其所列明的诸作品类型不过是人们具有共识的示例,那些未被类型化进而被明确列举的文学、艺术或科学领域的表达,并不妨碍其获得著作权的保护。
然而实际情况却并不像期待的那样,各界针对“应当如何理解和适用兜底条款”“作品类型的规定是否应采开放模式”“兜底条款是否应当保留”等问题仍然争论不断。这与近些年来频频发生的关于网络游戏、音乐喷泉、静态画面等客体的著作权侵权纠纷是密切相关的,也反映出“确定作品的类型”在很多人看来仍然是侵权救济展开的基本前提,故而人们仍十分看重对“非例示类型之表达是否能归入例示类型作品”的探讨。但在笔者看来,“作品类型决定著作权保护路径”的认知逻辑是不无疑问的。
对此笔者认为,作品类型与著作权保护路径一一对应的逻辑并不存在、亦无必要。在作品类型的问题上选择何种立法模式,本质上即是一个公共政策选择的问题。至于著作权的保护路径,具体展现为司法裁判中判断侵权行为是否成立的逻辑和思路,具有方法论意义。所以,从满足著作权侵权裁判之需的角度来说,研究保护路径所努力的方向不应当是多元化,“提取公因式”才是类型化的意义之所在。
毫无疑问,著作权法上对作品类型的例示不可能做到穷尽,而对作品例示持封闭态度与排斥将任何新的表达形式纳入著作权的保护范畴又并不能划等号,那么相较于对作品范围采开放态度(当然要符合作品的本质特征),前者所带来的问题恐怕一点也不少,原因在于,如果“法官是否会扩张解释既有作品类型”具有不确定性,这将对当事人产生逆向激励,从而造成社会福利的无谓损失。
二、著作权客体理论对网络游戏的审视
基于以上之分析我们再来审视网络游戏所引发的激烈争议,如果只是以“对于作品类型的例示应采封闭式立法模式”为依据,显然无法达到“定分止争”的效果,这也反映出著作权法领域实际上是缺乏权利客体理论共识的。为了应对这一情形,我们不妨从著作权赋权的基本原理入手,构建恰当理解作品以及作品类型的著作权客体理论,进而在此理论框架下就包括网络游戏在内的特定表达的定性形成共识。具体可从以下两方面展开:
1、著作权赋权原理对著作权客体认知的影响
理论界一般是从构成要件的角度来理解作品的,众所周知,“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的表达”“独创性”“以某种形式表现”即是用以界定作品的基本元素。尽管构成要件已如此明确,似乎不应当再有“如何理解作品”的疑惑和争论,然而实际情况是人们围绕“作品的范围该有多大”争论不休。直观看来,根据“作品的定义”所确立的构成要件,“作品的范围”即是由符合该定义的全部表达所形成的集合;但是,如果在二者之间附加一定的价值判断,【1】“作品的定义”和“作品的范围”就成为并不一致的两个范畴,后者只是前者的一个子集。这里所谓的价值判断即是公共政策选择,在其作用下,特定的表达形式即使满足了作品的全部构成要件,也将被排除在作品的范围之外,此即“作品范围应采封闭模式”的完整阐述。然而,支持封闭模式者大多都未能清晰地揭示该模式背后的公共政策选择,【2】以至于作品类型例示的法律意义及其背后的理论考量是含糊不清的。所谓公共政策,是指连接个人行为和集体选择从而实现社会效用最大化的利益分配方案。在著作权法领域,个人行为对应的是创作行为,而集体选择则是指非权利人(既包括作为作品消费者的社会公众,也包括利用在先作品从事累积性创作的主体)的行动方案,故著作权法领域的公共政策选择体现为通过对两组概念“在先作品与在后作品”“创作者与使用者”的界分,为作为商品的作品确立适当的市场控制力。【3】
由此我们不难明白,著作权赋权本质上是围绕市场竞争而展开的,而赋权旨在解决一部作品到哪里为止,而另一部作品又从哪里开始。【4】作为抽象财产的法律描述,著作权的客体(作品)对应的是一个开放性的体系,方能满足不断发展的文学财产市场化的需要。
2、从著作权客体理论出发对网络游戏的审视
一如前述,有关作品类型及其与著作权保护路径的不同认知,造成了我国司法实践在著作权侵权认定思路的问题上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混乱。而要消除这种混乱,就应当破除“受保护之表达与作品类型之间存在一一对应关系”的错误认知,表达形式的“有名化”是对约定俗成的文化产品市场的“经验归纳与展示”,藉此降低市场主体的交易成本与司法救济中的法律适用成本,但其并非著作权客体理论的应有内容。因此,著作权客体是与文化产品市场相对应的概念,著作权法采用对作品下定义的方式明确了如何界定文化产品市场:“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是对市场范围的限定,“独创性”和“以某种形式表现”是对能够商品化的作品的内在要求。根据这一客体理论,当一种新的文化产品市场出现时,对于该市场中作为交易对象的、已被商品化的表达形式,我们不难判断其是否属于应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
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再来看网络游戏。根据《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2010)的规定: “网络游戏是指由软件程序和信息数据构成,通过互联网、移动通信网等信息网络提供的游戏产品和服务。”【5】可以看出,此概念的涵摄范围非常宽泛,因而也能反映出网络游戏产品的复杂性。自端游时代起步发展至今,我国网络游戏产业已经发展到用户6.64亿人、2022年实际销售收入2658.84亿元的规模,【6】基于网络游戏作品已然形成了十分复杂的产业链,【7】相关产品市场的成熟度毋庸置疑,甚至该产业的发展已经开始进入存量市场时代。所以,若从“是否已形成市场”“是否有解决市场竞争的需要”两方面来考察,对网络游戏进行著作权赋权的物质基础是非常充分的,而某一具体的游戏开发成果是否能产生著作权,则需要根据作品构成要件逐一展开判断。
何谓游戏?本质上其是指各种不同形式的互动性的娱乐行为,很显然这是一个非常抽象、包容性极强的概念。与过去习惯按照创作方式来类型化作品不同,网络游戏并不与特定的创作方式相对应(即便都是以“网络”的方式来承载和运行),这是因为不同游戏要展现的内容各不相同。网络游戏产业中更习惯按照不同的玩法来划分产品,其所包含的种类繁多,诸如剧情类、战术竞技类、射击类、策略类,以及棋牌类、音乐类、体育竞技类或其它休闲类,此外还有融合类型。
不论是何种类型的网络游戏,我们从作品构成要件的角度来分析时不难发现,是否满足“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的表达”“独创性”“以某种形式表现”的判断并不十分困难。而由于与娱乐相对应的偏好是多样化的,针对不同偏好的网络游戏彼此间在创作方式上差异甚大,所以,将网络游戏归入任何一种我们所熟悉的文学艺术或科学形式都是不适宜的,而《著作权法》第3条所例示的作品类型均与特定的创作方式对应。举例来说,剧情类游戏通常被界定为视听作品(《著作权法》2020年修订前称为类电作品)予以保护,【8】而将棋牌类游戏定性为计算机软件更为恰当。可见,网络游戏实际上是一个类概念,用以统称所有借助互联网来承载和驱动的、可以被称之为游戏的产品,与文字作品、美术作品等典型的作品例示类型相比差异显著。
综上所述,网络游戏更像是一个产业形态而非作品形式的概念,其与产品更为接近,或者说无所谓称之为作品还是产品;文字作品则不同,与之对应的典型产品是图书,但图书与文字作品之间显然是界限分明的。因此,网络游戏在著作权客体体系中独立存在具有正当性和必要性,尽管这一认知在现行法框架下尚未取得共识,那么一个暂时的替代方案是根据《著作权法》(2020)第3条“(九)符合作品特征的其他智力成果”来定性网络游戏。
三、网络游戏著作权的整体保护观
基于网络游戏的类概念特性,此类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必然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应当适用整体保护还是拆分保护的裁判思路?在我国的著作权法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长期习惯于按照作品的创作方式来确定某种作品的著作权保护模式,如果作品的创作过程中涉及多种方式的运用,即对其进行拆分,按照各种不同的创作方式将该作品拆解为文字作品、音乐作品、美术作品、视听作品等,进而按照拆解所得之作品类型,分门别类地保护其著作权。遵循这一思维习惯,网络游戏著作权采取拆分保护的路径似乎是顺理成章的,因为根据网络游戏所包括的诸多类型来看,其所涉及的创作方式基本上可以与《著作权法》第3条所例示的作品类型全部对应起来,拆分路径似乎更有利于在侵权判定时化繁为简。但在笔者看来,拆分保护实际上与著作权赋权原理不符,同时也是一种降低司法效率的做法。我们不妨区分网络游戏的不同创作情形来展开讨论:
情形1:网络游戏是基于诸多在先作品——例如剧本、角色形象、音乐等——创作而来。首先需要明确分析的前提,即侵权行为不是针对这些在先作品的单独使用,否则就不涉及网络游戏的问题了。此时,如果在著作权侵权诉讼中采用拆分保护的路径,相当于否认了网络游戏独立存在的必要,因为侵权判断是以对网络游戏的解构为始点的。从著作权赋权与解决市场问题之间的紧密关系的角度来看,这种保护路径因偏离了游戏市场本身的问题而与赋权原理是不相符的。更重要的是,解构主义的侵权判定思路将网络游戏的著作权保护问题复杂化了:其一,由于网络游戏是基于在先作品创作出来的,对之进行拆分之后,就只剩下计算机程序、静态画面、以及这些画面的连续动态组合了,因而网络游戏自身的独创性只可能体现在这些剩下的元素之上,那么,如果被诉侵权行为仅针对在先作品,网络游戏开发商实际上并不享有提起侵权诉讼的请求权;其二,如果被诉侵权行为使用的是连续动态画面,虽然画面与剧本等在先作品之间的区分完全不存在认知上的困难,但此时又有什么必要在侵权判定之前先进行拆分呢?其三,如果被诉侵权行为使用的是静态画面,由于这些画面属于网络游戏整体表达的组成部分,因而只需将“案涉画面是否构成游戏的实质内容”作为侵权判定的关键问题,即能得出裁判结果,同样不需要采用拆分保护的思维模式。在此方面,电影作品与网络游戏其实是一样的,静态画面有可能构成电影作品整体的实质内容,国外也有过秉持该观点的判决。【9】可是,更多的人主张采用拆分路径来保护电影作品的著作权,进而将这一保护路径延用到了网络游戏之上,而其实在电影作品的问题上可能一开始就走偏了。
情形2:网络游戏并非依据在先作品,而系直接创作所得。此时,诸如音乐、形象设计、图案等嵌入式元素同样很容易从整体游戏剥离出来,游戏开发商和这些元素之间的关系与情形1并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如果被诉侵权行为仅针对那些嵌入式元素,依然没有采用拆分保护路径的必要。而剧情或者故事内容(若游戏属于此种类型)对于网络游戏来说是融合式元素,拆分对于这样的元素来说实际上是一种推定其存在的拟制,【10】但令人疑惑的是,这一“拟制”的思想实验究竟是“还原”意义的拆分还是裁判者的演绎呢?一方面,剧情与游戏是相互融合的,所谓将剧情拆分出来纯粹属于主观想象,这样的抽象转换导致对游戏内容的扩大或缩小都是有可能的;另一方面,如果将所谓的剧情拆分出来是拟制出一个剧本的话,那也就是与情形1中“先有剧本后有游戏”正好相反的过程,既然情形1中从剧本到游戏的过程应定性为演绎,从游戏到剧本难道就不是演绎了吗?而演绎和拆分显然是性质完全不同的行为。因此在情形2之下,同样没有采用拆分保护路径的空间。
基于以上两种情形下的分析可知,照搬过去在电影作品上惯用的拆分保护路径来保护网络游戏,【11】既无必要、也缺乏客观基础,还容易导致司法的不效率。根据著作权赋权原理与客体理论,网络游戏作为一种已经非常成熟的产品,完全可以作为独立的作品被对待,而对其著作权采用整体保护的路径是更为恰当的选择。那么,网络游戏的整体保护观如何在实践中得到切实贯彻呢?笔者认为,核心问题即为整体观念上网络游戏的独创性何在。对此,我们还是应当立足于作品构成要件的分析框架,通过识别以“独创性”为支撑的作品的实质内容,进而以之作为“对照物”,判断被诉行为是否“触及”作品的这些实质部分。
在作品的构成要件体系中,“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的表达”与“以某种形式表现”是外在要件,属于对作品的客观描述,是比较容易达成共识的。当然,在有些案件中,关于满足外在要件与否也产生过争议,代表性的判例如美国“The Cartoon Network LP, LLLP v. CSC Holdings, Inc.案”,【12】上诉法院与地方法院在“以某种形式表现”(可固定性)要件是否须满足持续性的要求以及持续性的标准为何的问题上持不同见解;再比如我国的“音乐喷泉案”中,原告要求保护的“喷射表演效果”是否满足可固定性要件,也存在不同看法。【13】“独创性”则是内在要件,真正体现作品系智力创造成果的属性,之所以其地位如此重要,也是如前所述之著作权赋权的内在机理所决定的——“独创性”决定了一部作品与其它作品、私有领域与公有领域的界分,即解决所谓“一部作品到哪里为止,而另一部作品又从哪里开始”的问题。“独创性”因与创作者的内心活动关联而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和价值判断色彩,长久以来,“独创性的判断”都是著作权法上的一道难题,【14】对于网络游戏这种复杂表达形式来说,其独创性判断之困难尤为突出。
整体保护观之下对网络游戏独创性的识别,就是要从整体视角而不是“深入到”微观层面的各种表达手段,分析其是否含有区别于他人作品以及公有领域素材的实质内容。结合已有司法实践来看,影响网络游戏独创性判断、引发最多争议的要素就是“游戏规则”,各界在这之上存在的强烈分歧也正好说明了为何不少人倾向于采用拆分保护路径来处理网络游戏的著作权保护问题。
提及“游戏规则”,恐怕没有什么比它引发的争议还要多了,赞成和反对将之纳入著作权保护范畴者都非常多。但综观相关探讨,我们不难发现,诸多研究或判决中的游戏规则的含义其实并不一致,也即是说,大家分析和批判的“靶子”恐怕都不是同一个,那又怎么能够取得共识呢?无论是产业界、学术界抑或司法界,都没有关于“游戏规则”的明确定义,而且,网络游戏的类型多样,棋牌类游戏、体育竞技类游戏的规则与剧情类游戏的规则相比,显然不是同一层面的事物或者说不是同一个逻辑的东西。
在游戏开发商看来,作为网络游戏的基础和核心组成部分,游戏规则不仅定义了游戏的世界和其运转方式,还决定了玩家在游戏中如何与其他元素互动、如何获胜以及如何结束游戏。针对这样的界定或描述,人们通常不会有什么异议,而且大家也都明白,对于不同类型的网络游戏来说,游戏规则所具有的功能、传递的信息、决定的行为意义是不一样的。不过,由于游戏规定的前述定义仍然是抽象的、模糊的,因而在具体案件中作进一步解释时,还是很容易引发争议,典型的如“率土之滨案”,其一审判决一方面说游戏规则通常具有指示性、操作方法和流程等功能,另一方面又主张音乐、美术、摄影等作品都可以被翻译为特定的操作方法。【15】很显然,过于扩张性地解释“操作方法”这一概念,难免让人产生“这样的解释是在由果导因”之感。
在游戏设计领域,“游戏规则是任何可以用来定义游戏中所有发生事件的东西,它定义了游戏中的世界和其运转方式,比如角色的外观以及角色和游戏世界中其他对象交互。”【16】从生成方式来看,游戏规则可以是现实中的科学或自然规律的延伸,但也可以是设计师根据自己的设想而制定的,大多数情况下就是天马行空的产物,比如道具也是一种规则。综合前述这些方面我们不难理解,网络游戏为何常常被认为是为玩家提供一个有趣的、沉浸式的场景和体验。也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对于游戏规则的理解,关键点不应放在“它是完成特定行为的规则和程序”之上,而应着眼于“它定义了游戏世界的运转方式和不同对象之间的交互”。具言之,所有类型的网络游戏都含有的游戏规则是保障游戏运行的程序、流程和操作方法,而对于某些类型的网络游戏来说,例如剧情类游戏,其游戏规则还包含向玩家输出的场景和内容,这些交互性质的内容是此类游戏的实质组成部分,是其生命力之所在。如此看来,后一含义的游戏规则与电影作品向观众所讲的“故事”是相同性质的东西,属于受著作权保护之客体的组成部分。
有关电影作品中“讲故事”的内容(电影的实质组成部分)如何受保护的问题,学术界和司法界就有不少人主张应当遵循拆分的路径,将“剧情”“内容”交给作为文字作品的剧本去保护。但是,将通过整体性对比即可完成的任务非要用拆分的方式进行,总是溯及最初的著作权进行侵权比对,实际上是降低效率的做法。这是因为,著作权侵权判定所进行的比对,就是要判断被告是否“窃取”了原告具有独创性的实质内容,但并不需要判断原告的独创性是否为最初始的,电影用自己的表达方式展现剧本的实质内容,二者在独创性上的牵连性不影响电影所表达的剧情有自己的独创性,否则,有剧本的电影就不是在“创作”而是在“复制”了。因此,整体保护观避免了拆分保护在侵权比对时的多此一举,直接进行整体比对,从而判断被告是否未经授权地使用了原告的实质内容。对照网络游戏,基于前述游戏规则的含义及其地位,笔者认为实际并不存在所谓单独保护游戏规则的问题,其是融入到游戏产品的整体之中的,故采取整体保护观、回到独创性判断的根本问题上来,即能实现对网络游戏著作权的切实保护,涵盖了那些应受保护的游戏规则。
结 论
主张采用拆分保护路径是近年来在网络游戏著作权保护问题上的多数派观点,它不仅与《著作权法》第3条作品类型例示规定的解读有关,也是早先电影作品著作权拆分保护观点在网络游戏之上的延用。但在笔者看来,该主张并不能消除一直以来围绕网络游戏著作权保护所产生的争议,诸如作品类型例示究竟应为开放式抑或封闭式、游戏规则能否获得著作权保护等,同时拆分保护路径也缺乏必要性与适用空间,还会导致司法效率的降低。所以,有必要回到著作权赋权的基本原理,以之为基础构建恰当的认知作品及作品类型的著作权客体理论,藉此认识网络游戏在著作权客体体系中的独立存在具有正当性和必要性。与之相应地,网络游戏在现行法下可按照《著作权法》第3条(九)项“符合作品特征的其他智力成果”来定性。进而可知,作品构成要件尤其是独创性要件的分析框架足以支撑网络游戏著作权采取整体保护的路径。整体保护观有利于法官正确理解相关规则、选择恰当的裁判逻辑,在涉网络游戏的著作权侵权案件中有效解决“公与私”“此权与彼权”的界分,很好地回应“游戏规则能否在网络游戏著作权之下得到保护”等引发激烈争议的问题。
注释:
【1】值得注意的是,作品的构成要件本身就体现了一定的价值判断。
【2】赞成封闭模式的代表性学者王迁解释了自己的理由:开放模式的一个重大问题是会导致《伯尔尼公约》成员间的不对等保护。参见王迁:《论作品类型法定——兼评“音乐喷泉案”》,《法学评论》2019年第3期,第23、25-26页。但是,无论国际公约下的不对等保护是否是一个切实的、影响社会效用的问题,这一理由尚构不成针对“作品”立法的公共政策选择依据。
【3】See Mark Rose, Authors and Owners: The Invention of Copyrigh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3.
【4】同上注。
【5】参见该办法第2条第2款。
【6】数据来源于智研咨询:《2023年中国游戏行业市场现状分析:产业存量竞争式发展,电竞游戏市场潜力明显》,载https://www.sohu.com/a/654885352_120961824,最后访问日期2023年11月24日。
【7】网络游戏产业至少包括游戏开发、游戏运营、游戏分发三大基本环节。此外,网络游戏直播、电子竞技等发展迅猛的新兴产业则是由网络游戏衍生而来的。
【8】例如前注3所揭案例,涉案网游《奇迹MU》即被定性为类电作品。
【9】See Spelling Goldberg Productions v. BPC Publishing, [1981] RPC 283.
【10】此观点请参见崔国斌:《视听作品画面与内容的二分思路》,《知识产权》2020年第5期,第32页。
【11】照搬的基础在于剧情类游戏通常是作为类电作品来保护的。
【12】536 F.3d 121 (2nd Cir. 2008), cert. denied 557 U.S. (2009).
【13】参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京73民终1404号。
【14】虽然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多年来一直都在努力构建科学的独创性判断方法和标准,无论是“Feist案”确立的“最低限度的创造性”标准,抑或德国法上的“小硬币理论”,又或是其它的标准与理论,都曾在著作权法领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独创性判断问题上的众说纷纭,未来还将继续下去。
【15】参见广州互联网法院(2021)粤0192民初7434号民事判决书。
【16】知乎专栏文章《游戏规则的制定、破坏和解释》,载https://zhuanlan.zhihu.com/p/593485492,最后访问日期2023年11月27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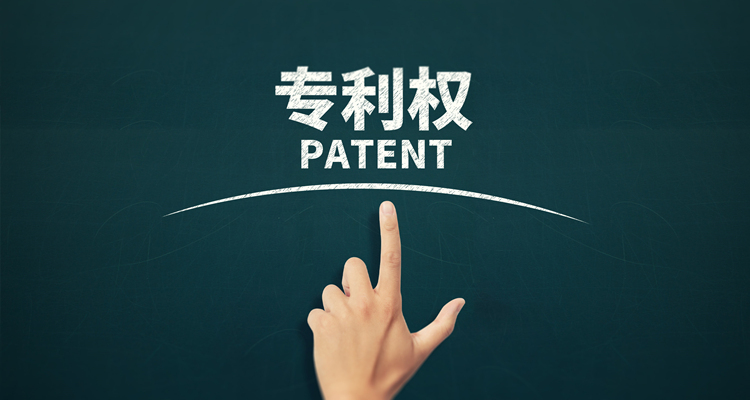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9464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946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