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苏志甫 天同律师事务所高级顾问
邹晓晨 天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律师
一、问题的提出
(一)“换皮抄袭”著作权法规制思路演进
近年来,随着网络游戏产业的快速发展,网络游戏保护问题日益成为产业界、学术界及实务界关注的话题。其中,“换皮抄袭”的规制路径、网络游戏“玩法规则”可版权性问题引发的关注和争议颇大。
1.“换皮抄袭”概念及成因
顾名思义,“换皮抄袭”是指通过替换网络游戏美术设计、文字表达、音乐音效等外在内容、保留玩法规则等内核设计,所实施的一种游戏开发行为。因“换皮游戏”制作周期短、研发成本相对较低,游戏厂商配合一定的买量宣传手段,就能快速将“换皮游戏”推向市场。如“太极熊猫v.花千骨案”判决中指出:“由于网络游戏的玩法规则、数值策划、技能体系等,是一款游戏的核心内容,因此其可以实现与在先游戏在操作习惯、用户体验等方面的一致。同时,通过对在先游戏的‘换皮’抄袭,可以大量减少游戏的开发成本投入,缩短游戏的开发周期。”[1]
实践中,由于“换皮游戏”全面替换原游戏的外观,甚至对游戏主题、名称、介绍等内容也进行替换,整体呈现出一定隐蔽性。同时,“换皮游戏”多为中小游戏工作室或个人开发者开发产品,因此,在相关主体的确定方面,也存在一定的难度。可见,低廉的成本投入、高额的流水诱惑以及行为外在呈现和实施主体的隐蔽性,是实践中“换皮抄袭”现象频发的主要原因。
2.“换皮抄袭”规制的实践演进
对于网络游戏“换皮抄袭”可否通过著作权法予以规制问题,我国司法实践的态度经历了从“否定”到“间接肯定”再到“肯定”的演进过程,但迄今尚未完全形成定论。2014年的“炉石传说v.卧龙传说案”是我国早期网络游戏“换皮抄袭”规制案例。该案中,原告主张权利游戏对卡牌的选取、文字说明及规则玩法具有较高独创性,应当受到著作权法保护。法院审理认为,原告主张的卡牌牌面设计、卡牌和套牌的组合属于“思想”而不是“表达”。最终仅支持涉案动画、标记等元素分别构成类电作品、美术作品。[2]
2014年至2017年,我国网络游戏行业发展进入井喷期。[3]在此背景下,有关加大对网络游戏保护力度的呼声越来越大。有观点指出,将网络游戏拆分成不同作品类型,分别予以保护的模式会割裂游戏的完整性[4]、增加权利人的维权成本[5]。在此情况下,在2017年“奇迹MU v.奇迹神话案”[6]中,我国首次认定网络游戏画面构成类电作品。尽管该案判决并未明确对网络游戏“玩法规则”可版权性问题进行讨论,但判决认定权利游戏运行画面整体构成类电作品,并在实质性相似比对部分直接将等级设置、角色技能、武器装备、怪物等元素纳入比对和认定范畴,实则已经将“玩法规则”纳入了保护范畴。
在2020年“太极熊猫v.花千骨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认定,“玩法规则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其是否受到保护,不应根据名称判断,而应根据具体表达方式,依照著作权法关于作品的规定特别是独创性的规定予以判断。”该案进一步提出“具体化的玩法规则构成表达而非思想”的观点。[7]类似地,“蓝月传奇v.焰武尊案”同样涉及网络游戏“换皮抄袭”问题。该案法院提出“游戏五层分层”的论述,以阐明游戏情节并非决然属于思想的范畴,认为在情节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中,存在着思想与表达的分界线。更进一步,法院认为权利游戏对于角色养成系统、消费奖励系统和场景(副本)段落中的具体玩法规则、属性数值的取舍和安排体现独创性。对此,应当赋予著作权法保护。[8]
而近期,在诸如“拳皇v.数码大冒险案”[9]“率土之滨v.率土模拟器案”[10]等案件中,司法实践对于网络游戏“换皮抄袭”的认识似乎又有了新的转变,呈现出回归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换皮抄袭”的一定倾向。例如,“拳皇v.数码大冒险案”一审法院认为,游戏规则设计创作过程中凝聚了大量劳动,是一款游戏的核心要素。但受制于著作权法“仅保护具体表达而不保护思想”,无法获得著作权法保护。二审判决进一步指出,“电子游戏的设计架构,包括游戏的主题、规则、玩法、情节等内容,一般情况下属于思想的范畴,不受著作权法保护。”最终,上海知识产权法院认定涉案游戏抄袭“玩法规则”构成不正当竞争。
司法实践在不同阶段对于“换皮抄袭”规制路径的思路变化恰恰显示,网络游戏“玩法规则”可版权性、网络游戏内在设计的“思想”与“表达”界分等问题,是具有较大争议性的问题。而实践对于网络游戏的机制、内涵,以及对于网络游戏“玩法规则”的价值、作用的理解,也是不断发展和深入的。
3.网络游戏“玩法规则”著作权法保护观点分歧
实际上,网络游戏“换皮抄袭”案件实践争议背后,蕴含具有争议性的问题——网络游戏“玩法规则”可版权性问题。关于网络游戏“玩法规则”是否属于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以及构成何种作品类型,学术界存在一定探讨。
支持网络游戏“玩法规则”受著作权法保护的观点主要认为:①网络游戏“玩法规则”的设计细致、复杂到一定程度,则超出思想范畴而构成表达[11]。②网络游戏“玩法规则”研发投入大,不予保护将打击创作者积极性[12];③网络游戏“玩法规则”具有重要的价值和作用,决定游戏商业运营效果好坏[13];④不保护网络游戏“玩法规则”可能催生同质化游戏,阻碍我国游戏产业的发展[14]。
而反对将网络游戏“玩法规则”认定为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的观点则认为:①网络游戏“玩法规则”的核心特征在于基础性和程序功能性,本质属于“思想”而不是“表达”[15];②以视听作品的名义保护网络游戏“玩法规则”,将导致视听作品的保护范围延伸到非画面因素[16];③网络游戏“玩法规则”本质仍属于思想或规则或方法的范畴,不会因为在游戏画面中呈现而转变为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17];④网络游戏“玩法规则”不会因为其具有创新意义而成为表达[18]。
(二)“换皮抄袭”著作权法规制困境
首先,“换皮抄袭”案件审理涉及著作权争议性理论问题。在现有立法框架下,网络游戏还不是我国著作权法明文规定的法定作品类型。尽管实践中,诸多案例将网络游戏连续画面认定为视听作品(类电作品)予以保护,但相较于传统意义上的视听作品,其内涵和保护范围并不清晰,这在一定程度上引发实务界及学术界认识上的分歧。同时,在“换皮抄袭”类案件中,由于原游戏美术设计、文字表达、音乐效果等明显构成著作权法客体的内容被替换,仅剩下边界模糊、概念抽象的“玩法规则”,使得此类案件的审理焦点更加集中于对“思想-表达划分”“独创性认定”“抽象-过滤-比对方法运用”等著作权底层理论问题。这些问题恰恰又是著作权法领域最为疑难和抽象的问题。更何况,实践中网络游戏品类众多,不同类型“玩法规则”的呈现方式差异巨大,进一步加大“换皮抄袭”案件中对事实抽象提炼、对规则解释运用的难度。
其次,“换皮抄袭”案件所涉利益具有重大性、复杂性。一方面,“换皮抄袭”案件所涉利益具有重大性。据统计,2021年中国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到2965.13亿元。[19]近年来,实践中亦不乏单案判赔额在千万级别的游戏侵权案件。其中,网络游戏“玩法规则”作为吸引用户的内核因素,对于网络游戏市场竞争、营收贡献均起到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换皮抄袭”牵涉的产业利益具有一定的复杂性。移动游戏销售市场呈现出典型的长尾模式,少量“头部游戏”占据绝大部分的销售份额和市场资源,数目众多的“尾部游戏”在研发、盈利能力方面均相对处于劣势。[20]“头部企业”具有雄厚的资金优势及IP制造能力,使得“尾部游戏企业”难以在制作上与“头部企业”形成抗衡,进而将目光转投向制作成本较低的“换皮游戏”。表面上看,“尾部游戏企业”攫取了“头部游戏企业”的劳动成果,但深究其因,“换皮抄袭”频发背后,实际反映出游戏市场的准入壁垒、优质IP资源垄断及文化产业创新能力疲乏的现象。因而,在“换皮抄袭”案审理中,如何划定“激励”与“保护”的边界,平衡各方主体的利益,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及复杂性。
二、“换皮抄袭”著作权法规制实务观点评析
(一)关于“经具体设计的玩法规则构成表达”
实践中,部分法院认为:当网络游戏“玩法规则”具体、复杂到一定程度,即构成“表达”。比如,在“太极熊猫v.花千骨案”中,法院在明确表达应根据玩法规则的具体表达方式,依照著作权法关于作品的规定特别是独创性规定予以判断这一观点的同时,进一步指出:“当规则表现为装备的细化分类、获得的方式安排,玩法设计安排的越细致、多样,就越有可能具备独创性而构成作品。”基于此,法院认定蜗牛公司在该案中主张的玩法规则构成具体的表达。[21]
在“守望先锋v.英雄枪战案”中,一审法院提出了网络游戏元素从抽象到具体的“五层分层理论”,认为确定涉案游戏“玩法规则”是否可受到著作权法保护的关键在于,“第三层为游戏资源的核心部分制作(包括游戏地图行进路线设计、游戏人物初始数值策划、用户界面的整体布局)和第四层资源串联及功能调试,究竟属于思想还是表达的范畴。”法院最终认定:“游戏规则通过以游戏设计要素为内核的游戏资源制作得以外在呈现,这种外在呈现即表达。因此,游戏地图的行进路线、地图进出口的设计、人物的类型、技能和武器组合等整体构成了对FPS游戏规则的具体表达。”[22]
而在“蓝月传奇v.烈焰武尊案”中,法院则将网络游戏的“玩法规则”视为网络游戏的情节,并且认为在网络游戏情节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中,存在着思想与表达的分界线。杭州中院进一步提出:“从第一层到第五层,是《蓝月传奇》游戏中的情节不断具体化的过程。通过三大系统内部分别对不同的宝物、道具、怪物及其各自分别的属性与数值的选择、组合、安排,以及不同系统之间的相互搭配、组合,《蓝月传奇》中的情节至少在第四、第五层上已经足够具体。随着游戏的进展,玩家或旁观者可以清楚明确地感知到游戏人物如何逐步成长。这样的情节已不再是单纯的游戏规则或玩法,而应被归入表达的范畴。”[23]
前述判决中,法院均提出网络游戏“玩法规则”资源要素的具体设计(如人物数值策划、装备设置及获得方式等、技能和武器的组合等内容),构成了具体表达。但上述论证思路存在一定不自洽之处:
首先,忽视了独创性认定时的表达形式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20修正)》第三条规定:“本法所称的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智力成果。”即,“以一定形式表现”和“具有独创性”,是获得著作权法保护的并列前提。根据“思想与表达二分法”,著作权对作品的保护是对独创性表达的保护。针对处于“思想”与“表达”模糊地带的争议客体,在评判其是否构成作品时,对独创性的认定必须基于该客体的表达形式。如该客体属于“思想”范畴,则作为作品受到保护的核心条件即独创性表达无从谈起。但实践中,部分案件在未解决“玩法规则”构成“思想”还是“表达”这一基本前提以及未清晰界定“玩法规则”具体表现形式的情况下,即以其满足一定的智力创造性、进而具有“独创性”进行判断,但上述认定方法存在脱离表达形式而模糊、笼统认定独创性之嫌。前述案件中所提及的“设计安排”“具体化到一定程度的情节”的具体表达形式是什么,所谓“经具体设计的玩法规则”是以何种形式具化呈现,在相关案件中并不十分清晰。上述认定存在将“思想表达划分”和“独创性认定”两个环节合二为一之嫌。事实上,智力创造空间和个性发挥余地所影响的“独创性”并非当然直达作品表达层面。仅论述涉案游戏设计安排的选择创作空间大,认定其构成“独创性表达”,实则跳过了“思想表达划分”以及界定保护客体具体表现形式这一关键前提。
其次,将游戏画面未予呈现的内容也纳入“表达”范畴。诚然,前述案件中提及的诸如游戏人物初始数值设定等资源要素内容,可能在游戏画面中,通过文字表达的形式予以呈现。该部分内容,若不造成“思想”和“表达”混同的前提下,可能受到著作权法保护。但对于前述案件中提到的诸如“装备的获得方式”“技能和武器的组合”等内容,实际上难以通过游戏画面直接呈现。结合游戏操作实践也不难理解,网络游戏中某些“玩法规则”是隐藏的,如“技能相生相克”“技能和武器的组合”,是需要玩家在游戏过程中反复摸索才能掌握,并不会在游戏画面中直接呈现。正是由于不同玩家对于游戏“隐性玩法规则”的认知程度、运用水平不同,不同玩家间的游戏竞技水平可能有显著差异。该部分内容本质上属于“思想”而非“表达”。
再次,所谓“具体化”的标准十分含糊,容易使得实践对于网络游戏“玩法规则”的界定和保护范围判断偏向主观判断,且缺乏说理阐明,进而造成不同法院之间对于“思想”和“表达”的裁判尺度不统一,有损司法的可预期性和权威性。
(二)关于“玩法规则设计需要大量劳动投入”
实践中,部分法院认为游戏开发者在网络游戏“玩法规则”的设计过程中投入了智力劳动,进而认定游戏“玩法规则”具备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实质条件。比如在“太极熊猫v.花千骨案”中,一审法院在论述涉案游戏是否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时指出:“涉案《太极熊猫》......玩法层次丰富,蕴含了游戏设计团队的大量智力成果。从蜗牛公司提交的证据SVN记录中可以清楚看到,该游戏自2013年底立项至公证保全的权利版本开发完成历经了一年多时间,形成了9万多条开发记录。经过前述开发过程形成的作品,是主创人员付出大量劳动、团队合作的智慧结晶,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艺术和科学领域具有独创性的作品。”[24]类似地,在“守望先锋v.英雄枪战案”中,一审法院也提到:“(涉案《守望先锋》游戏)技能效果相生相克,游戏玩法逻辑自洽,蕴含了游戏开发者大量的智力成果......可见,该款游戏是主创人员付出大量劳动、团队合作的智慧结晶,完全符合著作权法关于独创性的要求。”[25]
但是,网络游戏开发者在设计“玩法规则”过程中,投入相当程度的劳动,并不意味着“玩法规则”就具备“独创性”。正如最高人民法院指出:“独立完成和付出劳动本身不是某项客体获得著作权法保护的充分条件”。[26]更何况,前述判决在说理过程中,也没有区分“独”和“创”的内涵:首先,“独”要求作者对于作品贡献出来源于本人的表达。[27]但在“太极熊猫v.花千骨案”中,权利人提交“9万余条开发记录”仅能说明其对涉案游戏开发投入一定智力劳动,而该过程究竟是否创造出“玩法规则”的新表达,还是仅仅是对在先游戏“玩法规则”的重复或简单整合,并不得而知。第二,“创”要求作品应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智力创造性,要求体现作者独特的智力判断与选择、展示作者的个性。[28]但前述判决论述过程中,法院提到涉案游戏“玩法层次丰富”“技能效果相生相克”“玩法逻辑自洽”,仅仅是对“玩法规则”的结构、功能方面的评价与描述,而与智力创造程度的判断无关。
三、“换皮抄袭”著作权法规制隐患揭示
(一)混淆文字表达和视听表达
在 “换皮抄袭”类案件中,部分案件将游戏“玩法规则”的表达(文字作品)等同于游戏“画面或图像”表达(视听作品),实际上是将两种不同性质的表达混为一谈。[29]甚至于,部分案件一方面认定涉案游戏画面构成视听作品,但另一方面又以游戏“玩法规则”的文字性内容(如属性、数值等)为对象,进行实质性相似比对、认定。这一矛盾做法,进一步说明“玩法规则”的表达形式是文字,而不是连续画面。
譬如,在“太极熊猫v.花千骨案”中,法院认定涉案游戏构成类电作品,但在实质性认定部分却将“玩法规则”的文字性内容作为比对对象,指出:“一款网络游戏的设计,其游戏结构、玩法规则、数值策划、技能体系、界面布局及交互等设计属于整个游戏设计中的核心内容,相当于游戏的骨架......涉案《花千骨》游戏在对战副本、角色技能、装备及武神(灵宠)系统等ARPG游戏的核心玩法上与《太极熊猫》游戏存在诸多实质性相似之处,且在部分细节上存在的雷同,远远超出了创作巧合的可能性,故可以认定《花千骨》游戏对《太极熊猫》游戏的具体玩法规则所设计的特定表达进行了整体照搬和复制,构成著作权侵权。”[30]法院一方面认定游戏画面构成类电作品,但另一方面,又对“玩法规则”文字内容进行实质性相似比对。这一做法不仅使得同一判决前后论述对象不一,作品类型认定和实质性相似认定部分“各自为政”,更说不清楚涉案游戏的独创性表达究竟是什么。实际上,法院忽略不同作品类型间表达的差异,将视听作品的保护范围延伸到思想上。
(二)实质性相似认定理由牵强
“换皮抄袭”侵权认定案件中,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在涉案游戏基本画面不同的情况下,将“游戏规则”相同或近似与整体画面实质性相似划等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在针对电子游戏的报告中指出:“网络游戏是一种包含音乐、剧本、情节、视频、动画和角色等多种艺术形式的复杂作品”。[31]尽管,网络游戏“玩法规则”可能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网络游戏画面,但相较于动画、角色等元素而言,“玩法规则”并不是决定游戏画面整体视听效果的首要因素。但在“换皮抄袭”案件中,法院却通过游戏“玩法规则”的相似,推导出整体运行画面的实质性相似,实则忽略“玩法规则”和游戏画面的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也没有考虑到“相似比”的问题。
事实上,在部分案件中,法院已经注意到“换皮抄袭”案件的游戏画面是明显不同的。如“太极熊猫v.花千骨案”判决认为:“《花千骨》游戏的IP来自于《花千骨》同名电视剧,从其游戏整体运行的动态画面中看到,在剧情动画、对应剧情设计的关卡名称和美术场景、玩家扮演角色、灵宠、NPC的名称和美术形象、各类道具的名称和美术形象、游戏场景设计中的主界面场景、剧情场景、修行场景的名称和美术画面、美术设计中的人物设计、技能美术效果、动画特效、UI按键设计、UI图标设计、加载页面及切换页面设计、音效设计、AI设计等美术、音乐、动画、剧情文字等设计均与《太极熊猫》不同,该部分内容和要素系基于同名电视剧及小说作品《花千骨》而创作,故玩家从外观上可一定程度识别与原作品的区别。”[32]类似地,在“梦幻模拟战v.三国志赵云传OL案”中,法院明确指出:“在具体人物、道具造型、界面背景的层面上进行比对,两游戏或许无法找出一帧完全相同的游戏画面”。[33]由此可见,“玩法规则”层面的相似,并不意味着游戏画面视听表达效果相同。在涉案游戏视听效果显著不同的情况下,认定涉案游戏构成“实质性相似”未免显得牵强。
(三)难以与公有领域内容形成区分
网络游戏“玩法规则”的设计,或多或少难免存在对在先游戏玩法和公有领域内容的借鉴。实践中,经常出现同一品类不同游戏间“玩法规则”相互借鉴的情况。例如,“率土之滨v.率土模拟器案”中的争议对象之一“三国类战法规则”,就是以炙手可热的三国IP为背景设计的。据统计,国内外以三国IP为题材的游戏累计多达千余款。[34]三国类游戏的“玩法规则”设计大多借鉴《三国志》《三国演义》史书或小说,甚至包含对同名影视剧、三国类在先游戏内容的借鉴。数量庞大的三国品类游戏间相互启发、借鉴,在先游戏潜移默化影响在后游戏设计思路,实际上已经很难追溯特定玩法的来源与归属。
同时,网络游戏“玩法规则”的实用功能是在帮助玩家理解和引导操作。这导致网络游戏“玩法规则”的篇幅普遍不长,行文上以简洁的说明性语言为主。在有限的篇幅内,留待游戏设计者发挥的智力创作的空间并不大。例如,“率土之滨v.率土模拟器案”中,法院以“赵云”战法为例[35],希望说明“尽管将武将战法中的单独字、词隔离出来判断都属于公有领域素材,但该等字、词的组合用于战法并赋予其一定含义就具有独创性,能够体现作者的取舍、选择、安排、设计等”的观点。[36]但该战法规则内容是描述“对敌军武将的2次单体伤害”的技能效果,由“发动攻击”“敌军”“单体”“伤害”等游戏通用词汇组成,整体篇幅较短。因此,不论是词汇的组合方式,还是组合后的表达效果,都难以区别同类游戏编排的“复杂性”和“创造性”。
基于以上分析可见,特定游戏设计者的“智力成果”实际与公有领域前人的投入密不可分。在此情况下,若不对公有领域内容予以甄别及避让,其后果很可能是造成特定主体对某一品类游戏“玩法规则”的垄断,进而限制、阻碍品类游戏的发展。
四、“换皮抄袭”著作权法规制应当回归理性
(一)网络游戏“整体保护”路径反思
现有判决尝试以连续画面的方式保护网络游戏,其出发点或许是为了“整合”游戏涵盖的各独创性要素,进而进行“整体性”保护。但这一认定思路却忽略了游戏与电影作品之间的实质差异,也引发了解释和适用上的诸多问题:
首先,网络游戏画面与电影画面间的差异难以忽视。对于电影而言,其画面在摄制、剪辑、后期制作完成后即已固定,呈现形式唯一且确定。而网络游戏画面的显著特点是“交互性”。正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在针对电子游戏的报告中指出:“网络游戏的画面本质上并不是为了‘展示’而设计的。相反,电子游戏通过电脑程序运行,具有交互性的特点;而就当前‘视听作品’的概念而言,其蕴含的用户参与性更少。”[37]上海知识产权法院课题组发布的《网络游戏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研究——以著作权保护为主视角》课题调研报告亦明确:“网络游戏的多样性及复杂程度更甚于电影”。
其次,将网络画面等同于电影画面不符合玩家认知。尽管司法实践中从“网络游戏运行过程呈现的所有画面均不超出游戏开发系统预设范围”的角度认定网络游戏运行画面满足“固定性”要求,进而解决网络游戏画面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前提问题。但上述理解在一定程度上也与相关公众对游戏的一般认知相分离。事实上,玩家在操作游戏时接触到的是“实时画面”而非“整体画面”。并且,网络游戏中往往蕴含大量角色、道具、场景元素,经过元素间的排列组合,网络游戏运行实时画面的呈现形式甚至可能趋近于无限。更何况,从游戏运营角度,想要让玩家保持对游戏的新鲜感和可玩性,游戏设计者也不会让玩家轻易获得游戏“全貌”。甚至于,游戏设计者会设置“高阶道具”或“隐藏玩法”等,以增强游戏画面的不可预知性。因此,将网络游戏运行画面等同于电影画面,将操作游戏过程类比为消极观看电影过程,一定程度上是与网络游戏玩家的感知体验相背离的。
再次,将网络画面等同于电影画面,造成实践中实质性相似比对操作困难。网络游戏整体画面“固定”的理解,更多停留在理论层面。而在案件办理过程中,依照目前的现有条件,很难从海量元素排列组合后趋近无限可能的画面呈现方式中,调用对应内容进行比对。甚至当事人在取证过程中,也难以完整取证全部元素及支线情节。如“奇迹MU v.奇迹神话案”中,法院就曾指出“由于网络游戏的画面繁多,且需要依赖于玩家的操作而产生,故难以进行一帧帧的比对。”[38]更何况,实践中涉案游戏中相关元素的呈现方式不是一一对应的。可能出现替换或是调整顺序等情况,导致无法找到对应的游戏画面进行比对。或许是因为直接比对连续画面的操作难度、工作量过大,并且游戏运行画面的视听效果根本不相似,法院转而对游戏元素进行比对。甚至于,借助玩家做出涉案游戏整体体验相同或相似的评论,为得出涉案游戏构成实质性相似的结论提供正当性支持。[39]但这一思路带有强烈的“有罪推定”色彩,也脱离实质性相似比对和认定的基本逻辑。
因此,应当正视网络游戏与电影作品间的差异,正确理解网络游戏“玩法规则”对于游戏整体画面的作用。相比于电影作品画面呈现自摄制、制作完成后,其连续画面呈现方式就得到“固定”。网络游戏的交互性决定其运行画面的“固定”,是过程意义上的“固定”。即,网络游戏中固定的是画面组成素材以及素材间调用和组合的规则。网络游戏“玩法规则”在其中正扮演“枢纽”的角色——网络游戏运行画面的呈现,是依托于网络游戏“玩法规则”以及代码化指令共同实现的。从这一角度,网络游戏“玩法规则”发挥的是功能性的作用,即推动游戏中一系列视听表达效果的最终形成。因此,网络游戏“玩法规则”不是网络游戏的情节、脚本,也不等同于游戏整体作为视听作品的具体表达。
(二)“玩法规则”具有高价值不意味着当然有版权保护必要性
正如“拳皇v.数码大冒险案”判决书所指出:“游戏规则的可玩性决定着游戏作品的优劣与否,游戏规则设计创作过程中凝聚了大量劳动,属于一款游戏的核心要素。”[40]也有观点认为,网络游戏“玩法规则”对于一款游戏能否取得市场成功起到重要作用。[41]诚然,网络游戏“玩法规则”具有较高的产业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玩法规则”就当然具有受到著作权法保护的必要。
应当进一步区分,网络游戏“玩法规则”蕴含的价值究竟是智力创造方面的价值,还是市场竞争方面的价值。遗憾的是,部分判决并没有对网络游戏“玩法规则”价值来源进行甄别,直接将“玩法规则”产业价值,等同为独创性层面的价值。譬如,在“守望先锋v.英雄枪战案”中,法院认为:“该款游戏是主创人员付出大量劳动、团队合作的智慧结晶,完全符合著作权法关于独创性的要求”。[42]这一思路,实际是把“玩法规则”设计劳动投入,等同于创造性表达的贡献。
在近期网络游戏“换皮抄袭”案件中,似乎呈现出回归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规制路径的趋势。譬如“拳皇v.数码大冒险案”中,法院认定《数码大冒险》和《拳皇》游戏在规则说明文字、规则界面中功能板块结构设计及名称、主线(包括精英和噩梦)地图关卡数、人物属性设置等方面存在相似性。法院经分析认为,上述相似性内容实际属于游戏规则设计范畴。尽管法院认可网络游戏“玩法规则”设计对于游戏运营的重要价值,但最终认定《拳皇》游戏规则设计开发投入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法益。[43]
但需要注意的是,网络游戏开发者对“玩法规则”设计所付出的劳动投入在无法适用著作权法进行保护时,并非可以当然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保护。在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换皮抄袭”行为进行规制时,应具体案件具体分析,既要遵循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逻辑,也要注意与著作权法的立法政策相兼容,为公共领域、模仿自由留出必要的空间。根据2022年3月20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44],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应具备以下要件:一是经营者的行为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二是该行为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合法权益;三是属于反法第二章具体行为及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等规定之外的情形。由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行为规制法,重在维护公平、自由的商业竞争秩序,仅仅是交易机会或竞争优势的“此消彼长”并不足以触发其适用。从上述规定看,诉争行为必须是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和商业道德的行为,该行为不仅造成了“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损害后果,且须达到“扰乱市场竞争秩序”的程度。最高人民法院曾对外发布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第一条第二款即规定:“当事人仅以利益受到损害为由主张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但不能举证证明损害经营者利益的行为扰乱市场竞争秩序的,人民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尽管该条款最终未能成为正式条文,但其体现的法律适用倾向仍应受到重视。此外,著作权法优先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仅在原告的主张依据著作权法无法获得支持,且在与著作权法立法政策不存在冲突的情况下才存在适用的必要和空间。从作品创作、技术及商业创新的一般规律来讲,绝大多数的智力创造、商业创新都离不开对前人成果的借鉴或模仿。正如有观点指出,模仿是文化传承的基本方法,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关于模仿的技术或者艺术的历史。模仿是任何个人与生俱来的本能,也是全人类的行为习惯。时至今日,模仿仍然是社会得以正常运转的关键机制。如果模仿对象完全处于公共领域,则模仿不触及他人私权,行为人可以依法自行其是,与任何他人的私权都没有关联。而对处于法律模糊地带的模仿而言,其价值也是多重的,具体体现在捍卫公共领域、推动可持续的创新以及保障自由竞争等多个方面。[45]可见,对于明显属于公共领域的“玩法规则”,反不正当竞争法并不存在适用的空间;对于介于公共领域与独创性表达之间的“玩法规则”,反不正当竞争法在特定的情形下才能发挥补充性规制作用。
(三)“换皮抄袭”泛化认定的潜在负面效应
首先,“换皮抄袭”泛化认定可能限制同品类游戏的发展。如前文所述,网络游戏的设计与开发,均不可避免地存在对前人智力表达成果的借鉴。以“率土之滨v.率土模拟器案”涉及的三国IP题材为例,三国题材之所以尤其受到游戏市场的青睐,主要原因在与其具有丰富的元素、个性鲜明的人物、矛盾迭起的情节回合,天然带有广泛的受众群体和强大的市场号召力。而该部分优势恰恰源于前人的智力成果,而非特定游戏开发者的贡献,故应当由社会公众共同享有,而不宜为特定主体所垄断。尤其考虑到当前市面上以三国题材制作的改编游戏已多达千款,大量游戏“玩法规则”设计之间存在重合和借鉴。在此情况下,确认特定主体对某种“玩法规则”设计享有排他性权利,其后果可能是限制在后同品类游戏的发展,更可能造成游戏开发商间对“玩法规则”的哄抢和垄断。
其次,“换皮抄袭”泛化认定可能打开“诉讼闸门”。实践中,游戏侵权诉讼往往发生在产品同质化程度较高的游戏厂商之间。诉讼发起方通常是在精品IP方面有着较多积累,具有较大竞争优势,同时也掌握更多维权资源的“游戏大厂”。据统计,在2021年度118起游戏侵权诉讼案件中,维权数量排名前三的主体分别为网易公司、腾讯公司和网元圣唐公司。[44]在此情况下,泛化认定“换皮抄袭”的后果,可能是使得已经掌握优势资源的头部企业,借由侵权诉讼“围剿”竞争对手,进而使得当前已经呈现一定“两极化”的游戏市场,头部及尾部游戏企业的强弱对比更为悬殊。
综上所述,将网络游戏“玩法规则”纳入视听作品保护范围的思路存在不自洽之处,不仅混淆了文字表达与视听表达、造成实践判决中实质性相似认定逻辑的混乱,还容易将公有领域内容一概纳入保护范畴。网络游戏“玩法规则”的高产业价值,不是其作为视听作品受到著作权法保护的正当理由。而泛化认定“换皮抄袭”的后果,可能限制同品类游戏的发展,造成游戏开发商间对“玩法规则”的哄抢和垄断,进而影响行业生态。因此,对网络游戏“玩法规则”的著作权保护以及“换皮抄袭”行为的著作权规制应当审慎为之。
注释:
[1]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苏民终1054号民事判决书。
[2]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4)沪一中民五(知)初字第22号民事判决书。
[3]参见中国版权协会网络版权工作委员会、上海交通大学知识产权与竞争法研究会:《网络游戏知识产权保护白皮书》,第7-8页。
[4]参见田辉:《论计算机游戏著作权的整体保护》,载《法学论坛》2017年9月,第128页;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课题调研组:《电子游戏中设计及规则知识产权保护的调研报告》,2016年12月21日发布于“知识产权之家”微信公众号。
[5]参见郭壬癸:《论著作权视角下网络游戏内容之知识产权保护》,载《西部法学评论》2018年第4期,第61页。
[6]参见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16)沪73民终190号民事判决书。
[7]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申5551号民事裁定书。
[8]参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浙民终709号民事判决书。
[9]参见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20)沪73民终33号民事判决书。
[10]参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01民终7422号民事判决书。
[11]参见何培育:《“换皮游戏”司法规制的困境及对策探析》,载《电子知识产权》2020年第9期,第22页;卢海君:《网络游戏规则的著作权法地位》,载《经贸法律评论》2020年第1期,第140页;朱艺浩:《论网络游戏规则的著作权法保护》,载《知识产权》2018年第2期,第70-71页。
[12]参见何培育:《“换皮游戏”司法规制的困境及对策探析》,载《电子知识产权》2020年第9期,第18页;曾晰、关永红:《网络游戏规则的著作权保护及其路径探微》,载《知识产权》2017年第6期,第69-70页。
[13]参见冯晓青、孟雅丹:《手机游戏著作权保护研究》,载《中国版权》2014年第6期,第35页。
[14]参见卢海君:《网络游戏规则的著作权法地位》,载《经贸法律评论》2020年第1期,第134页;参见朱艺浩:《论网络游戏规则的著作权法保护》,载《知识产权》2018年第2期,第72页;曾晰、关永红:《网络游戏规则的著作权保护及其路径探微》,载《知识产权》2017年第6期,第69-70页。
[15]参见王迁:《网络游戏规则可版权性分析》,2020年1月2日发表于“网络法实务圈”微信公众号。
[16]参见崔国斌:《视听作品画面与内容的二分思路》,载《知识产权》2020年第5期。第39页。
[17]参见张伟君:《呈现于视听作品中的游戏规则依然是思想而非表达——对若干游戏著作权侵权纠纷案判决的评述》,载《电子知识产权》2021年第5期,第67-69页。
[18]参见张伟君:《呈现于视听作品中的游戏规则依然是思想而非表达——对若干游戏著作权侵权纠纷案判决的评述》,载《电子知识产权》2021年第5期,第71-72页。
[19]参见中国音数协游戏工委、中国游戏产业研究院:《2021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
[20]20 See Drew S. Dean: “Hitting Reset: Devising A New Video Game Copyright Regim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Vol. 164, p. 1247.
[2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申5551号民事裁定书。
[22]参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5民初77945号民事判决书。
[23]参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1民初3728号民事判决书。
[24]参见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苏中知民初字第00201号民事判决书。
[25]参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5民初77945号民事判决书。
[26]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申字第1392号民事裁定书。
[27]参见王迁:《著作权法》,中国人民法学出版社2017年4月版,第24页。
[28]参见王迁:《著作权法》,中国人民法学出版社2017年4月版,第27页。
[29]参见张伟君:《呈现于视听作品中的游戏规则依然是思想而非表达——对若干游戏著作权侵权纠纷案判决的评述》,载《电子知识产权》2021年第5期,第67-69页。
[30]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苏民终1054号民事判决书。
[31]“Video games are complex works of authorship – containing multiple art forms, such as music, scripts, plots, video, paintings and characters – that involve human interaction while executing the game with a computer program on specific hardware.”参见WIPO:《The Legal Status of Video Games: Comparative Analysis in National Approaches》, P7, para2.
[32]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苏民终1054号民事判决书。
[33]参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43540号民事判决书。
[34]参见李国强、宋巧玲:《以三国IP类游戏为例,谈游戏的审美体验和它的跨界性》,2018年08月28日发表于“腾讯游戏学堂”微信公众号。
[35]法院举例的“赵云”战法“银龙冲阵”的具体内容为:“随机对敌军单体发动2次攻击(伤害率150%),并使首次受到伤害的敌军单体受到攻击时的伤害提高0%(受攻击属性影响),持续 N/A回合”,认为该战法名系原告独创,结合了赵云武将的外形特点,其内容是对敌军武将的2次单体伤害,这也反应了孤身冲入敌方阵地的形象特点。
[36]参见杭州互联网法院(2019)浙0192民初8128号民事判决书。
[37]“Some scholars suggest that video games are essentially multimedia works that belong in the category of audiovisual works, affirming that these works are fundamentally a ―series of related images, following the most common definition of an audiovisual work provided in legislation around the world. However, one must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at these regulations also affirm that such images are ―intrinsically intended to be shown, which is not the final purpose of video games. On the contrary, video games are meant to be played and run using a computer program, with (inter)active implications for users, while audiovisual works, as currently defined, imply mostly passive viewer participation.”参见WIPO:《The Legal Status of Video Games: Comparative Analysis in National Approaches》, P7, para2.
[38]参见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16)沪73民终190号民事判决书。
[39]如“太极熊猫v.花千骨案”中,江苏高院参考了部分新浪微博用户发言及IOS系统关于涉案游戏相似的评论,并认为:“网络游戏的最终用户即网络游戏玩家对两款游戏的相似性感知及操作体验,亦是判断两者是否相似的重要考量因素”,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苏民终1054号民事判决书。
[40]参见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20)沪73民终33号民事判决书。
[41]参见冯晓青、孟雅丹:《手机游戏著作权保护研究》,载《中国版权》2014年第6期,第35页。
[42]参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5民初77945号民事判决书。
[43]参见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20)沪73民终33号民事判决书。
[4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经营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合法权益,且属于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章及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规定之外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予以认定。”
[45]参见韦之:《试论模仿自由原则》,载《中国专利与商标》2019年第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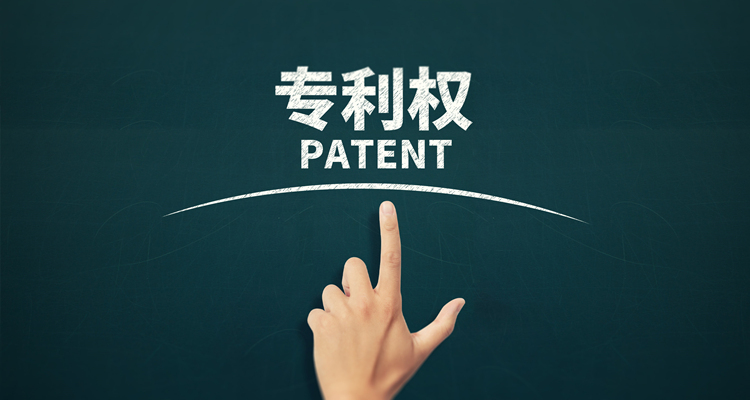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9464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946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