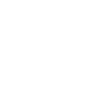文 | 何娅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
人工智能作为当今社会发展的一大特征,不仅早已上升到国家层面,也渗透到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人工智能创作的画作、音乐、诗集、文章、影视等已经屡见不鲜,这些人工智能的产物不仅具有极高的欣赏价值,还具有不小的经济价值。以计算机计算和大数据为支撑的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挑战着基于传统的自然智力而创作出的作品成果,在众多方面和领域中,其已经可以与之媲美甚至有所超越。例如,微软的人工智能小冰推出了“个人”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法院诉讼服务大厅的机器人可以准确提供法律检索、法律风险评估和法律咨询;谷歌的人工神经网络系统DeepDream可以创作出色彩斑斓的画作......这些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完整度、精准度、价值度以及速度等均达到了与普通作品难以辨别区分的程度。这不得不引发社会各界对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思考,即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属于作品?如果属于作品其著作权的归属应当如何定位?这不仅涉及法律问题,也关乎伦理问题。
一、人工智能生成物在著作权法层面的解读
人工智能是否为“人”。著作权法属于私法的范畴,适用民事法律制度,民事法律主体的“人”包含自然人和法人。创作是人类智力活动成果的体现,是人类精神世界的外在映射。一般而言,创作的主体为自然人,只有在特别的情况下,法人才能被视为作者,即《著作权法》第11条规定,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主持,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作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作者。
创作是一种表达,表现外在的结构形式,体现内在的逻辑构架,创作的目的在于交流,创作者通过创作将自己的内在精神世界展示出来,传达一定的价值观、自由意志,这是人类特有的活动。人工智能以大数据为基础,通过编程设置算法,完成固定的指令,该过程被预先设定好,是对人类既定指令的演算。人工智能不能跳出预先设置的计算模式和框架结构,也无法拥有自主意识进行自由思考,更不具备人类的精神世界,表达特定的价值取向。即便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人工智能可以实现与时俱进的更新,不断填补和学习新的知识和数据,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工智能拥有了独立的,平等于自然人的精神意识。
人工智能不能等同于人,那其是否可以像法人一样被赋予法律人格,从而被视为作者。法人被赋予法律人格之前,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此之前,对法人赋予民事主体资格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我国《著作权法》制定之初,法人也不是一开始就能成为作者,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最终赋予法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主体资格,承认其也可以创作,像自然人一样享有精神权利。可见,“智力成果”并不是自然人独有的,著作权法承认非生命体以外的主体成为创作主体,从而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者。人工智能虽然不具备独立思考的意志,没有具体价值取向,但是它为人所设计,代表了设计者的思想和意志,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工智能也可以像法人一样被视为作者。
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具备独创性。同大部分国家一样,我国著作权法采取思想和表达二分法的保护模式,不保护创作思路,只保护创作成果。独创性即独立创作,非抄袭和剽窃,要求作品具备最低限度的创造性,不考虑创作者的思维方式和思想内容。那么对于人工智能生成物,也可以抛却其算法规律、演算方式,主要考量其外在表现形式、表达表述。实际上,人工智能已经能够精准地模仿人类,其存储的超大数据库,高效的运算速度,表现的智力和创作水平已不亚于人类。同时,很多领域不再单纯依靠人类创作,而是综合运用人类劳动和人工智能,达到人机合一,以至于难以完全区分人为因素和人工智能因素。
最新修订的《著作权法》第三条增加了第九项“符合作品特征的其他智力成果”,也就是说只要具备独创性,有一定形式表现的“其他智力成果”就可以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人工智能生成物具备独创性无疑,如赋予其“智力成果”的属性,那么人工智能生成物也就是严格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
二、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司法保护模式
关于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典型判例目前全国法院有两例,一案为北京互联网法院于2019年4月25日作出一审判决的“菲林诉百度”案,该案也是我国“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著作权纠纷第一案”。涉案文章系原告北京菲林律师事务所通过威科先行库自动生成,后被告未经许可在其经营的百家号平台上发布被诉侵权文章。北京互联网法院认为,自然人创作应是著作权法意义上作品的必要条件,涉案文章的完成过程中仅有软件开发和软件使用两个环节有自然人的参与。但涉案文章不能传达软件设计者的思想情感,也不能传达软件使用者的思想情感,软件开发者和使用者均不能构成作者,即使其具备独创性也不能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但是,不能因此而排除涉案文章进入公众领域进行传播,为公众所学习,即原告对涉案文章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
另一案为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的“腾讯诉盈讯”案。原告深圳腾讯公司诉“网贷之家”未经其允许,抄袭腾讯机器人Dreamwriter撰写的文章,本案以腾讯胜诉结案。南山法院认为:涉案文章符合文字作品的形式要件,其表现形式体现了相关专业领域的知识,文章结构合理、表达逻辑清晰,具有一定的独创性。原告主创团队在数据输入、触发条件设定、模板和语料风格取舍上的安排与选择属于与涉案文章的特定表现形式之间具有直接联系的智力活动。该文章的特定表现形式及其源于创作者个性化的选择与安排,并由Dreamwriter软件在技术上“生成”的创作过程均满足著作权法对文字作品的保护条件,故认定涉案文章属于我国著作权法所保护的文字作品。
综上可见,不管是否将人工智能生成物定性为作品,无论是北京互联网法院还是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都对其内容给予了司法保护,承认其内容具有一定的独创性,只是保护方式和保护力度不同。北京互联网法院不承认其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则将其定性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导致这一差异的原因在于两家法院分析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创作时间点不同,北京互联网法院认为创作起算时间点应为该内容自然生成的时间,人工智能不是自然人,且其他自然人也未参与到内容生成过程中,其生成物虽具有一定的独创性,但不具备作品的形式要件,因此不属于作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则以自然人对人工智能进行条件设置、数据输入、算法设定的时间为创作起算点,整个创作过程直到按照特定条件设置的内容输出时为止。该创作过程糅合了自然人的意识,人工智能更像是一个被选择的工具,是完成创作的载体,最终的创作物具备了作品的形式要件和独创性,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对涉案标的物定性的不同,导致了两案对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司法保护途径不同,但均实现了司法上的公平正义。
人工智能的运用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趋势,其已经在游戏、电影、文学等各个产业发挥了创作的才能,这些作品具有独创性及一定的经济价值,创作高度达到了无法分辨其是自然人创作还是人工智能创作的程度。如果因为人工智能的“非人性”而否定其生成物的“作品性”,不利于对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保护,使之成为“天下免费的午餐”,人人皆可取之,也不利于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更不符合著作权法鼓励创作、方便公众学习的立法意图。因此,对人工智能生成物进行司法保护是必要的。
参考文献
[1](2019)粤0305民初14010号民事判决书。
[2](2018)京0491民初239号民事判决书。
[3] 徐小奔:《知识产权损害的价值基础与法律构建》,《当代法学》,2019年第3期。
[4] 易继明:《人工智能创作物是作品吗?》,《法律科学》2017年第5期。
[5] 王迁:《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在著作权法中的定性》,《法律科学》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