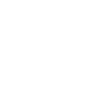文 | 李明德 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主任、教授
短视频是一种视听作品,由滚动的画面和伴音所构成。由于这类视听作品较为短小,因而称之为“短视频”。近年来,无论是在短视频的制作方面,还是在短视频的保护方面,都存在一系列问题。本文将从著作权法的角度,探讨短视频制作和保护中的一些问题。
一、电影、类电、视听作品
随着作品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尤其是摄影摄像技术、录音技术和播放技术的发展,出现了电影作品。早期的电影是无声电影,但很快就与录音技术相结合,成为了有伴音的电影。静态的“电影”由一幅幅“摄影”图片所构成,而在连续播放时就形成了我们所看到的滚动画面。英文中的“motion pictures”即反映了这样一个技术特征。
随着电影成为一个作品种类,其也逐渐被纳入世界各国的著作权法或版权法中。在这方面,《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规定,成员国应当予以保护的作品包括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1]近年来,一些国家和相关国际条约,又使用了“视听作品”的表达。例如,美国《版权法》第102条在规定受保护的作品种类时,使用了“电影和其他视听作品”的表达。又如,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主持下于2014年缔结的《视听表演北京条约》,也使用了“视听作品”的表达。
对于这样一种作品种类,我国《著作权法》在不同历史时期使用了不同的表达。例如1990年《著作权法》第3条规定,受保护的作品包括“电影、电视和录像作品”。2001年修订《著作权法》时,依据《伯尔尼公约》的规定,使用了“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表达。与此相应,在我国司法实践和学术研究中就有了电影和“类电作品”的说法。2020年修订《著作权法》时,则依据国际上近年来的惯例,使用了“视听作品”的表达。[2]
从著作权法的角度来看,无论是“电影、电视和录像”,还是“电影和类电”,或者是“视听”,都是一种表达,或者说是使用滚动画面和伴音(或者无伴音)的一种表达。正是从“滚动的画面加伴音或者无伴音”的角度出发,我们对于这类作品应当有一个最为宽泛的理解。假如使用“电影”的表达,则不仅常见的故事片、风光片、政论片可以纳入“电影”的范畴,而且各类电视节目,包括电视剧、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电视广告、天气预报,甚至是新闻30分、新闻联播中的每一个独立的报道,都可以纳入“电影”的范畴。假如使用“视听作品”的表达,不仅包括了上述提到的电影、电视,而且包括了音乐电视、电子游戏的画面和伴音,以及本文所要讨论的短视频。
从2020年《著作权法》的修订过程来看,立法者和一些专家学者显然没有对电影、类电、视听作品给予最为宽泛的理解。例如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20年8月公布的第二次审议稿,使用了“电影、电视剧作品和其他视听作品”的表达。将“电影、电视剧和视听作品”分别列举,显示了立法者是从日常和狭义的角度来理解“电影”“电视剧”。[3]后来,在相关专家学者的努力之下,最后修订完成的《著作权法》第3条使用了“视听作品”的表达。然而,修订完成后的第17条,仍然显示了立法者对于“电影”“电视剧”的狭义理解。根据该规定,“视听作品中的电影作品、电视剧作品的著作权由制作者享有”,其他“视听作品的著作权归属由当事人约定”。[4]
毫无疑问,从“滚动的画面加上伴音或者无伴音”这样一种表达方式来看,无论是使用“电影”的表达,还是使用“视听作品”的表达,都没有实质性的区别,视听作品绝对不是一类新作品。将“电影和类电作品”修改为“视听作品”,既没有扩大,也没有缩小这类表达的范畴。至于《著作权法》在2020年修订过程中使用了“电视剧”的表达,在修订完成后的第17条使用了“电视剧”的表达,则表明立法者过多地受到了日常用语的影响,没有从著作权法保护“表达”的意义上,将“电视剧”纳入“视听作品”的范畴。
二、短视频与独创性
如上所述,短视频属于“视听作品”或者“电影”。与此相应,短视频要想构成作品,获得著作权法的保护,则应当符合表达和独创性两个要件。
2020年修订的《著作权法》第3条,对作品下了一个定义,即“文学艺术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智力成果。”对于其中的“文学艺术科学领域”,应当给予最宽泛的解释,其可以涵盖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至于其中的“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智力成果”,则可以理解为“表达”。至于“独创性”,则是指受到保护的表达应当由相关的作者独立创作。与此相应,作品就是“具有独创性的表达”,分别由表达和独创性构成。
按照这样一个定义,由滚动的画面加上伴音而形成的“视听作品”,显然属于表达的范畴。或者说,“视听作品”是以连续画面和伴音的方式,表现了人的智力成果。从著作权法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表达所形成的作品,与文字表达、音符表达、形体动作表达、图形表达、数字表达所形成的作品,没有实质的区别。事实上,当前流行的“短视频”,完全可以纳入“视听作品”的范畴。因为短视频也是通过连续的画面和伴音,表达了人的智力成果。所谓的“短视频”,无非是指这类视频播放的时间较短而已。
按照作品的构成要件,由滚动画面和伴音所构成的视听表达,只有在具有“独创性”时才可以获得著作权的保护。首先,独创性是指,相关的表达来自作者,而非来自抄袭。具体到视听作品,则要求相关的画面和伴音来自作者,是由作者独立创作的。其次,独创性是指,相关的表达不仅应当来自作者,而且应当体现作者独特的精神、情感和人格。在这方面,《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第6条之二规定了对于作者精神权利的保护,即作者在转让了所有的经济权利之后,仍然享有署名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5]在这方面,《德国著作权法》和《日本著作权法》将作者所享有的这种权利,称之为“著作人格权”或者“作者人格权”。[6]由“作者精神权利”和“著作人格权”“作者人格权”等表达可以看出,构成作品的表达,包括视听表达,应当体现作者的精神、情感和人格。
从“视听”表达的概念出发,又引出了一个“录像”的问题。例如,法国《著作权法》不仅提供了对于视听作品的保护,而且提供了对于“录像”的保护。[7]在这方面,我国《著作权法》在保护视听作品的同时,也提供了对于“录像”的保护。[8]显然,从技术的角度来看,无论是“视听作品”还是“录像制品”,都是滚动的画面加上伴音(或者无伴音)。这样,二者的区别就在于,相关的“视听”或者“录像”,是否体现了作者足够的精神、情感和人格。如果体现了作者足够的精神、情感和人格,满足了《著作权法》所要求的独创性,就会构成“视听作品”,获得著作权的保护。如果没有体现作者足够的精神、情感和人格,则属于“录像或者录像制品”,可以获得相关权的保护。在法国和中国的著作权法中,这称之为“录像制作者权”。
三、短视频的“二次创作”
近年来,短视频的创作和传播逐渐成为一大热点。伴随着短视频的传播,一场关于短视频侵权的纷争也正在逐渐发酵。在B站、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影视剪辑类短视频随处可见。创作者将长达几十集的影视剧浓缩成若干短视频,择其最具情节张力的部分制作成视频合集。诸如此类的短视频屡见不鲜。
2021年4月9日,超过70家影视传媒单位发布联合声明,针对短视频制作中未经权利人许可的剪辑、切条、搬运、传播现象,发出维权警告,要求短视频平台提升版权保护意识。[9]根据报道,一些平台用户,专业从事影视素材的“搬运”活动,未经许可截取他人影视作品中的片段,进而形成自己的解说类、盘点类、混剪类的侵权作品(即“二次创作”),然后在相关的平台上传播。这类侵权作品的传播,往往还与流量、点赞、带货一类的商业活动相关。如此大规模发声,意味着短视频侵权已经触及了长视频平台的底线,并且引发了激烈的短视频侵权论证之战。[10]短视频侵权行为屡禁不止,其背后原因无外乎有两个,一是该类侵权行为侵权成本低、产量大,可以为行为人带来更多广告和流量;二是面对短视频海量信息,监管有所滞后,不少侵权者存在“法不责众”“天塌了有个儿高的顶着”等侥幸心理。且随着该类行为覆盖范围的不断扩大,其所带来的不利后果也逐渐加重。该类侵权行为不仅侵犯了创作者和相关有经营资质机构的权益,更打击、蚕食了原创精神,让文化市场上本就不足的原创精神雪上加霜。
短视频无疑是互联网迅速发展后为文化传播提供的重要引擎之一。然而,鼓励作者独立创作,反对复制和抄袭他人作品,是版权保护的一个基本原则,自版权制度产生以来,这一点从没有改变过。当然,人类创作任何类别的作品,都是在前人创作的基础上,都需要借鉴甚至借用既有的作品。短视频的制作在借鉴和借用其他作品时,即进行所谓的“二次创作”时,应当注意两个问题。
第一,版权制度仅仅保护表达,而不保护思想观念、科学发现、数学规则和技术方案。与此相应,后来的创作者完全可以自由借鉴他人作品中的思想观念等要素,形成自己独立的表达。事实上,作品的独创性就是指相关的“表达”是由作者“独立创作”的,而不要求思想观念和创意等要素是作者独立提出的。在这方面,短视频的制作者毫无疑问可以借鉴既有影视作品中的思想观念或者创意,运用滚动画面和伴音的手段创作自己的视听作品或者短视频。一旦超出此借鉴和借用范围,将会构成侵权。
第二,即使是“借用”他人的表达,也应当符合“适当”的原则。关于这一点,我国《著作权法》第24条第2项规定,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可以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但应当指明作者的姓名或者名称、作品名称,并且不得影响该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其中的“指明作者的姓名或者名称、作品名称”,意味着应当尊重他人的精神权利。至于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其目的仅限于为了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而非以新的作品替代既有的作品。而且,相关的引用还必须是“适当”的而非大量的。在这方面,大量“搬运”他人影视作品中的素材,显然超出了“适当引用”的范畴。
现在存在一种声音,即认为短视频的存在属于新现象,因此将围绕短视频而开展的“二次创作”认定为“侵权有理”。 短视频的出现是新现象,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禁止未经许可使用他人作品并超出适当引用范围”,这不是新规则,这个是从著作权法产生以后就有的规则,不能因为现象新就变成“侵权有理”。 著作权法鼓励独立、繁荣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向社会公众提供丰富多彩的精神食粮,但是反对抄袭是它亘古不变的基本原则。抄袭当然就是侵权,是著作权法所明令禁止的。反观当下,所谓的“二次创作”,其中又有多少是来自创作者本身呢?著作权或者版权保护表达,不保护思想观念、创意、技能。尽管人类创作作品总是基于前人的创作成果,但是此处主要是指使用前人的思想观念及创意等,包括各种观点和看法。正如上文所述,一旦短视频的制作超出了适当引用的范围,诸如未经许可的剪辑、切条、搬运、传播等“二次创作”行为,基本上都应当被认定为侵权行为,当然,具体到个案中,法院还可以就此再进行深入审查。
针对此类愈演愈烈的短视频侵权行为,为了让网络视听产业走得更稳健、更长远,对于侵权行为进行反击就显得尤为重要。影视媒体企业一方面要求那些剪辑制作者停止侵权,另一方面则要求短视频平台提升版权保护意识,采取必要的制止侵权的措施。的确如此,构建良性的网络视频版权生态,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既要有市场主体对自己权利的重视,也要有市场主体对他人权利的尊重。从著作权维权来说,除了权利人要主张权利,其他竞争者也要既保护自己的权利,同时尊重他人的权利,不能无偿利用他人的智力活动成果,获得自己的市场利益,这肯定属于不劳而获,或者可能在过程中添加了自己的东西,那就属于少劳多获,这也都是不公平的。具体到权利人这一重点维权群体,无论创作的视频是长或短,针对上述所谓的“二次创作”行为,权利人都应当积极采取法律措施,有时候并非必然需要诉诸诉讼,可能通过发律师函抑或是提起行政投诉等途径也可以解决相关问题。
四、短视频与权利归属
如前所述,短视频属于“视听作品”,而“视听作品”与“电影作品”、“类电作品”,又具有概念上的可互换性。或者说,无论是“电影作品”、“类电作品”,还是“视听作品”或者“短视频作品”,都是由滚动画面和伴音所构成的作品。
“电影作品”或者“视听作品”,是由多位作者共同完成的作品。例如脚本作者、音乐作者、美术作者、分镜头作者。又如导演、演员、摄像,以及后期剪辑和制作合成人员等等。如果按照谁创作谁享有权利的理念,则一部电影作品的著作权可能归属于若干个作者和演职人员所有。如此一来,无论是行使发表权还是复制权、放映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都会成为一个问题。因为,每个权利人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和要求。同时,无论是电影作品还是视听作品,都是需要花费巨额投资而创作完成的作品。在这方面,制片人要从事融资的活动,要发起和组织某一电影或者视听作品的拍摄,要与脚本、音乐、美术作品的作者签订许可合同,要雇佣导演、演员、摄像、后期剪辑和制作合成的演职人员。除此之外,制片人还要将制作完成的电影或者视听作品推向市场,通过复制、发行、放映、广播和信息网络传播等方式,收回自己的投资和成本,并且赚取必要的利润和从事新的拍摄工作。
正是基于电影或者视听作品的这种特点,世界各国的版权法或者著作权法通常都规定,电影或者视听作品的每一位合作者享有署名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这是对于作者精神权利的尊重。当然,就电影作品或者视听作品而言,保护作品完整的尺度相对宽松一些。因为最终合成的电影作品或者视听作品,受到整体效果、播放时长、观众反馈等因素的制约,对于每一个作者所创作的表达进行改变的可能性较大。按照《伯尔尼公约》第6条之二,只要这种改变没有达到损害作者名誉或者声誉的程度,就没有侵犯作者的保护作品完整权。[11]同时,按照世界各国的版权法或者著作权法,由电影或者视听作品的创作而产生的经济权利,例如复制、发行、放映、广播、信息网络传播等等,则归属于制片人所有。一方面,由制片人享有和行使经济权利,可以保障电影或者视听作品的上市和商业化利用,不会受到众多作者的制约。另一方面,由制片人享有和行使经济权利,还可以鼓励制片人投资电影或者视听作品的拍摄,保障制片人在电影或者影视作品的市场化运用中收回投资和获得利润。
关于电影或者视听作品经济权利的归属,世界各国有两种做法。在英美等版权法体系的国家,通常依据雇佣关系的理念,将电影或者视听作品的版权归属于制片人所有。按照雇佣关系,制片人相当于雇主,导演、演员、音乐、美工和后期剪辑、制作合成者,相当于雇员。与此相应,经由雇佣关系而产生的电影或者视听作品,版权归属于制片人所有。例如,美国《版权法》第201条规定,在雇佣作品的情况下,版权归属于雇主,除非双方当事人有相反的约定。又如,《英国版权法》规定,除非合同另有约定,在雇佣过程中完成的作品,包括电影作品,雇主为该作品的原始版权所有人。[12]
而在欧洲大陆的著作权法体系国家,依据谁创作谁享有权利的理念,通常认定电影或者视听作品的经济权利,在源头上归属于相关作者所有。但同时又规定,在参与电影或者视听作品制作时,如果相关的作者和演职人员与制片人缔结了合同,则推定他们已经通过合同约定,将利用作品的经济权利转让或者许可给了制片人。例如《法国著作权法》规定,如果参与电影制作的作者与制片人缔结了合同,如无相反的约定,推定将利用视听作品的权利转让给了制片人。又如《德国著作权法》规定,参与电影制作的作者,如果没有相反的约定,推定将其利用电影作品的专有权利授予了制片人。[13]
在这方面,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既不同于英美版权法体系的做法,也不同于欧洲大陆作者权法体系的做法,而是直接由法律做出规定,电影或者视听作品的经济权利归属于制片人所有。例如,我国1990年《著作权法》第15条规定:“电影、电视、录像作品的导演、编剧、作词、作曲、摄影等作者享有署名权,著作权的其他权利由制作电影、电视、录像作品的制片者享有。”又如,我国2001年《著作权法》第15条规定:“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但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等作者享有署名权,并有权按照与制片者签订的合同获得报酬。”显然,通过法律规定的方式,将电影或者视听作品的经济权利归属于制片人所有,有利于相关作品的市场化利用,有利于制片人收回成本和赚取必要的利润。
然而2020年修订的《著作权法》第17条,却在电影或者视听作品经济权利的归属上,做出了一个别出心裁的规定。其中的第1款规定:“视听作品中的电影作品、电视剧作品的著作权由制作者享有,但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等作者享有署名权,并有权按照与制作者签订的合同获得报酬。”显然,就视听作品中的“电影作品、电视剧作品”而言,这个规定仍然延续了原来的权利归属原则,即编剧、导演等作者享有署名权,经济权利归属于制片者享有。然而,其中的第2款则规定:“前款规定以外的视听作品的著作权归属由当事人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由制作者享有,但作者享有署名权和获得报酬的权利。”按照这个规定,电影作品、电视剧作品以外的“其他视听作品”,则在经济权利的归属上,遵循有约定按约定,无约定归属于制片者所有的原则。显然,这个规定有可能在视听作品的保护实践中造成一些问题。
第一,如何在电影作品、电视剧作品与其他视听作品之间划出一条界线。如前所述,无论是称之为“电影作品、电视剧作品”还是“视听作品”,都是以滚动画面和伴音的方式来表达某种思想观念或者创意。从著作权法的角度来说,只要滚动的画面和伴音满足了表达和独创性的要求,就可以构成电影作品、电视剧作品或者视听作品。现在硬生生地将“电影作品和电视剧作品”从视听作品中分离出来,并且将电影作品和电视剧作品以外的视听作品称为“其他视听作品”,其划分的标准显然不是作品的构成要件。如果是采用艺术的标准、故事情节的标准,或者主题、内容的标准进行划分,在相关的保护实践中如何适用这类标准,就会成为一个问题。
第二,在相关权利的转让和许可过程中,如何确定“其他视听作品”的权利归属。按照《著作权法》第17条第2款的规定,显然会有一些“其他视听作品”,通过约定的方式确定权利的归属。这样,在相关视听作品转让和许可的实践中,就需要受让人和被许可人确定,究竟谁是可以从事转让或者许可的权利人。如果没有找到适格的权利人,则有可能产生虚假的转让或者许可。显然,这增加了市场交易的成本和不确定性。
在2020年修订《著作权法》的过程中,立法者做出第17条第2款的规定,显然是回应了一些编剧、导演希望自己也能成为制片者的诉求。事实上,编剧、导演,包括词曲作者、美术作者、脚本作者,以及摄像、演员和后期剪辑制作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肯定是行家里手,可以创作出很好的视听作品。然而,拍摄视听作品的融资,组织视听作品的制作,与相关作者和演职人员谈判和缔结合同,以及将制作完成的视听作品推向市场,进行商业性的运营,这些完全是另外一个专业领域的事情。事实上,在欧美各国和其他很多国家,编剧、词曲作者、美术作者,导演、演员、摄像等演职人员,通常是在与制片人缔结相关合同时,争取自己的最大利益,然后从事自己熟悉的创作工作。至于融资、组织制作、市场运营等工作和相应的其他风险,则交由制片人处理。显然,由制片者享有相关电影或者视听作品的经济权利,是社会分工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大体说来,经过学术界的澄清和努力,2020年修订的《著作权法》在其第3条关于作品种类的规定中使用了“视听作品”的表达,这显然是一个著作权法意义上的表达。然而,立法者仍然坚持原来的“电影作品、电视剧作品”和“其他视听作品”的表达,在第17条中既使用了著作权法意义上的“视听作品”的表达,又使用了其他领域的“电影作品、电视剧作品”的表达。正是沿着这样的错误思路,进而规定了电影作品、电视剧作品和其他视听作品的权利归属原则。或许有必要在这里指出,《伯尔尼公约》使用的“电影作品”和“类电作品”,以及很多国家著作权法或者版权法使用的“视听作品”,都是一个法律术语。而我国《著作权法》第17条使用的“电影作品、电视剧作品”,尤其是“电视剧作品”,则显然不是一个法律术语。而使用统一的“视听作品”这一表达,统一规定视听作品的权利归属原则这一问题,只能留待下一次《著作权法》的修订予以解决了。
注释:
[1] 参见《伯尔尼公约》第2条。
[2] 参见1990年《著作权法》、2001年《著作权法》、2020年《著作权法》第3条。
[3] 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著作权法修正案(草案)(第二次审议稿)》,2020年8月。
[4] 参见2020年《著作权法》第17条。
[5] 参见《伯尔尼公约》第6条之二。
[6] 参见《德国著作权法》第四章第二节“著作人格权”;《日本著作权法》第二章第五节“作者人格权”。
[7] 参见《法国知识产权法典》第215条。
[8] 参见《著作权法》第四章第三节“录音录像”,以及第42条、第43条和第44条。
[9] 参见央广网4月10日报道,《超70家影视传媒单位企业联合声明,呼吁短视频平台提升版权意识》。
[10] 参见《爱优腾齐轰短视频侵权:二次创作掩盖盗版本质》,系于2021年6月3日召开的中国网络视听大会报道,载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1616939526060624&wfr=spider&for=pc,访问时间:2021年6月9日。
[11] 参见《伯尔尼公约》第6条之二,作者有权反对他人对其作品进行歪曲、肢解、篡改或者其他贬低其作品的行为,而且这些行为损害了作者的名誉或者声誉。
[12] 参见《美国版权法》第201条“版权归属”;《英国版权法》第11条“版权的原始归属”。
[13] 参见《法国知识产权法典》第132-24条;《德国著作权法》第89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