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刃 江苏新天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Bolar例外”的确立与发展
“Bolar例外”源自于美国联邦上诉法院对Roche Products公司和Bolar Pharmaceutical公司一案[1]的判决,故命名为“Bolar例外”。根据美国《专利法》第271条(35 U.S.C. §271)之规定,除该法另有规定外,在专利保护期内,任何人未经许可在美国境内实施制造、使用、许诺销售或销售取得专利权的发明之行为,即构成侵害专利权。但美国《药品价格竞争与专利期限恢复法案》(Hatch-Waxman法案)尚有如下规定:基于规范药品制造、使用或销售的联邦法律的要求,仅为药品开发和提交上市审批材料而制造、使用或销售专利产品的,不视为侵权。Hatch-Waxman法案被补充进了美国专利法第271条第5款中,简称“Bolar例外”。依照美国专利法第271条第5款第(1)项的规定,他人为了获取FDA进行审批所需要的信息,可以在专利权保护期限届满之前实施有关专利以进行必要的研究试验;但是依照第271条第5款第(2)项的规定,不能在专利权保护期限届满之前向FDA提交制造、使用、销售该药品的申请,否则将构成侵犯专利权的行为。
设立该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克服药品和医疗器械上市审批制度在专利权期限届满之后对仿制药品和仿制医疗器械上市带来的延迟[2],其核心要义在于,仅为获得和提供药品或者医疗器械行政审批所需要的信息而以特定方式实施专利时,不视为侵犯专利权。
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相继确立“Bolar例外”后,我国在2008年《专利法》第三次修改中也作出相应调整,将国际上普遍认可的“Bolar例外”条款纳入《专利法》体系内。我国现行《专利法》第75条第5款规定“为提供行政审批所需要的信息,制造、使用、进口专利药品或者专利医疗器械的,以及专门为其制造、进口专利药品或者专利医疗器械的”,不视为侵犯专利权。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引入“Bolar例外”制度,在医药专利权到期后,仿制企业能够及时进入市场,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使得民众能够实现对药品和医疗器械的有用、安全和有效的需求。[3]“Bolar例外”制度有效提高了社会公众药品可及性的程度,同时有助于缓和仿制药企业和专利药企业之间利益冲突的紧张局面,但在实践中尚存在理解与适用方面的诸多争议。
二、从典型案例看“Bolar例外”在中国的适用
(一)“安斯泰来案”
在安斯泰来制药株式会社、麦迪韦逊医疗公司诉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润众制药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一案[4]中,原告安斯泰来株式会社、麦迪韦逊公司是200680025545.1号发明专利的被许可人,该专利的申请日期是2006年3月29日,授权日期是2012年4月18日。2015年,正大天晴公司、润众公司共同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提出恩杂鲁胺原料药的注册申请(药品名称:恩杂鲁胺,受理号:CXHL1500217苏),被告正大天晴公司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提出恩杂鲁胺胶囊的注册申请(药品名称:恩杂鲁胺胶囊,受理号:CXHL1500218苏),两申请于2016年5月获得临床试验批件。在新药申报过程中,被告润众公司主要负责恩杂鲁胺原料药的申报,被告正大天晴公司负责恩杂鲁胺胶囊的申报。经庭审比对,两原告认为,被控侵权产品的化学结构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3描述的化合物RD162'式相同,落入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两被告抗辩认为,两被告申报注册药品中所涉及的药品名称是恩杂鲁胺,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3描述的化合物RD162'的化学结构式一致,是相同的化合物,但并未落入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具体理由在于权利要求3是独立权利要求1的从属权利要求,权3所描述的结构式特征并不在权利要求1的保护范围之内,两者自相矛盾,保护范围不清楚。在此基础上,并不能得出被告申报注册药品恩杂鲁胺即落入涉案专利权利要求3保护范围的结论。在专利侵权判定层面,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此项抗辩不能成立,被控侵权产品落入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本案中,两被告提出了“Bolar例外”抗辩,认为其行为属于为提供行政审批所需要的信息,制造、使用专利药品,依法不视为侵犯专利权。原告方认为,涉案专利的申请日为2006年,授权日为2012年,而两被告在2015年即专利授权后的第三年(此时距专利期满尚有11年),即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提出药品注册申请,被告的行为违反了《药品注册管理办法(2007年)》第十九条“关于药品专利期满两年之前不得申请药品注册”的规定,不具有合法性。争议在于,专利法在“Bolar例外”条款中并未规定仿制药注册申请时间问题,是否意味着在专利保护期内的任何时间他人均可进行仿制药注册申请,此时《药品注册管理办法(2007年)》第十九条的规定是否应当纳入“Bolar例外”的解读?本案受理法院的观点是,《药品注册管理办法》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布的部门规章,药品注册申请人的行为有无违反该管理办法的规定,属于行政管理的范畴,而本案为专利侵权纠纷,应由法院依据有关专利的法律法规进行处理,故两被告申请注册涉案药品的行为有无违反《药品注册管理办法(2007年)》的相关规定不属于案件的审理范围,法院对此不予理涉。两被告制造和使用涉案专利化合物是为了恩杂鲁胺药品注册申请获得临床批件的需要,符合《专利法》第六十九条(新《专利法》第七十五条)第(五)项的规定,故不构成专利侵权。
(二)“恩必普案”
在石药集团恩必普药业有限公司诉丽珠集团利民制药厂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一案[5]中,原告系02123000.5号发明专利的共同权利人之一,该专利的申请日为2002年6月17日,授权日为2004年9月15日。原告经过检索药品评审中心的官方网站,查询到受理号为CYHS1600199的“丁苯酚氯化钠注射液”于2017年5月18日进入该中心,企业名称为“丽珠集团利民制药厂”,申请类型为“仿制”,注册分类为“4”,当时正处于“排队待评审”状态,遂提起专利侵权诉讼。
并无意外,本案被告也提出“Bolar例外”抗辩。该案受理法院认为,被告丽珠制药厂向药品评审中心申报涉案仿制药的行为系一种请求行政机关给予行政许可的行为,其直接目的并非为生产经营目的,向国家药品行政管理机关提出药品行政审批的行为不属于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中的任一行为,因此不构成专利侵权。关于是否落入专利的权利要求保护范围问题,法院的观点是,即使被告丽珠制药厂确实使用涉案专利向药品评审中心提出药品申请并以申报涉案仿制药为目的,少量制造被控侵权的药品,但依据《专利法》第六十九条(新《专利法》第七十五条)第(五)的规定,被告的行为也不构成侵犯原告恩必普公司的专利权,因此,法院认为已无必要对涉案仿制药是否落入了涉案专利的保护范围进行审查。
上述两个案件中,被告提交行政审批手续均早于涉案专利权到期前两年,并且其提交的文件还存在其他方面的瑕疵,法院在判决时直接援引专利法规定的“Bolar例外”条款,均未评述被告提交行政审批管理手续的合法性问题,以及该问题的存在是否影响“Bolar例外”的适用,在理论界和实务届产生了较大的争议。
三、“Bolar例外”的限制
笔者认为,上述两判决存在值得商榷之处,“Bolar例外”制度的本质仅仅是“不视为侵犯专利权”的一种例外情形,不加限制的机械适用或扩大解释不利于专利权的保护,并可能阻碍医药领域的创新。
(一)“例外”的例外之——合法性限制
从法律解释的角度分析,现行《专利法》第75第5款的“行政审批”理应以药品管理所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的规定来进行解释和理解,上述专门规范性文件所禁止的行为并不产生《专利法》规定的“为提供行政审批所需要的信息”这一前提。
“Bolar例外”条款规定的符合“为提供行政审批所需要的信息”是专利侵权行为被豁免的前提,而此申请审批行为本身的合法性问题显然应当纳入是否可以享受豁免的考量范围。一项不合法的申请行政审批行为本应受到负面评价,甚至接受行政处罚,该行为的实施不应当产生新的权利,哪怕只是对抗请求权的抗辩权。笔者认为,判定申请审批行为合法性时,应当考虑该行为是否符合《药品注册管理办法(2020)》第10条第2款(质量可控)、第18条(信息公示)、《实施办法(试行)》第4条(信息公示)、第6条(专利声明)等规定,进而判断能否适用“Bolar例外”。
(二)“例外”的例外之二——客体限制
“Bolar例外”适用的争议还存在于对“药品”和“医疗器械”范围的理解。从广义角度看,“药品”涵盖三种类型[6]:一是用于预防、诊断、治疗人体疾病的药品;二是用于治疗动物疾病的兽药;三是用于预防、消灭或者控制危害农业、林业的病、虫、草和其他有害生物的农药。有学者认为,我国既是人口大国,也是农业大国,对农药和兽药的需求十分旺盛,目前国内市场上流通的农药、兽药专利大多由国外公司持有,适度放宽“Bolar例外”的适用范围系对现实国情的考量。
笔者认为此观点缺乏理论依据与法律基础。在医药专利领域之所以出现大量区别于其他专利的特殊制度,源自于生命健康权与专利权的冲突,基于伦理考量,专利权作出适当的退让,但此退让必须是适度的、有限的,否则将动摇专利制度的基础,不利于药品的研发与创新,最终反而不利于保护生命健康。显然,此处的生命健康权特指人类,并不包括动植物。根据《药品管理法(2019)》第2条第2款之规定,“本法所称药品,是指用于预防、治疗、诊断人的疾病,有目的地调节人的生理机能并规定有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用法和用量的物质,包括中药、化学药和生物制品等。”《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103条也规定“医疗器械,是指直接或间接用于人体的仪器、设备、器具、体外诊断试剂及校准物、材料以及其他类似或者相关的物品。”《药品注册管理办法(2020)》第10条第3款规定“使用境外研究资料和数据支持药品注册的,其来源、研究机构或者实验室条件、质量体系要求及其他管理条件等应当符合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要求协调会通行原则,并符合我国药品注册管理的相关要求。”由此可见,我国现行立法规定的“药品”与“医疗器械”均仅限于人体服用或使用。
(三)“例外”的例外之三——时间限制
原《药品注册管理办法(2007)》第19条规定:“对他人已获得中国专利权的药品,申请人可以在该药品专利期届满前2年内提出注册申请。”新修订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2020)》已删除该规定,此举意味者仿制药品的注册申请不再受药品专利期限的约束,理论上讲,在药品专利有效期内的任何时间他人均可注册申请仿制药。可以想见,医药领域的专利侵权诉讼数量将快速增长,仿制药生产商“bolar例外”抗辩成功的概率也将大大提升。有鉴于此,2021年7月4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发布了《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决机制实施办法(试行)》;2021年7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申请注册的药品相关的专利权纠纷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上述两规定共同构建了我国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决机制。笔者认为仿制药审批等待期规定为九个月时间过短,如果后续没有专门的制度性安排,法院几无可能在九个月内作出生效判决,国家知识产权局的行政裁决在九个月内更不可能终局性生效,因此,上述新规定能否在仿制药上市之前有效地解决专利纠纷尚待实证研究。
专利法规定“bolar例外”制度系考虑到药品和医疗器械关乎公共安全和人民身体健康,临床试验与数据报批往往需要数年时间,如果在专利到期后才能提交仿制药的审批资料,必然导致仿制药的上市会在专利权到期后数年,变相延长了专利权的保护期。该制度体现了知识产权利益平衡原则,诚为良法,但若在实施过程中完全不考虑专利权保护期的剩余时间,似有矫枉过正之嫌。笔者认为,在距离专利权期限届满为时尚早之时,即以提交行政审批为名,实施他人专利的行为(特别是制造数量远超报批所需合理数量的行为)不具有正当性。此处需要讨论的是如何判定“为时尚早”?考虑到不同类药品的实际审批时间往往有较大差异(例如抗生素和治疗癌症的药品),原《药品注册管理办法(2007)》第19条统一规定在专利期届满前2年内可提出仿制药注册申请似乎不妥(《药品注册管理办法(2020)》已删除此条款),但笔者认为“为时尚早”问题在诉讼中至少应当作为一项可辩的事实,由原被告双方就涉案药品申报审批所需合理时间进行举证说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在条件成熟时也可以定期发布各类药品、医疗器械行政审批平均周期作为指引和参考,对于显著超过审批所需合理时间的实施专利的行为,特别是制造数量远超报批所需合理数量的行为,仍然应当依法判定是否构成专利侵权。
注释:
1.221 USPQ 937, cert denied(1984);733 F.2d 858. 参见尹新天:《专利权的保护》(第2版),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第225页。
2.程永顺、吴莉娟著:《新<专利法>中的药品保护研究》,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7页。
3.参见闫海、王洋、马海天等:《基于药品可及性的专利法治研究》,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5页。
4.参见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1民初529号民事判决书。
5.参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7)京73民初1584号民事判决书。
6.参见宁立志:《我国“Bolar例外规制”的学理结构与制度重建》,载《政法论丛》2019年第2期,第4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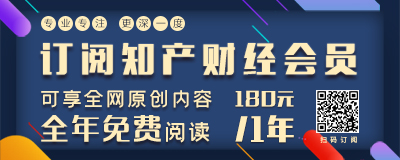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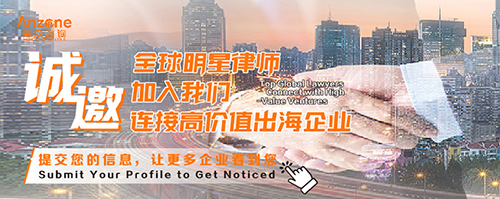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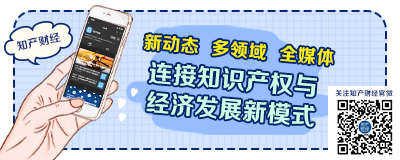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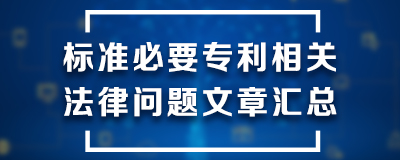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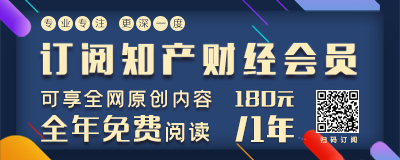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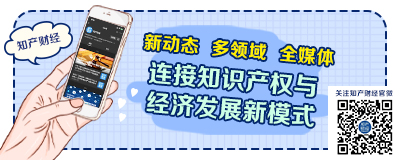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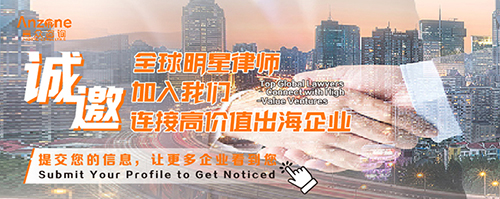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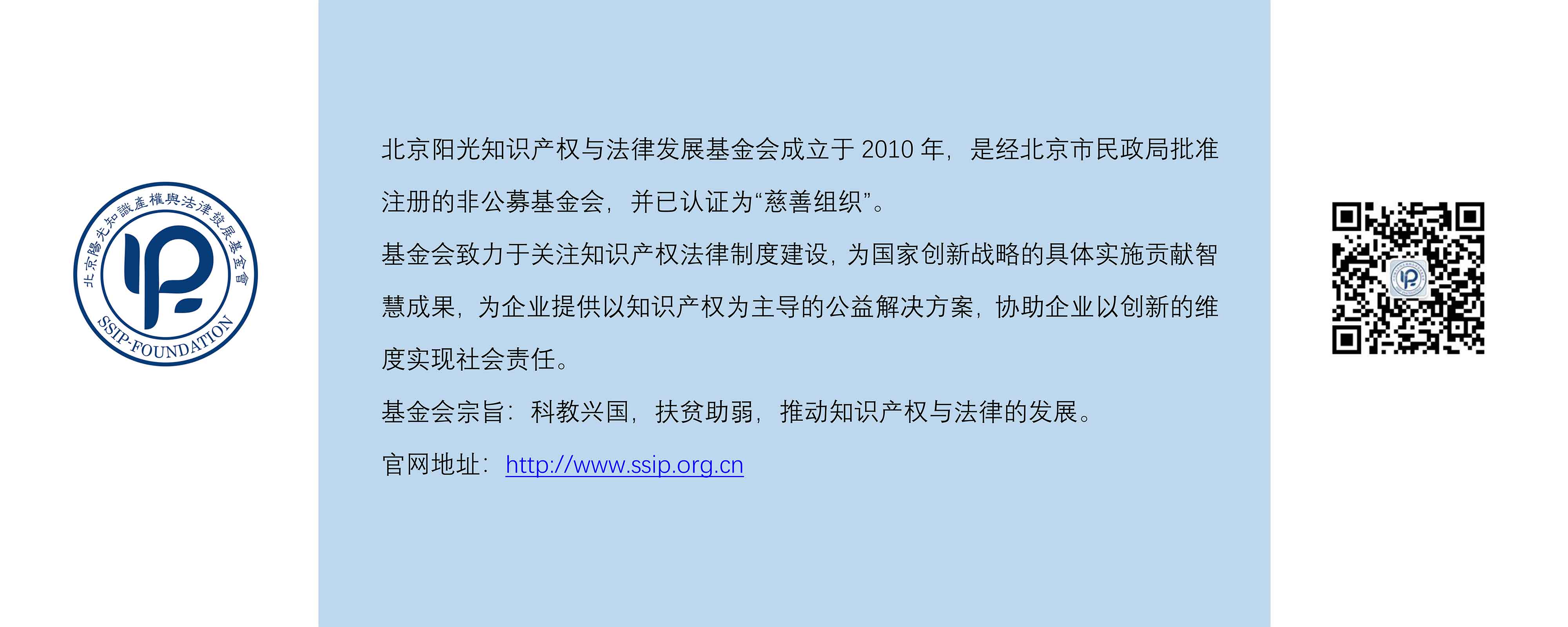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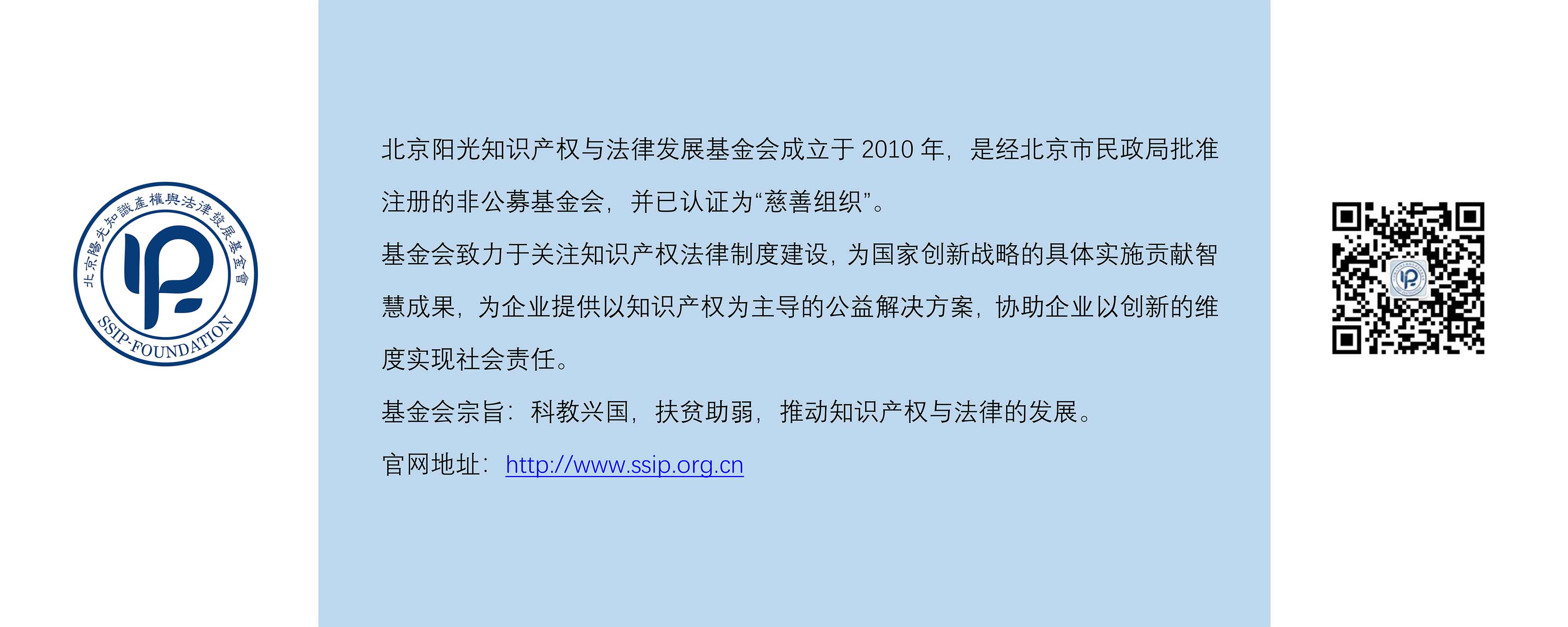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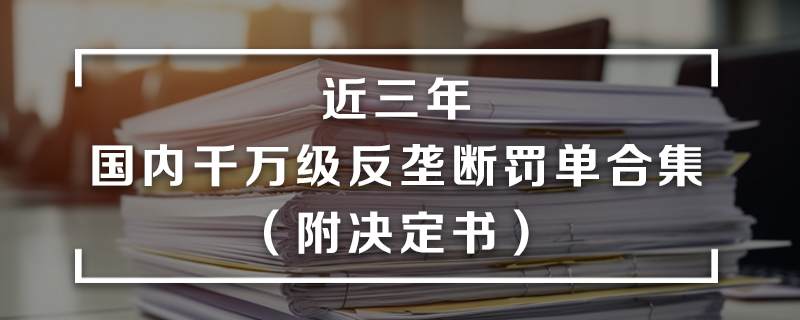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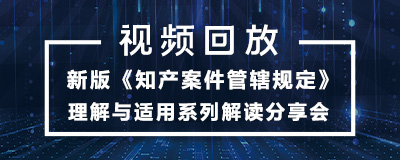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9464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946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