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迎接第25个“世界知识产权日”,长沙市天心区法院依例公布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系列典型案例,以此浓厚知识产权保护氛围,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践行阳光司法与为民司法。本期主题为:商业性公司著作权维权的原告主体适格问题。
近年来,商业性公司进行著作权维权的案件数量大增,形成产业化、链条化、逐利化的批量维权模式,市场化的趋势明显。其中诸多商业性公司仅从著作权人处获得作品维权的权利,并未真正获得包括复制、发行、信息网络传播等在内的实体权利。对于仅获得著作权维权权利而未获得实体权利的商业公司,以自己名义的起诉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一直为司法实务界所普遍关注。
近日,天心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以授实体权利之名行仅授诉权之实的案件,最终法院裁定驳回了原告的起诉。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让我们来一起看看这起案例。
案情简介
杭州某科技公司系沉浸式剧本游戏(俗称:剧本杀游戏)《骨语》的著作权人。2023年7月6日,作为授权人的杭州某科技公司与作为被授权人的沈阳某知识产权公司签订《授权书》,约定授权人将《骨语》复制权、发行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改编权、摄制权等其他著作权财产权,以独家授权的形式授予被授权人行使,且被授权人还有以自己名义维权的权利。授权期限为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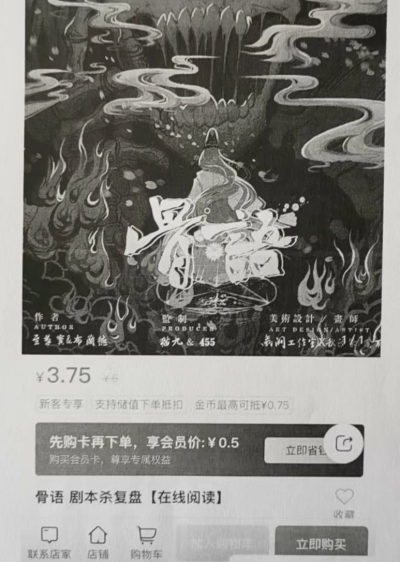
原告在案涉微店中的购买证据
沈阳某知识产权公司发现,长沙某网络公司未经允许,其微信公众号转链接跳转至出售案涉作品的另一网络微店。于是,沈阳某知识产权公司以自己的名义将长沙某网络公司作为被告诉至法院,认为被告构成帮助侵权,并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停止销售侵犯原告复制权、发行权及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作品;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合计10000元。
一、2025年1月24日庭审中,原告的陈述与主张:
1.被告公众号转链接跳转售卖案涉作品,因微店主体信息没有披露,故无法查实微店主体真实身份;
2.被告并非直接售卖,系帮助微店主体侵权,属帮助侵权,因被告已经停止侵权了,无法当庭重复操作演示;
3.原告获得案涉作品的独家授权,但只进行了诉讼维权,并未实际使用和运营作品,也未支付相应授权费用;
4.原告以自己名义在广东、四川、重庆等法院进行了数起维权诉讼。
二、其他查明情况:
1.杭州某科技公司作为案涉作品的著作权人于2023年7月11日在四川版权局进行了作品版权登记;
2.授权书后附有作品清单为案涉作品等三部作品,并特别注明“以上为部分作品列举,具体作品以授权人实际支付为准”。
法院裁决
天心区法院经审理认为
虽然原告与杭州某科技公司签订的《授权书》载明了包括发行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等实体权利在内的授权,但是为期二年的授权使用期至本案开庭日已逾一年六个月,原告仅用案涉作品进行数起维权,并未进行实际使用和运营,亦未对价支付使用费,结合原告授权作品清单为部分列举的开放式授权情况等,可判断原告与杭州某科技公司约定授权独家使用条款有规避只单独授权维权之嫌。
以主观见之于客观判断,原告无意且实际未对授权作品进行使用运营,取得授权仅为获得维权的权利即程序性权利。故此,原告无有效证据证明其真正取得著作权人实体权利授权,说明其与案涉纠纷不具有直接利害关系,无权以原告的身份提起维权诉讼,对其起诉应予驳回。
2025年2月6日,天心区法院裁定:驳回原告沈阳某知识产权公司的起诉。
一审宣判后,当事人未上诉。
法官说法

案件承办法官 彭丁云
知识产权保护需要让“真创新”受到“真保护”,“高质量”受到“严保护”,但在著作权领域内,较普遍存在著作权人授权商业性公司以商业性公司名义只进行诉讼维权的现象,如此弊端重重:商业性公司过分强调商业利益则会不利于纠纷的实质性化解;商业性公司中参与诉讼人员因缺乏法律职业资格与执业经验技能,不利于案件事实查明与诉讼推进,甚至可能出现有违法律职业道德风险;商业性公司如再授权律师代理会不当增加维权成本等。
这种商业性批量诉讼维权,成为了一种商业策略和牟利工具,如上所述,会催生一系列有违法律和道德的风险。如何引导或者规制这种现象与趋势,需要回到著作权程序权利是依赖并保障实体权利的特质与功能上来,即著作权维权诉权只有与实体性权利一并转移或许可时,这样的维权诉讼才可取和值得鼓励,以自己名义起诉的商业性公司与诉争事项才有真正意义上的直接利害关系。
但需要说明,尽管只进行维权商业性公司因主体资格存在问题而被驳回起诉,但对著作权人而言,其包括诉权在内的其他权利并未因此受限与影响,仍可以自行进行诉讼维权,或者将实体性权利与维权程序性权利一并实质授予的主体进行诉讼维权。这也就是说,只要满足有助于实质促进作品的推广使用、创作者的创作创新和著作权人财产性权益合法实现等条件,著作权人或者所授权主体采取的维权方式都在肯定、鼓励范围内。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9464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946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