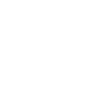文 | 祝建军 深圳知识产权法庭法官
一、问题的提出
国际社会为了解决无线通信的互联互通问题,通过建立国际标准组织并使各标准组织成员国采用统一的技术标准来实现该目标,国际范围内的技术标准应运而生。各国参与无线通信标准制定的企业,为了收回投入研发技术标准的成本,并获取较高的经济利益,在标准提案或技术标准被公开前,将相关技术标准在各个国家申请专利,标准必要专利随之产生。所谓标准必要专利是指实施标准时必然要使用的专利。标准必要专利通常在技术上具有不可替代性、必然实施性和事实上的强制性。正是由于标准必要专利具有上述特点,为了防止专利堆叠和专利劫持行为,各国际标准组织通常都要求其加入成员(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对自身持有的标准必要专利按照公平、合理、无歧视的FRAND原则对外进行授权许可。
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就某一技术标准在各国通过申请所取得的专利表现出地域性和同族性的特征,而无线通信企业所生产和销售的无线通信产品通常在世界范围内流通,表现出跨国性。如此一来,标准必要专利的地域性、同族性与使用标准必要专利生产、销售无线通信产品的国际性交织在一起。为了节约成本、提高谈判效率,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与标准必要专利实施人在市场交易中所涉及的许可谈判范围,通常涵盖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所拥有的全球同族标准必要专利、标准必要专利实施人在全球范围内所销售的产品,并以非排他、有偿许可的方式进行许可授权。当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和实施人通过谈判无法达成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协议而引发纠纷时,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和实施人均可以通过请求法院裁决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率的方式来解决双方之间的纠纷。
关于当事人请求司法裁决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率的范围,从世界各国的司法实践来看,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是请求裁决全球许可费率,比如,最近英国法院在Unwired Planet International Ltd.(以下简称UP)诉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为)侵害专利权禁令救济纠纷一案中,主动为双方当事人裁决UP全球标准必要专利包的许可费率,并通过颁发禁令来保障其裁决得以执行。【1】英国法院的裁判做法,随后吸引了康文森、IDC等NPE采用UP诉华为案相同的诉讼主张来要求解决与实施人之间的许可费率纠纷。二是请求裁决中国许可费率,比如,南京知识产权法庭在华为诉康文森无线许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文森)标准必要专利许可使用费纠纷案件中,根据华为的诉讼请求,判决了康文森应许可给华为中国区域的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率。【2】
通过上述论述,不禁让人思考如下问题:既然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和实施人在许可谈判时以全球许可费率作为谈判范围,那当事人选择在中国法院提起标准必要专利中国许可费率之诉,是否违反FRAND原则?提起标准必要专利中国许可费率之诉的前提条件是什么?标准必要专利中国许可费率应如何确定?
二、当事人请求裁决标准必要专利中国许可费率是否违反FRAND原则
有观点认为,根据业界谈判惯例,基于节约成本、提高谈判效率的考量,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和实施人在进行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谈判时,通常是以全球许可作为双方谈判的范围,即持该观点的人认为,只有同意全球许可谈判才符合FRAND原则,因为通过谈判达成全球许可协议可以一揽子解决双方之间的标准必要专利许可授权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当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和实施人经过谈判无法达成许可协议时,一方当事人向中国法院请求裁决标准必要专利中国许可费率,这不符合FRAND原则,因为按照该诉讼逻辑,要解决双方之间的标准必要专利许可使用费纠纷,必须要到各个国家去提起诉讼,即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去解决许可问题,这样明显违反效率原则,并增加成本。比如,英国法官在UP诉华为案中论述到,合理的方式是就全球许可达成一致,而不是逐个国家/地区去寻求许可,这属于“疯狂之举”。【3】因此,持该观点的人认为,当双方无法达成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协议时,一方当事人向中国法院请求裁决标准必要专利中国许可费率,违反FRAND原则,其诉请不应被支持。
本文认为,探讨该问题,应注意区分以下两种不同行为的性质:其一,根据业界惯例,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与实施人通过谈判希望达成标准必要专利全球许可协议,这应属于双方意思自治的范畴,各国法律通常均持赞同肯定的态度;其二,当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与实施人经过谈判无法达成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协议时,能否由一国法院裁定全球许可费率,各国法律及司法实践还存在不同观点。如此一来,当事人通过谈判希望达成标准必要专利全球许可协议,与当事人谈判失败后希望通过诉讼由法院裁决全球许可费率,这二者之间并不能当然划等号。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为了避免争议,华为等中国企业在与NPE进行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谈判且无法达成协议时,有时会选择在中国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裁决NPE在中国区域的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率。对受案的中国法院来说,根据当事人的诉请,审理并确定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中国标准必要专利包的费率,无论从程序法还是实体法来说,无可厚非。应当说,选择在中国法院提起标准必要专利中国许可费率之诉,无论从人们的法律观念还是从法律制度层面来讲,都是符合我国法律规定的。那种认为,当谈判双方无法达成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协议时,一方选择在中国法院提起标准必要专利中国许可费率之诉,违反FRAND原则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关于由一国法院裁决全球许可费率的问题,本文认为,应对此持谨慎态度,应由法院在个案中根据具体案情作出选择判断。如果谈判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共同选定由某一国家的法院裁决全球许可费率,该协议管辖的做法符合国际惯例,并被大多数国家的法律所认可,在这种情况下,由双方共同选定某一个国家的法院并根据当事人的诉请裁决全球许可费率没有问题。比如,TCL与爱立信经过谈判无法达成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协议,双方一致同意由美国加利福尼亚中心地区法院裁决TCL应享有的爱立信所持全球标准必要专利包的许可费率,美国法院据此管辖约定受理了双方之间的纠纷并作出裁决。
另外,在争议双方未作出共同选择的情况下,一国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诉请裁决标准必要专利全球许可费率,不应违反涉外知识产权案件管辖的最密切联系原则。本文认为,对于大多数中国企业来说,其在中国制造无线通信产品,然后销售到世界各地,中国市场是其主要市场,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如果要裁标准必要专利全球许可费率,当事人选择由中国法院进行裁决,符合涉外知识产权案件管辖的最密切联系原则。比如,OPPO广东移动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OPPO)与夏普株式会社(以下简称夏普)经过谈判无法达成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协议,OPPO选择在中国法院请求裁决夏普所持有的3G、4G、WiFi全球标准必要专利包的许可费率。由于OPPO生产、销售的无线通信产品的主要市场在中国,中国法院根据OPPO的诉请受理并裁决全球许可费率,符合涉外知识产权案件管辖的最密切联系原则。【4】
三、当事人提起标准必要专利中国许可费率的条件
当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和实施人经过谈判无法达成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协议时,一方可以请求中国法院裁决标准必要专利中国许可费率。此时在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是,人民法院裁决标准必要专利中国许可费率,应否查明谈判的一方或双方存在违反FRAND规则的行为,从而导致双方谈判陷入僵局。弄清楚该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人民法院裁决标准必要专利中国许可费率,必须以查明谈判的一方或双方存在违反FRAND规则的行为为条件,那么人民法院就需要花费大量庭审时间去查明相关事实。相反,如果人民法院作出裁决不需要以查明该事实作为条件,那么就可以节约大量庭审时间,提高审判效率。
本文认为,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裁决标准必要专利中国许可费率,只需要证明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与实施人经过充分协商,但仍无法达成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协议,满足该条件,当事人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该项诉讼请求。人民法院裁决标准必要专利中国许可费率,无须以查明谈判的一方或双方是否存在违反FRAND规则的行为为条件,理由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专利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第3款规定,“标准必要专利实施许可条件,应当由专利权人、被诉侵权人协商确定。经过充分协商,仍无法达成一致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确定。人民法院在确定上述实施许可条件时,应当根据公平、合理、无歧视的原则,综合考虑专利的创新程度及其在标准中的作用、标准所属的技术领域、标准的性质、标准实施的范围和相关的许可条件等因素。”从该司法解释的规定来看,当事人提起标准必要专利中国许可费率之诉,以“经过充分协商,仍无法达成一致”为条件,无须去查明谈判的一方或双方是否存在违反FRAND规则的行为。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年4月26日颁发的《关于审理标准必要专利纠纷案件的工作指引》(试行)第15条第2款规定:“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与实施者已经充分协商,但仍无法就许可使用费达成一致的,可以依法提起诉讼”。从广东高院制定的上述指导意见来看,当事人提起标准必要专利中国许可费率之诉,以“已经充分协商,但仍无法就许可使用费达成一致”为条件,该规定与上述《专利法司法解释二》的规定相一致,亦无须去查明谈判的一方或双方是否存在违反FRAND规则的行为。
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与实施人经过充分协商仍无法达成许可协议,从而陷入僵局的情形有三种:一是,一方有过错违反了FRAND原则,而另一方没有过错未违反FRAND规则;二是,双方均有过错违反了FRAND原则;三是,双方均没有过错未违反FRAND原则。可见,在谈判双方均没有过错未违反FRAND原则的情形下,许可谈判仍会陷入僵局,此时市场处于失灵的状态,当事人可以请求中国法院裁决标准必要专利中国许可费率。
综上,只要当事人举证证明双方经过充分协商,但仍无法达成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协议,即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裁决标准必要专利中国许可费率,而无须证明或查明谈判一方或双方是否存在违反FRAND规则的行为。
四、标准必要专利中国许可费率的确定方法
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率是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和实施人之间专利许可谈判的核心问题,也是双方发生争议后法院裁决标准必要专利纠纷案的焦点问题。无线通信领域里的标准必要专利与非标准必要专利相比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标准必要专利数量庞大且分属于众多不同的权利主体,实施人多是因实施标准而在先使用标准必要专利,然后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与实施人再通过谈判进行标准必要专利授权许可。同时,双方在进行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谈判时,权利人所持有的标准必要专利以声明的方式呈现,而各标准组织通常只制定标准必要专利实施的FRAND原则,不会对各成员所声明的标准必要专利是否为真正的标准必要专利进行判断。由于判断标准必要专利需要花费庞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故目前国际上没有任何一个机构或者组织,能够对标准组织成员所拥有的标准必要专利是否为真正的标准必要专利进行判断。因此,当事人举证以满足裁决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率所需的证据非常艰难,而法院裁决标准必要专利中国许可费率亦非常困难。
目前司法实践中裁决标准必要专利中国许可费率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可比协议法,二是自上而下法(Top-down)。【5】可比协议法是将能够可比的协议所约定的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率作为参照,来确定具体案件中FRAND许可费率的方法。比如,在深圳中院审理的华为诉交互数字公司(以下简称IDC)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纠纷一案中,法院采纳苹果公司与IDC之间签订的许可协议为可比协议,从而确定了IDC应给予华为的标准必要专利中国许可费率。【6】
Top-down方法是指首先确定所有标准必要专利族可能收取的总专利许可费,然后按照每个标准必要专利权人的专利族组合的价值计算出其占所有标准必要专利族组合的总价值的份额,再将专利许可费分摊给各个许可人,从而得出每个标准必要专利权人的专利许可费率。比如,在南京知识产权法庭审理的华为诉康文森标准必要专利许可使用费纠纷一案中,法院采用Top-down方法计算出康文森许可给华为的2G、3G、4G标准必要专利中国许可费率。【7】
在确定标准必要专利中国许可费率的案件中,究竟应采用可比协议法还是Top-down法,需要根据具体案件中原、被告双方的举证来确定。应当说,根据司法实践的经验,从举证难易的角度看,Top-down方法是大多数案件中可能被采用的方法,而可比协议法相对比较难适用。因为根据业界惯例,当事人对已签署的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协议通常将其作为商业秘密来严格保护,这使得其很难作为证据被获取。退一步讲,即使获取有关专利许可协议,但其能否作为具体案件中可被采用的可比协议,需要复杂的经济学分析,而提供具有说服力的经济学分析报告非常不容易。对于Top-down方法来说,当事人可通过分析评估的方法来确定当事人所持有的标准必要专利族的总数,以及所有标准必要专利族的总数(分母),再举证标准必要专利的累积许可费率,从而可以计算得出具体案件中当事人应授权的标准必要专利中国许可费率。
当然,有的案件当事人举证能力非常强,其既举出适用Top-down方法的证据,也举出适用可比协议方法的证据,此时,其可能采用Top-down方法和可比协议法相互印证的方式来证明其主张的标准必要专利中国许可费率符合FRAND原则,从而获得相对比较优势的诉讼地位,进而取得比较好的诉讼结果。
注释:
1 祝建军著:《标准必要专利全球许可费率司法裁判问题研究》,载《知识产权》2020年第10期。
2 具体案情可参见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1民初232、233、234号民事判决书。
3 仲春著:《标准必要专利全球费率裁判思辨》,载《知识产权》2020年第10期。
4 具体可参见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粤03民初689号OPPO诉夏普管辖权异议民事裁定书。
5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标准必要专利纠纷案件的工作指引(试行)》第18条规定:“确定标准必要专利许可使用费可参照以下方法:(1)参照具有可比性的许可协议;(2)分析涉案标准必要专利的市场价值;(3)参照具有可比性专利池中的许可信息;(4)其他方法”。目前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尚无参照专利池方法裁判标准必要专利中国许可费率的案件。
6 具体案情详见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深中法知民初字第857号民事判决书以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粤高法民三终字第305号民事判决书。
7 具体案情详见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1民初232、233、234号民事判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