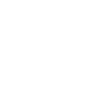我国《专利法》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满地春风而诞生,自1984年颁布以来,已经走过了36年的光阴,并于1992年、2000年、2008年及2020年先后四次进行修订。而放眼世界,专利制度更是早已走过了相当漫长的历史:13世纪,特许专利制度的萌芽便已在亨利三世统治下的英格兰产生;1474年,意大利威尼斯共和国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专利法,并依法颁发了世界上的第一号专利;1624年英国制订的《垄断法规》,则被视为现代专利法律与制度之先声。在这种明显失衡的历史跨度对比下,中国专利法律与制度似乎至今依然显得十分年轻,更无怪乎《专利法》与专利制度诞生之初,许多国人都将其视为纯粹的“西洋制度”,甚至对专利制度能否与我国的政治、经济制度相兼容抱持怀疑态度。
但同样不容忽视的是,就在《专利法》诞生后的这绝不算漫长的36年里,中国在创新创造与知识产权保护方面都取得了堪称奇迹的成就。36年里,《专利法》与专利制度迅速传播至神州大地的每个角落,成为推动经济腾飞与创新爆发最重要的源动力之一;仿佛一颗被吹落山崖的种子,将根系牢牢扎在峭壁之中,最终长成参天大树。《专利法》与专利制度自从来到中国的第一天起,便逐步深深嵌入中国经济社会的内在肌理,与国人走向大世界、创造新生活的美好愿景交织交融,昔日的舶来品,由此染上了浓重的中国底色。而这一切的故事,都浓缩在了《专利法》四次修订背后的起、承、转、合之中。
起:中国《专利法》与专利制度的诞生之路
回望中国《专利法》与专利制度的缘起,北京务实知识产权发展中心主任、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三庭)知识产权庭原副庭长程永顺将时间推至1972年。这一年,随着前一年中国政府正式重返联合国,封闭已久的国门露出了些许松动的迹象;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的访华,更让1972年成为了历史教科书中的一个标志性年份。尼克松在访华时提出,为鼓励和发展中美两国贸易,中国应探索建立专利保护制度。为全面了解“专利”这个在当时对中国人尚属陌生的概念,中央派出考察团,出国考察国外专利制度的实施情况。自此,专利制度逐渐走进了中国人的视野。
打破坚冰之后,中外知识产权交流逐渐升温。1973年,最高人民法院原院长、党组书记,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时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法律部处长任建新受邀以观察员身份,代表中国出席在日内瓦召开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领导机构第四次系列会议。“谈起我们国家的《专利法》和专利制度,我觉得任建新老前辈是最不该忘记的先驱之一。”程永顺说道,“任老与知识产权的结缘,就是从1973年的这次受邀参会开始。虽然当时中国在WIPO只有一个观察员的身份,但正是通过这次参会,任老开始了解到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概念的本质,特别是深刻认识到了知识产权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和国际交往中的重要作用。于是,回国后,任老马上撰写报告提交中央,提出了中国应该建设专利制度的建议。”
由于当时尚处于特殊的历史时期,任建新的建议并没有立即得到落实。幸运的是,中国与WIPO从此建立起了联系。当时负责接待任建新的WIPO副总干事阿帕德·鲍格胥(Arpad Bogsch)博士,后来也升为WIPO总干事,在任长达24年之久。无论在任时还是卸任后,鲍格胥对于推动中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都抱着极大的热情。他不仅为中国第一部《专利法》的出台做出了重要贡献,还曾多次来到中国,并担任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名誉教授等职务。中国知识产权事业的第一颗火种,就此悄然埋下。
时间来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作出改革开放的决定,也就是在这一年,中国专利制度史上的一系列重要事件相继发生:3月,时任中央主要领导同志指示原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研究提出我国专利管理办法,并统一管理专利工作;7月,党中央在批复外交部、对外贸易部、对外经济联络部的一份报告中提出“我国应建立专利制度”。紧接着,1980年1月,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专利局。与此同时,起草《专利法》、设立专利代理机构等一系列工作也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但就在此时,反对的声音相继出现。
“当时,围绕中国要不要建立专利制度的争议甚嚣尘上。无论是中央各部委的一些领导,还是广大的普通企业,都有三个方面的顾虑。”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知识产权与竞争法研究院院长孔祥俊说道,“一是专利制度‘姓社姓资’的问题。顾名思义,‘专利’是指专有的权利和利益,即专利制度赋予一项发明创造的首创者受保护的独享权益,保护的是私权,于是有人认为,专利制度本质上就无法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兼容。二是专利制度与当时主流技术引进模式的矛盾问题。早年间,我们国家在对外技术交流上采用的是‘一家引进,百家享用’的模式,也就是由中央各部委以国家的名义牵头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然后交由各个企业自由仿制。专利制度显然与既有的‘科技大锅饭’模式背道而驰,《专利法》立法之初所面临的现实阻力也就可想而知了。三是本国市场的保护问题。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国家百废待兴,经济几乎走到了崩溃边缘,各项技术全面落后于发达国家,更谈不上有什么创新。这时候一搞专利保护,会不会致使外国人一下子涌进来,把本国企业的市场全占了?也难怪听到《专利法》准备起草的消息,各行各业最初都表现出了惧怕的态度。好在当时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高瞻远瞩、以顺利推进下去。”
回答了“要不要建立专利制度”的问题,“选择什么样的专利制度”的新问题旋即又摆在了决策者面前。建国以来,中国一直实行单一的发明和技术改进奖励制度。当时,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前苏联实行“双轨制”,即只赋予外国人申请专利的权利,而本国发明人只能获得证书和一定的奖励,其发明产权则属于国家。中国是应当追随社会主义老大哥的步伐也建立“双轨制”,还是学习欧美国家经验建设一套属于自己的专利制度?最终,邓小平主席再次拍板:“中国就搞专利制度!”今日回首,我们可以笃定地说,这个英明的决定,为中国近四十年的创新发展与保护省下了无数弯路。
《专利法》自准备起草至最终颁布,前前后后共花费了五年时间。由法律、外贸、科技情报和科技管理界的8位专家,组成了起草小组。起草人之一、当时在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成果局任职的赵元果老人曾回忆道,起草小组在世界各国既有专利法与国内现实情况之间反复权衡,为我国专利制度的性质以及《专利法》的指导思想、主要原则、内容和结构划定了基本框架。这五年间,错综复杂的舆论争议和普遍存在的现实阻力,始终伴随着《专利法》的立法过程,甚至一度使得立法准备工作被迫搁浅。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级高级法官、全国审判业务专家宋健回忆道,1981年,《专利法》草案第11稿上报国务院,曾遭到部分单位的强烈反对,立法工作被迫搁浅;关键时刻,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果断作出“中国需要建立专利制度”“《专利法》以早通过为好”的指示,扭转了僵局。“无可否认,中国重新打开国门、与国际接轨的迫切需求以及来自外部世界的压力,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专利法》与专利制度在中国的诞生。但更不可忽视的是,中国自己也有创新发展的长期内需,这才是中国建立专利制度的最为根本和强大的动因。可以说,在建立专利制度这件事上,国内国际两方面的力量一拍即合。”程永顺说道。
1984年3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正式通过《专利法》立法决议。新中国第一部《专利法》的诞生,不仅在国内引发了强烈反响,更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当时,国际上几乎没有人能想到,中国这样一个刚刚走出长期封闭、市场广大、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夜之间就拥有了自己的专利法律和制度;更出人意料的是,新鲜出炉的中国《专利法》不仅与国际规范相贴合,也保留了诸如职务发明等许多独具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其中的许多条款一直延续到今天,散发出强大的生命力。”程永顺说道。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原副主任张春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时任WIPO总干事鲍格胥的一番话依然记忆犹新:“中文真奇妙,只用六十几个条文就把三个专利(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说清楚了!”鲍格胥的评价,正代表着国际社会对于当时中国《专利法》的主流态度。此后,鲍格胥曾奔走多个国际场合,宣传新生的中国《专利法》。完善的法律设计、极高的历史站位,《专利法》一诞生,便为开启中国知识产权事业的黄金时代奠定了基调。
承:“狼来了”与《专利法》第一、二次修法
1985年4月1日,当时尚未完工的国家专利局办公处门口,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航空航天工业部207所工程师胡国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道,当时,他已在此等候了三天三夜之久,身边还挂着一块写着“第一名航天207所”的硬纸板。到了办公时间,胡国华第一个走进专利局大门,递交了一份名为“可变光学滤波实时假彩色显示装置”的专利申请书——这份由胡国华用三天时间加班加点赶写出来的申请文件,成为了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份专利申请,后来又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号授权专利,编号为“85100001.0”。就在同一天,国家专利局还接到了来自中外申请人的共计3455件专利申请,而这,只是《专利法》正式实施的第一天。
1985年3月19日,中国正式成为《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成员国;1985-1990年,国家专利局收到来自国内外申请人的三种专利申请共计167343件,授权61637件。《专利法》正式实施后的三年内,据不完全统计,25个省、市、自治区及7个开放、计划单列城市新增产值25.6亿元、创利税4.54亿元、创外汇3874万美元。原中国专利局局长黄增益在《专利法》实施三周年之际撰文指出,仅用三年时间,《专利法》便保障我国顺利建立起专利制度,取得了初步成果,这从侧面说明了新生的《专利法》之科学性。然而,随着国际实践的快速变化,新的问题很快也随之而来。
1984年,也就是在中国《专利法》出台的同一年,美国国会颁布了《药品价格竞争与专利期补偿法案》(又称《哈奇-韦克斯曼法案》,Hatch-Waxman Act)。该法案给予含新化学实体的新药五年的数据独占保护期,并依照新药审批过程中耽搁的时间赋予原研药厂商相应的专利保护期补偿,旨在保护原研药厂商与仿制药厂商之间的利益平衡。而彼时的中国《专利法》出于国情考虑,规定对药品、化学物质和食品不授予专利权。《哈奇-韦克斯曼法案》由此成为彼时中美之间知识产权保护冲突的一大缩影。
“当时,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专利制度已经走过了上百年历史,开始重视起药品等精细化的专门保护;而我们刚搞《专利法》,不仅不完全清楚该保护些什么,也害怕落到没有药吃的地步,争论过后,最终在立法中搁置了药品保护的问题,这就导致中国与美国等其他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上分歧频出。1991至1992年,中美之间的第一次贸易摩擦达到了顶峰。药品、软件等问题,都是当时中美之间知识产权保护的主要分歧所在。”程永顺回忆道。
经过激烈的磋商博弈,1992年1月17日,中美两国正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谅解备忘录》,中国政府承诺修改《专利法》,将专利权授予所有化学发明(包括药品和农业化学物质),并将发明专利保护期限延长至20年,同时对专利强制许可做出限制。同年9月4日,《专利法》迎来了颁布8年之后的第一次修订。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原司长尹新天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总结道,第一次修订后的《专利法》最重要的变化,便是取消了对药品、化学物质和食品不授予专利权的限制。此次修法的主要目的虽是为了与中美《保护知识产权谅解备忘录》相适应,但客观上也推动了我国《专利法》与国际规范进一步接轨,大大促进了我国相关产业的发展。
就在第一次修法的又一个8年后,2000年8月2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决定》,标志着《专利法》迎来了第二次修正。此次修改后的《专利法》明确了通过PCT途径提交国际专利申请的法律依据,与国际知识产权条约进一步协调。一年后,2001年11月10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并开始履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定》)。
“《专利法》第二次修法,严格说就是为了‘入世’。”程永顺指出,“要加入WTO和《TRIPs协定》,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上就必须遵守对方的规则要求,相应地,我们的《专利法》也必须符合WTO和《TRIPs协定》框架下的最低标准。《专利法》第一次修法后,在专利保护范围、专利保护期限和强化专利人权利等主要方面早已与《TRIPs协定》一致,但这还不够,于是又有了第二次修法。当时,许多国人都认为,引进专利制度就是‘引狼入室’,给中国平添了许多国际压力。如今回望,不能否认,《专利法》的头两次修订,很大程度上都是在这种‘狼来了’的国际压力下促成的。当然,中国并没有在修法过程中失掉主动权,而当年的两次修法,也完善了中国知识产权立法保护的基础,为中国创新经济的腾飞插上了翅膀。”
转:“东风压倒西风”与《专利法》第三次修法
2008年是中国当代史上一个意义非凡的年份。这一年,汶川地震震惊世界、北京奥运会胜利开幕、“神舟七号”成功发射升空,都是国人铭记至今的大事件。同样在这一年的12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决定》,《专利法》迎来了第三次修正。相比于前述的一系列重要事件,《专利法》第三次修法似乎很难进入大众视野,不过,在程永顺看来,这却是《专利法》发展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一个节点。
“正如我之前所说,中国《专利法》与专利制度的产生,是内外两方面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对外,我们有与国际接轨的需求,也受到来自外部环境的压力和帮助;对内,我们则有自己创新发展的需求,这种需求或许当年看起来还显得微弱,但其中却蕴藏着无限的潜力。”程永顺说道,“前两次修法,主要是在外部压力的推动下进行的;而到了2008年的第三次修法,内部需求因素彻底压倒了外部环境因素,《专利法》开始要解决中国人自己的问题了。”
数据从侧面佐证了程永顺的观点。2008年,国内外三种专利申请共达828328件,其中国内申请为717144件,占比达86.6%,国内申请占比连续五年实现增长,这正是国内科研创新能力高速发展的生动体现。面对这一趋势,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以及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创新体系,让企业成为创新主体,实现高技术与传统产业的全面结合。到了2012年党的十八大上,上述一系列认识被精辟地总结为如今人们耳熟能详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此同时,第三次修订后的《专利法》,将原法第一条关于“促进科学的进步和创新”的表述,修改为“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提高创新能力”至此被单独提出,成为《专利法》立法目的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外,第三次修订后的《专利法》还将专利授权标准由相对新颖性调整为绝对新颖性,并将主要起标识作用的设计排除在外观设计授权客体之外,更加强调解决创新观念问题、提高国家创新能力。《专利法》的中国底色,由此显得愈发浓重。
除了目的与动因的转变,方式与方法的改革也成为《专利法》第三次修法的一大亮点。“当时的国家知识产权局采用了公开立法的方式推进修法,可谓前所未有的创举。”程永顺指出,“所谓‘公开立法’,顾名思义,就是把参与立法的权利开放给广大企业和个人。国家知识产权局首先在社会上广泛、公开地征求企业、权利人、学者、民众等各方面意见,然后根据收集到的意见形成若干专题进行研究,最终根据研究结果推动法律条文的修改。公开、透明、民主的修法方式,有效汇集起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保障了第三次修法的顺利推进。”
“第三次修法之所以能有如此大的进步,我认为,归根结底还是与国力的提升和国家整体战略的创新转向分不开的。当‘东风压倒了西风’,在没有什么外部压力的情况下,我们只需考虑如何通过修法促进我们自己的经济发展与科技创新就可以了。曾经,《专利法》的诞生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如今,第三次修法又创造了一个更新的时代。”程永顺总结道。
合:新时代下的《专利法》第四次修法
2011年11月,《专利法》第四次修法的准备工作悄然启动。此时,距离第三次修订后的《专利法》正式生效,仅仅只有两年时间。相比此前三次修法的八年间隔,《专利法》第四次修法,眼看将比以往时候来得都更早一些——然而,此次修法的复杂程度似乎远远超出了人们既有的认知。
如今回顾此次修法的全过程,有几个时间节点颇为值得注意:2013年1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将《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报国务院审议,国务院法制办遂对送审稿公开征求意见并进行专题调研;2014年上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专利法》执法检查,指出了知识产权案件审判时间长、举证难、赔偿低等问题,为修法提出多方面建议,修法工作从此全面展开;2015年7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又将新版《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再次报请国务院审议;2018年12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专利法修正案(草案)》,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2020年10月1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决定》,标志着此次修法工作终于落下帷幕。
《专利法》第四次修法工作,前前后后历时近9年,完成之时,距离上次修法更是已有12年之久,这既超过了以往三次修法的间隔,也超过了《专利法》从无到有的时间跨度。在此期间,中国已经成长为名副其实的专利大国:2019年,中国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达到140.1万件,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连续9年位居世界第一;截至2020年10月底,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已达到15.2件。就国际影响而言,2019年,中国更是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专利合作条约》(PCT)框架下国际专利申请量最多的国家。三十多年前市场主体和普通民众对专利制度的疑虑与担忧早已烟消云散,代之以政、产、学、研各界机构对专利指标的狂热追逐。与此同时,专利申请重量不重质、高价值专利稀缺、专利侵权频发、权利人举证维权难的问题,开始困扰行政主管和司法审判部门。庞大的市场体量、复杂的利益纠葛堆积的现实问题,以及高质量转型发展的时代要求,无不呼唤着《专利法》各项规定的进一步精细化。
在此背景下,此次《专利法》的修改力度也大大超出了过往三次修法。在制度设计方面,新修后的《专利法》完善职务发明制度、新增专利开放许可制度、加强专利转化服务,同时进一步改进专利授权制度,如完善外观设计保护相关制度、增加新颖性宽限期的适用情形、完善专利权评价报告制度等;在司法保护方面,新法也空前加大了对专利侵权行为的惩罚力度,规定了一到五倍的惩罚性赔偿额,并将法定赔偿额上限由一百万元提高至五百万元,同时完善举证责任分配和专利行政保护措施,新增诚实信用原则等。
程永顺则对《专利法》四修中新增的药品专利权期限补偿制度和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决程序有关条款赞许有加。“药品问题是此次修法最大的亮点,因为它与企业、与老百姓、与中国的未来发展都息息相关。”程永顺说道,“进入新时代,国人的生活和四十年前相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语。衣食无忧之后,大家都渴望过上质量更高的新生活,而这一切都需要有医药保障的健康来打底。但是药品、疫苗的研发成本极高,成功率又较低,审查周期偏偏又很长,如果研发企业不能通过足够长的垄断从药品中获取足够的回报,企业与民众两方的利益都得不到保障。美国的《哈奇-韦克斯曼法案》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而出台,最终成为美国建国200多年来最成功的、全民最支持的法案之一。过去,考虑到相对落后的国情,我们的《专利法》中缺失了对药品足够有效的保护。如今时过境迁,国外在药品保护上有这样成功的经验,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学?小康社会没有群众健康就是空谈,这次《专利法》修法搞好了药品专利权期限补偿制度和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决程序,与中央《“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提出的‘创新法制’的要求正是不谋而合。”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历史,也是一部《专利法》从无到有、从粗放到精细、从外部导向到内需驱动的发展变革史,而这一切,都浓缩到了《专利法》四次修法的起、承、转、合之中。“三十多年的实践早已证明,专利制度对整个中国的创新,乃至对全人类的发展,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或许没有专利制度,人类也会有创新,但创新的规模和质量,必定远远无法与今日相比。目前来看,专利制度依然是推动创新的最佳制度。”程永顺总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