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Economic Reasoning and Judicial Review[1]
作者:斯蒂芬·布雷耶 Stephen Breyer [Ⅰ] 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编者按:本文译者为厦门大学邹至庄经济研究中心博士生黄腾(文章开头至第一个案例结束)和厦门大学知识产权研究院硕士生李恩民(其余部分),厦门大学知识产权研究院龙小宁教授对译文全文进行了校对和润色。
本文分析了在作者曾作为大法官之一的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情境下,经济学在法律中的运用。文章重点关注了作者对其判决持有异议的三个案例。其中,第一个案例是关于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是否应该考虑经济成本;第二个案例涉及对转售价格维持(resale price maintenance)协议应该适用明线规则(bright line rule)还是合理规则(rule of reason);第三个案例则事关版权保护期限是否应该再延长20年。
本文聚焦经济学在法律中,特别是在美国最高法院中的应用。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Ⅱ]曾指出,这些并不是令人荡气回肠的那类事务,他还说“骑士时代已经终结”,“诡辩家和计算器的时代”——也就是律师和经济学家的时代——“来临了”,而“欧洲的荣光永远消失了”。但是,我们也并不必如此悲观。身处这个现代社会的人们追求繁荣;繁荣要求有运转良好的经济;经济又依赖于运行良好的法治(良法善治);而为了产生这样的法律,至少在有些时候,律师和经济学家们必须合作。笔者的观点是:他们之间的合作对于良好有序的民主化的混合经济来说至关重要。
本文旨在阐述法学和经济学之间的合作如何在美国最高法院中发挥作用。笔者将考察一些法律领域中的案件,在这些法律领域里,如果希望法律有效运转,案件的裁判就必须参考经济学家提供的深刻见解,这些领域包括经济规制相关法律、反垄断法和知识产权相关法律。笔者选择了一些案例,在其中作为反对意见的持有者,笔者并不同意多数大法官关于法律是否应该或者如何借鉴经济学中洞察直觉的观点。通过聚焦这三个案例,希望能够说明学科之间的合作仍然面临一些制度性的障碍。笔者鼓励经济学家和法律人共同努力来寻求克服这些困难的方法。
先简单介绍一下美国最高法院。包括笔者在内的九位大法官均是由总统提名和参议院确认,并且终生任职。在任职前,我们都是联邦上诉法院法官,而在担任联邦上诉法院法官之前,我们中有三位是学者,三位是私人部门的执业律师,还有三位是在公共部门任职的律师。
笔者任职的最高法院只裁决联邦法律问题(大部分的美国法律属于州法律,而不是联邦法律)。与(英国)上议院的法律委员会相似,我们对法律拥有最终解释权。但和上议院的法律委员会不同,我们也对联邦宪法负责,也即要对美国宪法做出决定性的解释。我们有自由裁量权来决定是否对案件具有管辖权;主要受理那些下级法院对司法解释存在争议的案件。
简要说一下相关的个人经历:1980年笔者被任命为联邦法官。在此之前是一名法学教授,研究领域为反垄断法和行政法,特别关注经济规制。之所以提到个人背景,是因为可能有人认为,这种背景可以让笔者在与经济相关的法律案件中更容易说服同事接受我的观点。但笔者对这种观点心存怀疑。为解释缘何有此印象,笔者总结出一个包括各种妨碍更好利用经济学洞察的制度因素的名单,现在就来讨论这个单子。
笔者发现了七个制度因素,并认为它们能帮助解释,为什么具有法经济学背景的法官,却可能会发现自己处在持有反对意见的少数派当中。其中四个因素主要涉及最高法院开展工作的方式,它们与经济学推理关系不大。其他三个因素的政策倾向性更强,其可能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在采纳经济学洞察直觉方面,法官可以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
第一,与许多欧洲高等法院不同,我们不会在大法官之间分割决策权。我们并不要求某位大法官专门擅长某方面特定的案件,或者为其他法官准备案件报告以供使用。也不会随着时间推移努力发展为不同领域的专家,而都要是多面手。我们明白,某些成员可能更了解某一特定领域;但我们也认识到,从多面手的角度来看,这种专业知识可能会让他们持有存在偏差的视角。因此,我们给予其他法官专业知识的尊重是有限的。我们每个人都充分参与每项司法裁决。我们相信,被任命为大法官是为了行使自己的判断力。我们每个人都对自己在每个案件中的决定负全部责任。上述这些事实意味着,一位大法官在某一特定领域的专长——虽然不是完全无关——鲜有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第二,时间有限。在最高法院,我们每年审查大约8,500份再审申请。我们会批准大约80份申请,每一份申请都提出了不同下级法院之间做出不同答复的法律问题。案件的难度、上诉状的长短、做出裁决的必要性,都会给工作进展带来压力。这些压力会影响法官的判断,可能已经做出决定,但可能又会改变想法。我们并不固执,但也明白,如果过于频繁地改变决策,我们将无法完成最高法院的工作。
一个技术性案件(例如涉及复杂的经济分析),其中的异议(dissent)在被写成书面草案之前,只有很弱的说服力。而写出这样的草案需要时间。等到少数意见得以传播时,多数人可能已经达成与你相反的结论。而且,由于上述所说的时间压力,已经达成的共识会抗拒变革。
第三,我们尽力将独立撰写的意见——反对意见或并存意见——限制在重要的原则性问题上。我们知道,统一的观点能够为其他法官和律师们提供更清晰的指导,这通常有助于避免对法律的理解产生混淆。当然,没有任何意见是完美的,但即使我们意见并不完全一致,也必须寻求共识。因此,我们可能会加入到一个意见中,虽然对其中的次要陈述(secondary statements)我们并不完全赞同。那么,什么事情会重要到足以引起书面分歧呢?笔者推测,相较于非技术专家型的法官,技术专家型的法官更有可能发现让他撰写书面异议的足够重要的次要陈述。这个事实可以解释笔者为何在一些具有技术性、经济导向类案件中出具了书面异议。
第四,涉及经济的案件,通常也是法律指示法院遵从其他政府决策者意见的案件。例如,此类案件可能出现在政府机构制定了基于经济考虑的公共政策的领域。法院必须决定的,不是该政策是否明智,而是它是否错误到“任意”、“反复无常”或“滥用自由裁量权”的程度。但很难证明一个政府机构的决定或国会的决定是如此荒谬的。因此,法院倾向于不进行自己的经济推理,也不详细审查政府机构的经济推理,而是简单认为政府机构的经济分析是合理的。
上述因素从制度安排上解释了为什么上诉法院有时貌似不愿接受基于经济学推理的分析。脑海中带着这些制度背景的认知,笔者将讨论另外三个与政策相关的因素,这些因素更直接地解释了经济学推理为什么在法律决策中没有发挥更大作用。接下来将更详细地讨论这三个因素:第一个是与法律对可操作性规则(administrable rules)的需要和偏好有关。第二个是在经济学家和律师中都存在的狭隘观念(tunnel vision),阻碍着双方去充分借鉴对方的学科。第三个与法律对新颖性的不信任有关——这一事实意味着,新的方法(例如经济学方法)在被法院引入司法之前,通常需要先在其他制度机构中缓慢地赢得认可。笔者持有异议的三个案件,会有助于解释上述的三个因素。
第一个案件,惠特曼诉美国货运协会案(Whitman v. American Trucking Associations)[2],该案涉及《清洁空气法案》(Clean Air Act)。相关的立法用语指示美国环境保护局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EPA)(以下简称环保局) 设定环境空气标准,而“达到和维持这些标准是保护公众健康所必需的”,并具有“足够的安全边际”[3]。法院认为这种表述不允许环保局(EPA)考虑经济成本问题。大多数法官的推理如下:第一,此处文本没有提到成本;第二,法案中其他相似部分的文本却提到了经济成本;第三,此处没有提及而别处提到,表明国会有意在此处不考虑经济成本;第四,法院在其他类似案件中得出过相似的结论,也即国会不希望环保局(EPA)考虑经济成本,除非对这样的考量有“明确的……文本规定”;第五,此处文本没有这样的“明确规定”。
笔者单独写了一份意见,提出得到类似结论的不同理由[4]。从纯粹的语言学角度来看,笔者认为环保局(EPA)可能发现,一个会产生巨大成本但几乎不能确保增加安全性的标准,并不是一个具有“足够安全边际”的“公共健康所必需”的标准。但笔者仍然认为,该法案的立法过程清楚地表明,国会是有意催促企业创造新的、更便宜、更有效的污染控制技术。国会也认为,政府机构在成本和收益间的权衡通常都太耗时。因此,笔者同意大多数法官的观点,即该法规通常禁止将经济成本考虑在内。而在我们遇到的那个具体案件中,也没有任何理由背离上述的推定。
但是,笔者意见中的观点是说:该法案并没有禁止在不寻常的案件(unusual cases)中考虑成本。在考察立法过程基础上对法案进行解读,其文本也具有足够的灵活性:即为了避免适得其反的结果,是允许环保局(EPA)考虑经济成本的。具备了“公共健康所必需”的标准的世界,并不是一个没有任何风险的世界。最安全的橄榄球护垫和头盔,也不能防止每一次受伤;对于橄榄球受伤而言是可以接受的“安全边际”内的风险程度,在安全饮用水的情景下,却会构成不合理的危险。因此,在一定范围内,环保局(EPA)必须有权决定什么是“足够安全”或什么是“公共健康所必需的”。它必须有权决定相关事项,如“抗污染标准”的实施本身是否会带来比其要去除的污染更大的健康风险。举例来说,在制定臭氧标准时,环保局(EPA)可以将臭氧对健康的好处作为一种抗衡因素进行考虑,例如皮肤癌患者的减少。
如果是这样,环保局(EPA)也必须有相似的权力,以裁决某一被提出的标准是否由于成本异常高和收益异常低,而获得适得其反的结果——至少在不寻常的案件中。原因是:针对某一既定的环境风险,一项意图解决90%环境风险的法规所产生的成本可能是合理的,但旨在解决100% 风险的法规则会产生令人难以承受的高昂成本。而如果全面禁止考虑成本,那么环保局(EPA)可能会感觉它负有法律义务去以公共健康的名义而采用后者这种更严格的规制。但这样做可能会迫使公司转移走原本用于解决其他环境风险的资源。因为解决环境危害的可利用资源并不是无限的,为了解决最后10%的风险,由于(上面谈到的)资源的转移,将导致令公众面临其他无法预料的更严重风险的不良后果。
笔者认为,国会永远不会支持那种因为规制行为的成本过高而导致弊大于利的情况。因此,对于是否考虑成本的问题,《清洁空气法案》的本意不可能是“从不”,而且笔者认为指出这一点很重要。
现在可以看到这个案件中观点的真正分歧。如果大多数法官的意思是“从不考虑成本”,那么它的解读可能会产生适得其反的结果——这不可能是国会想要达到的结果。当然,笔者自己“有时政府机构可能会考虑成本”的观点也可能被提出异议。它会引来下述问题,“那好,什么时候考虑?”这一表面上涉及污染案件中考虑经济成本的必要性和价值的争论,已经变成了法律中“明线规则(bright-line rules)”的必要性和价值的争论。
这一事实说明了法官在使用经济学推理上的一部分困难。经济学推理不会自然欢迎使用“明线规则”。经济学经常关注由于多一点或少一点的(影响)而引起的结果的渐变。但法律,至少在终审法院,通常寻求明确的可操作的区别,而并不关注程度上的差异。这是可以理解的。“明线规则”有时会降低裁判(judging)的交易成本,因为这样的规则更简单且易于操作。此外,“明线规则”可以为广大公众提供更高的清晰度,从而降低合规成本,甚至也可能降低诉讼成本。
《反垄断法》中即揭示了下列紧张关系:经济学对灵活标准的偏好与法律对明线规则的偏好。例如,固定价格的本身违法规则 (per se rule) [Ⅲ]并不包含固定价格不可能具有经济合理性的判断。相反,该规则只说明,固定价格的经济正当理由很少,这种情形极少出现并且很难证明,而明线规则的执行优势相比之下是如此之大;因而,不值得付出努力去制定和执行更复杂、经济上更精密的法律规则。事实上,法院在应用更复杂精密的规则时所面临的困难,可能会导致产生其后果超过复杂规则所能带来好处的错误。
那么,类似的推理能否用来证明《清洁空气法案》实施禁止考虑成本的单独认定规则(per se rule)[Ⅳ]是合理的?笔者并不这么认为,因为笔者相信这样绝对禁止的规则可能会带来严重的、适得其反的伤害。该法案的用语和目的允许更多的开放式解释。结论是:“通常”和“不寻常”等模糊的法律用语必须提供足够的行政指导。
但是,相较于具体结论的价值,笔者更有兴趣指出的是,我本人观点与本案中大多数法官的观点之间的差异可能引发更重要的法律问题:在多常见的情形下采用明线规则是合理的?在什么情形下对法规采用比较开放、比较不绝对的解读是可行的?一项法案的文本,包括其立法背景,能在多大程度上为一个困难的法律诠释问题提供明确的答案?基于国会制定该法规的目的,一位通情达理的国会议员会更倾向哪种选择:禁止行政人员和法官考虑成本的绝对规则所带来的危害,抑或是“通常”这个词[Ⅴ]背后所隐含的模糊标准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法律意见中给出的(这些问题的)答案,包括法律规则的“明线”度、“绝对性”或适用范围等,本身就反映了对相关考虑因素的司法权衡——也即法律成本和收益。
做出这样的判断,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总的来说,笔者相信国会绝少想要一个可能导致适得其反的严重后果的“明线”法律解释。因此,笔者倾向于不赞成绝对的法律界限;相反,生活通常过于复杂,无法适用绝对的规则。此外,更开放、不绝对的解释方法可能被证明更有助于法学对其他学科的知识进行兼容并蓄,特别是那些通过“多一点,少一点”的思维进行推理的学科,比如经济学。
第二个案例是Leegin Creative Leather Products, Inc.v PSKS, Inc.[5],在这个案件中笔者得出了正好相反的结论。笔者认为,出于行政和其他法律方面的考虑,“明线规则”[Ⅵ]是可取的。
这个案件涉及到维持转售价格的问题。自1911年法院裁判Dr. Miles Medical Co. v John D. Park & Sons Co.一案以来,法院对固定转售价格协议均采用“本身违法规则”。这项规则要求法院在不审查特定一项协议是否合理的情况下,假定此类协议总是(或几乎总是)反竞争的,因此根据《谢尔曼法》该协议应被认定为不合法,因为《谢尔曼法》禁止竞争对手之间达成反竞争协议。
而在Leegin案中,最高法院推翻了之前的判例。相反,它认为对转售价格维持协议,法院必须适用“合理规则”,而不是“本身违法规则”。这种“合理规则”允许被告出示证据以证明某个转售价格维持协议是合理的,理由是该协议的经济利益大于反竞争损害。包括笔者在内的四名法官对此提出反对意见,我们认为,“合理规则”的支持者没有提出充分的理由来推翻一项广为接受的现行法律。
本案或许能引起大家的兴趣,因为美国反垄断法融合了经济和行政两方面的考虑,这一具体案件要求我们考虑以下几种因素:
(1)潜在的反竞争影响;
(2)潜在的经济合理性;
(3)以及对于法院是否具备能力来实施本案所形成的法律规则的关切。
对这三类因素的考察指向不同的方向。经济学家在前两项考察中提供了较大的帮助。但笔者的问题是,在与行政有关的第三项考察工作中,他们能否继续提供帮助?
法官们要了解经济学家的想法并不困难。当事人和增援团会在提交给法院的案件摘要(brief)中陈述他们的观点,这些摘要中也会引用相关主题的经济书籍和期刊文章。经济学家们基本同意,转售价格维持协议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反竞争后果。
从经销商角度看:转售价格维持协议与横向价格协议类似,可能减少或消除单一品牌经销商之间的价格竞争或多品牌经销商之间的价格竞争(如果厂商普遍采用这种做法的话)。通过这种做法,厂商可以防止经销商向客户提供多数消费者青睐的那种较低价格;厂商可以防止经销商依据需求变化做出反应,比如说在需求下降时降价;厂商通过鼓励经销商以服务竞争代替价格竞争,而后者可能会导致过多资源涌入该行业的危险;他们还可能会抑制效率更高的经销商的扩张(因为这些经销商更低的价格可能会吸引更多的客户),从而抑制新的、更高效的零售模式的发展等等。
从厂商角度看:在集中化程度高的行业,转售价格维持协议可能强化企业的竞争抑制行为。在这种行业里,企业可能会心照不宣地采取联合行为(tacitly collude),即观察彼此的定价行为,因为每个企业都明白一家企业的降价可能会引发所有企业的价格竞争。在这种情况下,维持转售价格可以使每个厂商更容易(通过观察零售市场)确定竞争对手何时开始降价。在批发价格下降而最低转售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厂商将处于无利可图的境地,因为经销商无法将批发降价的好处让渡给消费者,以刺激消费者需求。在上面两种情况下,转售价格维持协议都可以避免价格竞争的“爆发”,因此,这类协议倾向于维持稳定的生产者价格。
经验证据也表明,如果转售价格维持是合法的,将产生不可忽视的反竞争后果。1975年,国会废除了《米勒-泰丁斯公平贸易法》(Miller-Tydings Fair Trade Act)和《麦奎尔法》(McGuire Act)。这些法律允许(但不要求)各州颁布“公平贸易”法,允许维持最低转售价格。在这些法律被废除时(1975年),维持最低转售价格在36个州是合法的,还有14个州认定其是非法的。实证研究比较了前者和后者的价格水平。司法部称,实证研究表明维持最低转售价格使价格水平提高了19%到27%。
在这两部法律被废除后,最低转售价格维持协议在每个州都成为本身非法的。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FTC)的工作人员在研究了大量的价格调查后写道,这些调查总体上“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转售价格维持)提高了(在转售价格维持制度安排下)出售的产品的价格”。如今,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用一篇著名的反垄断论文的话说——“与相反的情形比较,转售价格维持会导致更高的消费者价格”。
与此同时,经济学家们也认同下面的观点,转售价格维持协议有时可以被证明具有正当性,因为有时候它们可能会带来重要的消费者利益。例如,转售价格维持协议可以促进新的主体进入市场。新加入的、希望打造新品牌的厂商可能说服经销商帮助它这样做——但前提是,厂商向这些经销商承诺,保证他们以后可以收回投资。因为如果不维持转售价格,后期进入市场的经销商基于早期投资的成果,可以通过价格竞争压低价格,使得早期经销商无法收回其投资。通过向最初的经销商保证以后不会发生这种价格竞争,维持转售价格的做法可以鼓励经销商们出售新产品,从而帮助新进入的厂商取得成功。其结果可能是生产者层面的竞争加剧,即品牌间的竞争加剧,从而提高消费者净收益。
此外,在没有维持转售价格的情况下,生产者可能会发现其销售产品的努力,受到了维持转售价格倡导者所说的“搭便车”行为的影响。假设一个厂商总结出如果想要成功,经销商需要提供特定的服务,比如产品展示、优质商店、创造特定产品形象的广告等等。如果不维持转售价格,一些经销商可能会搭上其他经销商在提供这些服务时所做投资的“便车”。这样的经销商可以节省资金,因其不用为这些服务付费,因此他们可以降低自己的价格,增加自己的销售额。在这种情况下,经销商可能不愿意投资以提供必要的服务。
最后,经济学家们也认为,如果是厂商而不是经销商团体制定转售价格维持协议,那么还存在一个特别的原因让人相信该协议能产生益处。这是因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厂商本应鼓励经销商之间的价格竞争。通过这样的办法,他们通常能销售更多的产品而使得利润增加。即便厂商拥有足够的市场力量来赚取超额利润时,情况也是如此。也就是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通过向其经销商提供竞争市场对应的批发价格(甚至可以是比它稍高一点的价格),并鼓励经销商们之间进行价格竞争,厂商即可以籍此获利。因此,如果维持转售价格的推动力量来自厂商,他们做这种选择就必须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并且在缺乏集中的生产者市场的情况下(生产者市场集中的情形下这种特殊原因可能包括稳定批发价格的愿望),这一特殊原因可能很好地反映了刚才描述的特殊情况:新进入主体、“搭便车”或这些情况的其他形式。
但是一个问题出现了。这些经济学上的答案虽然有用,但它们本身并不能回答我们的法律问题,也即是否要推翻一百多年来一系列判例所确立的“本身违法规则”,而代之以“合理规则”。这是因为,法律不同于经济学,它是一种管理体系,其效力取决于规则和判例的内容,而且只是法官和陪审团在法庭上以及律师为其当事人提供咨询时所应用的那些规则和判例的内容。这些情况意味着,法院有时应该对商业行为适用"本身违法规则",即使这些商业行为有时会产生经济利益。而作为法官,笔者必须知道转售价格维持是否属于这种情况。
然而,在这些关键问题上,许多(并非所有)经济学家都保持沉默。我们现有的经济分析和实证研究表明,转售价格维持会造成损害,特别是当经销商是推动力量时。其他的一些分析(尽管几乎没有实证证据)表明,转售价格维持有时也可以产生效益。但是,这些好处在实践中可能出现的频率有多高?法院在个别案件中识别他们的存在有多困难?笔者在这些问题中找不到经济学上的共识。
所达成的共识是“搭便车”现象的确发生了。但不受任何法律措施限制的“搭便车”现象在经济领域中经常发生。许多到加利福尼亚的游客在太平洋海岸公路上免费搭车,我们都可以免费地从创意中受益(比如创建第一家超市的主意)。经销商经常会“搭便车”,利用其他人在建立品牌和声誉方面所做的投资。但是,“搭便车”问题严重到会阻止经销商投资的情形发生概率有多高呢?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出一个经销商拒绝提供重要的售前服务,比如详细解释一个产品是如何工作的(或者没有提供一个合适的氛围来销售昂贵的香水或鳄鱼皮钱包),以免顾客使用“免费”服务(或享受高价零售商提供特定品牌的钱包或手袋的供货所带来的心理益处)却从另一经销商处低价购入。但这样的经销商真的很多吗?毕竟,我们确实生活在这样一个经济体中,尽管Dr. Miles一案确立了“本身违法规则”,但企业仍然向消费者销售复杂的技术设备(还有昂贵的香水和鳄鱼皮钱包)。
法院对收益可能大于潜在危害的情形进行识别的难易程度又如何呢?如果经销商而非生产厂商是“推动力量”,那么该协议就不太可能合理。但假设几个大型多品牌零售商都销售维持转售价格的产品,进一步假设,小生产厂商制定零售价格是因为他们担心,大零售商会青睐(比如,通过分配更好的货架空间)其他实行转售价格维持的厂商的产品。那么是谁“发起”了这种做法呢?是希望避免竞争的零售商,还是寻找最佳方法来应对所处环境的生产厂商呢?
这些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从“明线规则”转向“合理规则”本身是有成本的。这种转变打乱了那些依赖旧规则群体的既定期望,例如参与打折的零售公司的投资者、他们的客户、商场运营商或为他们提供财务支持的计算机服务公司。随着法院对“合理规则”进行更细致的轮廓描绘,由此产生的法律混淆会产生成本。法院或陪审团不当地应用更复杂的规则因而导致错误,也会产生成本。事实上,如果没有明线规则,由执法人员提起刑事诉讼往往是不公正,因而也是不切实际的。由于执法资源有限,这可能会诱使一些厂商或经销商签订总体而言是反竞争性的协议,即使此类协议在实际被提起诉讼时并不能通过司法程序的检验。
在这类管理问题没有从经济学家那里得到太多帮助的情况下,最高法院的法官们最终以五比四的结果赞成将相关的法律规则从“本身违法规则”改为“合理规则”。异议者认为,管理方面的担忧让案件决策成为比分接近的对局。他们也询问道,30年前国会废除允许维持转售价格的联邦法令并有效实施“本身违法规则”以来发生了什么变化。他们指出,甚至从更早之前,英国学者巴兹尔·亚梅爵士(Sir Basil Yamey)即在他关于维持转售价格的书中列出了相关论点,至今这些论点并没有什么变化。我们得到的结论是基于法律上的原因,这与法律不愿推翻公众可能依赖的早期判例法有关。由于没有新的信息为变革提供新的理由,我们认为这个领域的法律不应该改变。
笔者认为两种立场都有道理。但问题是,参与此案的众多经济专家难道不能给予我们更多的帮助吗?那些大多赞成“合理规则”的经济学家们,难道不能针对实际执行管理方面的关注,为我们提供更多的信息和分析吗?这些被关注的问题,和经济学一样,要为这一领域的法律提供指引。
而这种信息应该是存在的。例如,与明确禁止转售价格维持的欧盟不同,英国采纳某种形式上的“合理规则”:尽管1998年英国竞争法普遍禁止纵向定价协议,但公司仍可以向公平交易办公室(OFT)申请在以下情境下豁免实施这种全面的禁止:也即当维持转售价格不会阻碍经济竞争,并且会改善生产或流通过程或者会促进技术进步或经济增长。OFT是否发现了许多合理的转售价格维持实例,还是发现只有少数是如此?没有人告知我们(答案)。无论如何,难道不能设计一份调查问卷或研究来揭示,在各种消费品行业中“搭便车”行为造成了多大程度的问题吗?
因此,笔者提出以下问题:为什么没有人去研究数量?法院自身能否更好地利用经济学专家?法院能直接请经济学家去研究相关的实施管理问题吗?最高法院想这样做并不容易,因为最高法院主要是通过当事人律师撰写的法律陈述中所包含论点的形式收取专家意见。但下级法院可以聘请他们自己的专家——他们可以专注于回答法院或当事人寻求答案的问题。
笔者注意到,英国法院最近通过了鼓励法院任命中立专家的规定[6]。根据修订后的英国民事诉讼规则,初审法院可以在当事人双方希望对同一问题提出专家证据时,由法院来指定一名专家。大法官[Ⅶ]办公室的评估报告对单一、共用(single joint)专家的更多使用大加赞扬[7],因为它创造了一种更少对抗性的文化,节省了时间和成本[8]。英国法院的尝试是基于一种在大陆法系国家已经相当普遍的做法,在那些国家,法官将从由科学或技术机构提供或由法院自己保留的名单中选择一位专家。例如,在法国,法院会保留了一份“地区”和“国家”的专家名单,这些专家都符合特定的标准。法院任命专家(通常但不完全来自这些名单)并确定要调查的问题。任务完成后,专家需要向法院提交书面报告[9]。
笔者饶有兴致地阅读了法国的一起最近案例,即La Ligue Contre Le Racisme Et L'Antisemitsme v. Yahoo!, Inc.[10],在这起案件中,法国法院禁止雅虎向法国互联网用户提供访问出售纳粹纪念品及其他亲纳粹网站的服务。本案的关键问题涉及到雅虎将法国用户的搜索请求与其他国家用户的搜索请求区分开的实际能力。相应地,法官委托专家小组提交一份报告,同时允许雅虎批评或反对该报告的部分内容。达到的效果是快速和一致的——不是指裁判的结果——而是指支撑结果的许多技术事实。
话到这里,似乎有些偏离了文章主题。在讨论转售价格维持案时,笔者本意是想说明美国法院是如何依赖经济专业知识,同时指出专家可以进一步帮助法院关注那些与最终法律结论相关的法律或实施因素。在此留给读者一个问题:法院如何能够鼓励那些专家去这样做?
第三个案例,Eldred v. Ashcroft[11],该案涉及一部将未来版权和现有版权的期限均延长20年的法令。对于一些作品,保护期将从其作者死后50年延长到70年,对于其他作品的保护期限从75年延长到95年。问题在于,宪法中关于版权的条款是否授予了国会颁布这一法规的权力。宪法中的相关条款授予国会“通过确保作者在有限的时间内......对他们各自作品的专有权”“促进科学(即学术和知识)进步”[12]的权力。最高法院认为,这种表述涵盖了延期。
笔者对此持异议(dissent),因为我认为将保护期限延长20年超出了宪法相关条款所涵摄的范围[13]。在笔者看来,延长保护期限相当于在做这样一种不合理的努力——旨在创造一种并非有限的、反而实际上是永久的版权保护条款。以笔者对宪法相关条款的了解,该条款要求的是版权法规应当服务于某些公共而非私人目的,即通过为作者创作作品提供激励,以及在“有限的”时间后取消对作品传播的相关限制,来达到“促进学术和知识进步”的目的。
延期二十年的做法可以实现私人目的,它将从现有作品的消费者(例如读者或电影观众)那里获得数十亿美元的收入,转移给这些作品已逝制作人的继承人(或关联公司)。但从公众的角度看,这种做法会带来很大的伤害:这会给作品传播带来不必要的限制,而那些作品的保护期限越短,就会越快进入公共领域。例如,这种延期将要求那些希望使用具有百年历史且通常没有商业价值的作品的人去找到那些(通常难以找到的)版权的目前持有人,并从他们手中获得许可。
想一下那些老师们,他们希望学生们看到大萧条时期的照片专辑、阅读那些真正生活在奴隶制下的人被记录下的话语,或者将加里库珀对约克中士的英勇演绎与凡尔登战场上的实景拍摄进行对比。想想历史学家、作家、艺术家、数据库操作员、电影保护主义者、各类研究人员,他们希望让过去触手可及以供自己或他人使用。要求他们获得版权持有人许可的期间——从作品完成后的第75年开始——再延长20年,往往会严重阻碍他们的工作。
笔者找不到对延长保护期的任何支持理由可以抵消上述这种危害。没有人能够合理地得出结论,来说明版权保护的传统理由(提供创作激励)可以用于支持这一保护期的延长。过去的作品,例如米老鼠电影,因为其已经存在所以本身不需要激励。而对于未来新的创作活动,任何额外增加的激励都是微不足道的。
要理解为什么是这样,需要参考相关利益团体提交给法院的无可争议的数据;也需要参考其他团体(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提供的经济分析。他们明确指出,没有潜在的作者有理由相信他或她会有超出微乎其微的概率,能写出一部流传足够久(在未来75年后再加上20年)的经典作品,因而延迟保护期对他们的创作无关紧要。事实上,在所有受版权保护的作品中,只有不到2%的作品在75年后仍具有商业价值。并且由于相关版税要到75年或更长时间后才能到账,届时收到它们的将不是作者,而是遥远的继承人或继承公司的股东,因此增加的那些货币激励效果也将大减。以1%的概率从未来第75年开始在20年内每年赚取100美元,这样的收益其现值不及今天的7美分。
有多少潜在的莎士比亚、沃顿或海明威会被这样一笔款项所感动?无论如何,延期20年所带来的现值增加与永久版权带来的现值增加相比没有显著差异。事实上,再加20年延期的版权期限产生的价值将超过永久版权价值的98%。
笔者也没能找到其他与版权有关的理由可以支持延长期限。它没有帮助提高显著的国际统一性,也没有起到其他与版权相关的重大国际商业影响,但它确实使几家出版商、股东和各种娱乐公司受益,包括Walt Disney 和AOL Time Warner(目前是“祝你生日快乐”旋律的版权持有人,该曲于1893年首次出版,并在1935年诉讼后获得版权)。然而,这种私人商业利益,在笔者看来并不是版权条款要保护的对象。因此,笔者的观点是,版权保护期限延长是违宪的。
基于本文的目的,笔者不想强调关于版权结论的实质内容,而想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下面这一事实上,也即笔者的七位同事不同意我的结论以及相关的实证和逻辑说理。暂时抛开这一分歧意味着笔者可能在案件分析上犯了错误的这种可能性,并且如笔者所知,同事们无论从任何角度看都并非愚钝,那笔者不禁发问,为什么自己的论点会没有说服力呢?这个问题可能存在一个有趣的答案。
这样说并不是指存在什么技术性、专业性和复杂性的问题,也不是指需要时间来撰写异议,更不是指我们法院在这一领域必须高度服从国会判断这一法律事实。而指的是另一个笔者认为更重要的因素,这个因素包括我所接受的方法的新颖性,这种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种经济分析型的成本和收益权衡。这种方法并不完全新颖,它在文献和先前的判例法中得到支持。但是,由于它对经济和商业因素的严重依赖,它与过去大多数的版权观点在风格上(如果不是实质内容上的话)完全不同。
法律是一种保守的制度,法院必须保护那些依赖先前法律和先前方法的人。因此,法院通常会在是否对重要法律体系采用新方法时犹豫不决,而且这种迟疑有其充分的理由——至少要等到相关公众,通过其他机构的行为,发现新方法是可接受的。这里指的相关团体和其他机构包括国会、版权协会、出版商、作者、学校、图书馆、研究机构,等等。接受笔者的异议观点(dissent)中所采用的方法的人数还没有达到临界规模——至少目前还没有。
笔者的本意并不是说,法院在适用或制定版权法或任何其他法律时,必须遵循公众意见。而我想指出的是,美国法律的形成是一个高度民主的过程。相较于由高等法院或立法机构颁布,新法律更多是从下面“冒出来的”。通常来说,立法过程类似于许多利益集团之间的对话,包括专家、行家里手、商业企业、工会、各种利益集团和普通公民。这种对话发生在期刊、研讨会、报纸、听证会和法庭诉讼中。一个机构的决定会被另一个机构视为论据。它也可能体现在行政法规、法律甚至宪法解释中,但这些都不是永久性的,所有这些都会顺势而变或逐渐演化。
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对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阐述更好地解释了笔者的想法:
“对学问的追求”,他说,“不是竞争对手之间争夺最佳位置的竞赛,甚至不是辩论或研讨会;这是一个对话......每一项研究似乎都是一个声音,其语调既不暴虐也不尖刻,而是谦逊且乐于交谈......它的融入不是强加于人,而是源于说话时声音的质量,它的价值在于给参与者的头脑中留下的遗迹。”[14]
同样,法律方法和法律分析的发展也是一个协作和演化的过程。法律不断在更新,借鉴一个哲学隐喻:我们在一块板一块板地翻修一艘漂浮在海面上的船[Ⅷ]。
因此,(案件裁决中的)异议(dissent)将继续在进行中的政策辩论里发挥作用。即使它不是法律,但其他人可能会发现它的论点或方法有说服力;他们可能会在不同的场合中修改或采用它们;而且如果得到足够广泛的支持,也许连司法分析方法也会因此而改变。如此看来,评判异议(dissent)的标准在于其说服力,而它并不会因为多数法官持相反的意见就无可挽回地失去了说服力。考虑到这一更宏大的进程,笔者心存希望,援引经济学推理的孤独异议在未来不再孤独。
本文用了三个案件的异议(dissent)来说明法律的三个特点,这些特点与法律中对经济政策的应用有关。第一个特点是,法律需要用一种——笔者称之为“开放文本的方法”(open-textured approach)——来解释,与扩大严格法律标准的适用范围的做法相比,这种方法认为考虑基础性的人性目的是更有价值的。“明线规则”虽然有时有用,但并不总是首选的方案,特别是当适用该规则的结果被证明与法规的立法目的相悖的时候。
第二个特点涉及到,使用能将法官感兴趣的基本法律问题——特别是对于法律规则可执行性问题——涵盖其中的形式,来提供经济学信息和见解的必要性。笔者意图用它来说明,专家们需要了解可执行性考虑,例如(明线)规则的必要性,在法律中所起的作用。
第三个特点所涉及的是,鉴于法律对使用新方法的迟疑,需要司法系统以外的机构进行方法辩论和采纳,这样可以让知识产权司法裁判中融合入经济分析的方法。
总的来说,笔者希望通过本文已经鼓励了那些对经济和法律感兴趣的人,不要将法律决定视为既定的。他们必须了解制度因素的重要性,包括对于法官和律师而言具有可施行性的规则的必要性。但他们不能假设只有法官或律师才是实施问题的专家。法律规则的形式,以及它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成为“明线规则”,本身就值得研究。那些在智力上可以舒适运用均衡概念的人,那些欣赏“多一点、少一点”一类分析方法的人,也可以在这些方面有所贡献。
显然,笔者赞成那些有经济学或规制政策制定专业背景的人士参与司法程序。你们越是了解司法决策并愿意接受有益批评,就越好。无论是作为个别案件的专家,还是更广泛地作为知情的法庭观察者和批评者,你们都可以让律师和法官更了解经济分析工具,并鼓励他们使用这些工具。
这种参与符合笔者自己对法律程序的看法——法律程序太重要了,它不能简单地只留给法律专家、律师,甚至是法官。
注释:
1.本文是2007年9月11日在约克对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发表的一次演讲,这次演讲的部分内容是基于2003年12月在AEI-布鲁金斯监管研究联合中心会议上发表的同名演讲,该演讲内容可在美国企业研究所网站上在线获取。感谢英国科学促进会(经济部)、约克大学(经济系)和英国国际法与比较法研究所对本次活动的支持。
2.531 U.S. 457(2001).
3.42 .S.C. § 7409(b)(1).
4.531 U.S. at 490-96 (Breyer, J., concurring).
5.551 U.S._, 127 S. Ct. 2705 (2007) ,Leegin Creative Leather Products, Inc., v PSKS, Inc.
6.See Lord Woolf, Final Report: Access to Justice, Ch.13 (July 26, 1996).
7.UK Dept for Constitutional Affairs, Civil Procedure Rules 35.7, 35.8 (2003).
8.See The Lord Chancellor's Dept, Civil Justice Reform Evaluation, Emerging Findings: An Early Evaluation of
the Civil Justice Reforms (March 2001); The Lord Chancellor's Dept, Civil Justice Reform Evaluation, Further
Findings: A Continuing Evaluation of the Civil Justice Reforms (August 2002).
9.See, e.g., M. Neil Browne et al, The Perspectival Nature of Expert Testimony in the United States, England, Korea, and France, 18 Conn. J. Int'l L. 55, 96 - 100 (2002).
10.High Court of Paris, May 22, 2000, Interim Court Order No. 00105308 (cited in Yahoo!, Inc. v. La Ligue Contre Le Racisme Et LAntisemitsme, 169 F. Supp.2d 1181 (N. D. Cal.2001).
11.123 S. Ct. 769 (2003).
12.US Constitution, Art. I, § 8, cl. 8.
13.123 S. Ct. at 801 - 814 (Breyer, J., dissenting).
14.Michael Oakeshott, The Voice of Liberal Learning, pp. 109-11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译者注:
Ⅰ 译者注:斯蒂芬·杰拉尔德·布雷耶(Stephen Gerald Breyer,1938年8月15日-),美国律师、法学家和法律学者,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他于1994年5月17日由比尔·克林顿总统提名,自1994年8月3日起任职。他是最高法院的自由派大法官之一。布雷耶曾经担任哈佛法学院教授。(资料来源:维基百科)
Ⅱ 译者注: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9年1月12日-1797年7月9日),爱尔兰裔的英国的政治家、作家、演说家、政治理论家和哲学家,他曾在英国下议院担任了数年辉格党的议员。他最为后人所知的事迹包括他反对英王乔治三世和英国政府、支持美国殖民地以及后来的美国革命的立场,以及他后来对于法国大革命的批判。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使他成为辉格党里的保守主义主要人物(他还以“老辉格”自称),反制党内提倡革命的“新辉格”。伯克也出版了许多与美学有关的著作,并且创立了一份名为Annual Register的政治期刊。他经常被视为是英美保守主义的奠基者。(资料来源:维基百科)
Ⅲ 此处的原文为per se rule。
Ⅳ 此处的原文亦为per se rule。
Ⅴ 译者注:此处原文中的work似为word之误,译文中按照word来翻译。
Ⅵ 译者注:明线规则(bright-line rule),即各国法院中均常使用的明确界定的规则,与之相对的概念是法官使用案件中所涉及的多方面因素以达成判决的所谓平衡测试。
Ⅶ 译者注:Lord Chancellor,英国上议院的大法官,类似于其他国家最高法院院长。
Ⅷ 译者注:即特修斯之船(又译为忒修斯之船),亦称为忒修斯悖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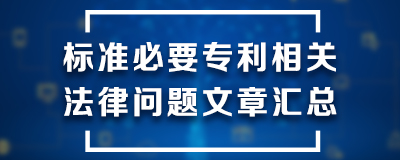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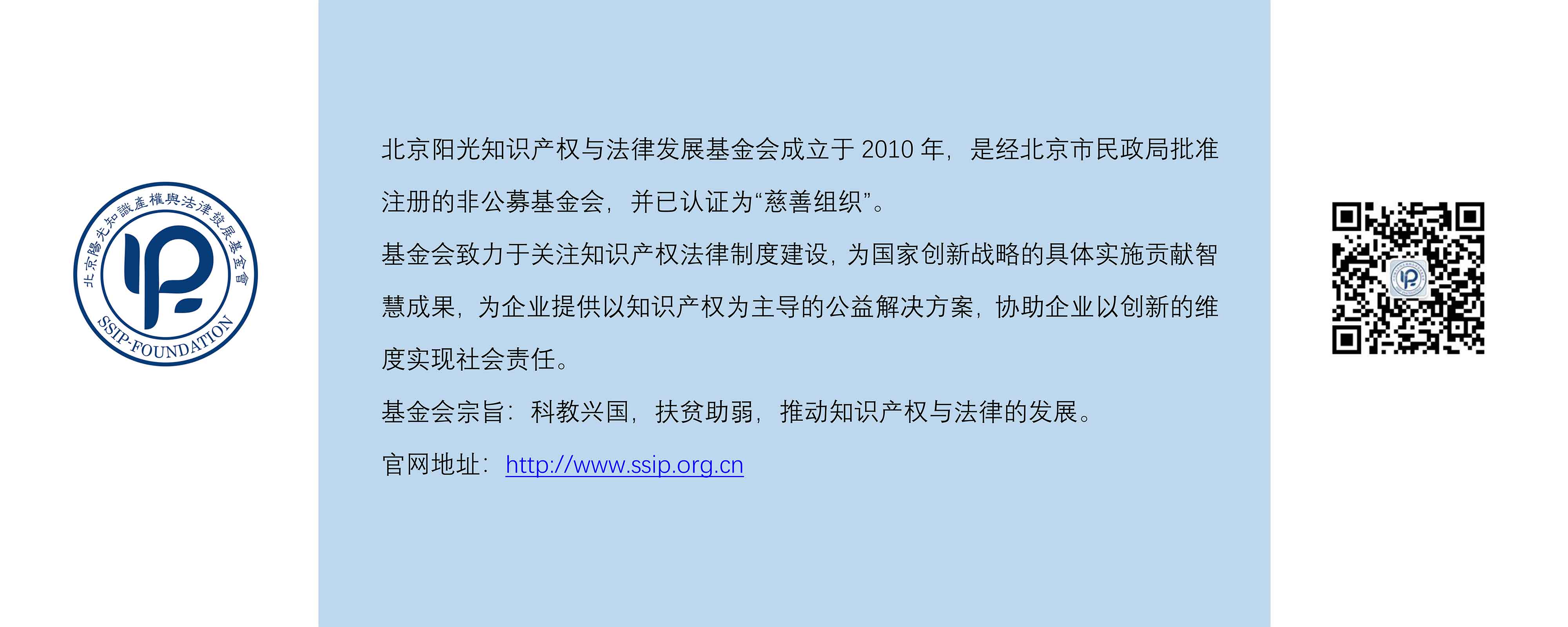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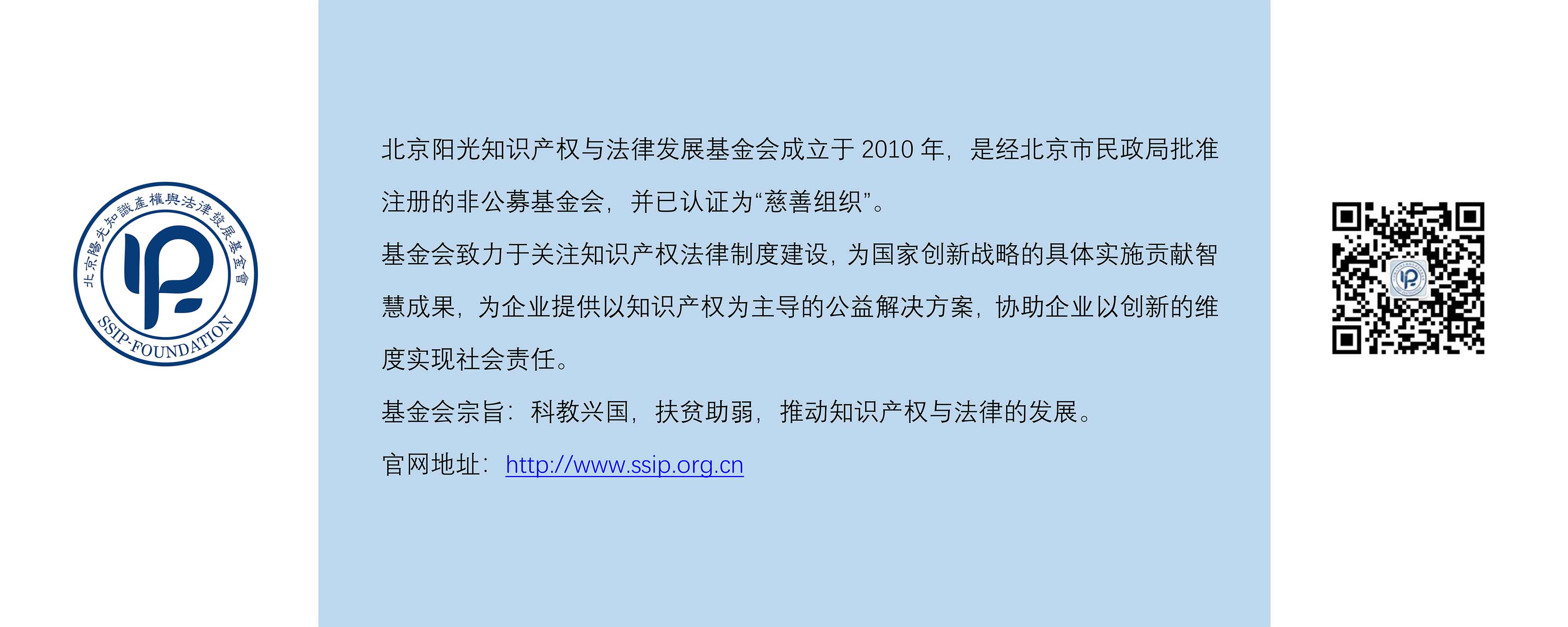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9464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946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