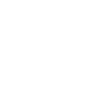文 | 徐婷姿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法官
3月20日,知产财经全媒体在天津召开了“新著作权法下直播、转播的法律适用”研讨会,特邀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法官徐婷姿在本次会议中就“体育赛事节目的法律保护路径”主题发表了演讲,知产财经对其演讲内容进行了整理,以飨读者。
一、产业现状及发展趋势
体育赛事一般是由赛事的主办方,如单项体育协会,通过自己的章程宣扬自己对体育赛事的相关权利,此外他们在向下层层授权协议中,也会明确己方权利主体的地位。但在合同的表述上,用的不是广播权、广播组织权、信息网络传播权这样的法律概念,而是用具体播放设备、播放平台限制权利范围,比如全媒体、新媒体、传统电视台渠道、卫视独家版权、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DVB、OTT等等。如何把上述表述和法律概念适配起来,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其次是可能出现的侵权方式。目前存在的侵权方式有网络点播、直播体育赛事节目,IPTV直播、点播、回看等,网播组织和广播电视台两类主体都可能会成为被告。
2018年底,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体育竞赛表演产业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其中规定“(十六)打造发展平台。加快推动体育赛事相关权利市场化运营,推进体育赛事制播分离,体育赛事播放收益由赛事主办方或组委会与转播机构分享。大力支持体育新媒体平台发展......赛事相关权利归各级单项体育协会以及其他各类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等合法办赛的赛事主办方所有。”该文件对体育产业的发展持鼓励态度,倡导以体育赛事为原点的多产业融合发展,大力支持体育新媒体平台的发展。在此基础上,讲到了赛事的相关权利为赛事主办方所拥有。
像匈牙利、法国等国家,他们有专门法律将体育赛事相关权利归属于赛事组织者,因为体育赛事涉及到的权益很大,商业投入和相应的商业风险也很大,保护赛事主办方的权利符合发展趋势。
二、体育赛事节目法律保护路径选择
在了解了基本情况的基础上,我们要对法律保护的路径进行选择,第一道选择题是,通过著作权法路径保护还是通过反法的路径保护。笔者认为,体育赛事节目在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中,在可能的情况下,应选择著作权法保护路径而非反法保护路径。因为著作权法系权利保护法,权利内容和保护范围均明确,系排他性的对世权。而反法系行为规制法,其保护范围内容需个案认定,具有不确定性,这种消极的权益保护无法满足体育赛事节目许可市场以权利为前提的授权机制的需求,不能为体育赛事节目的许可、转让等流转提供充分必要的法律保障。因此,从体育赛事发展的角度来说,通过这种积极的行为来保护,肯定优先于这种消极的权益保护,所以在第一道选择题中,在符合著作权法保护条件的前提下,我们优先选择著作权法。
第二道选择题是,在著作权法的范围内,到底是以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这种狭义的著作权来保护,还是以录像制作者权这种邻接权来进行保护。该选择的实质是体育赛事节目是否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在这一点上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构成作品,逻辑起点就是作品的认定是以独创性的有无而非高低来判断,也就是说只要具有独创性,那么它就是作品。近期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新浪与乐视“中超赛事节目”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案、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理的苏宁体育诉电信“中超赛事节目”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案,还有浦东法院审理的央视国际与聚力公司“欧洲足球锦标赛”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案,无一例外都认为涉案赛事构成作品且构成类电作品。
还有另一种观点认为体育赛事节目是录像制品,因为在这种认知里,著作权法要求的独创性是指独创性的高低而非有无,必须是具备一定程度的独创性,才能纳入作品的保护范围。
我们可以用一种逆向思维的方法来考虑这个问题,也即怎样保护能够更为有效。从这个角度进行考量,笔者认为录像制作者权并不能很好地实现法律保护的周延性。
不选择录像制作者权有五方面的理由:一是无法为赛事节目传播提供周延的法律保护,邻接权是一个封闭性的权利体系,只有5项权能,与拥有十几项权能的著作权不可同日而语;二是无法为体育赛事产业发展留足空间,如权利人利用体育赛事节目制作游戏、MV、开发广告等保护的问题,著作权权利中的“其他”就具有延展性;三是录像制作者权下的广播组织权无法为节目传播提供周延的法律保护;四是录像制作者权的权利主体不易与赛事主办方挂钩;五是录像制作者权会造成授权链条的复杂化。
三、新著作权法背景下的司法实践
在著作权保护路径下,法官的裁判思路是什么?正常情况下,我们首先是要明确权利的主体和身份,比如说原告起诉时,要明确他是以著作权人的身份起诉,还是以邻接权人(广播组织权人)的身份起诉?他是否有这样一个权利,这是首要的。第二点要对被告的行为是否落入原告主张的权利范围进行评判,如果落入了,最后再考虑赔偿责任问题。
在具体的裁判过程中有几个可以探讨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广播权与广播组织权的关系。广播权或者信息网络传播权是狭义的著作权,广播组织权是一种邻接权,笔者认为两者的关系是一种依附关系,邻接权依附于狭义的著作权之上,也就是说广播组织必须取得著作权人的许可进行作品的播放后,这样的播放才能使广播组织获得一个合法基础上的广播组织权。在实践中有些广播组织可能经著作权人的授权,获得了某些平台上的独家播放权,这些播放权可能构成广播权或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一部分,这时候如果有其他人在同一个平台上使用该作品,他就可以以著作权人的身份来起诉并获得保护。但是其他人如在不同平台上使用节目或者节目信号,广播组织只能求助于广播组织权这样一个邻接权来起诉。
实践中,有些赛事主办方会委托电视台制作赛事的节目信号,电视台在制作过程中除了提供相应的画面以外,还会加入一些解说、字幕,但这些添附行为对其权利范围不存在影响,赛事节目本质仍是类电作品(著作权法2020修正案中的视听作品),其权利范围依然取决于合同的约定,权利性质不会因投入而变化。
第二个问题是,广播组织权不影响条款的适用。这个“不影响条款”也是著作权法修改后新出现的条款,它的适用主要涉及两点:第一点是能不能禁用,因为要求广播组织权的行使不能影响到其他著作权人的权利,如果有第三方主体在著作权人授权的范围内予以使用,那么他的这种使用就不能被广播组织所禁用,否则将影响著作权人授权权利的行使。第二点是能不能赔偿。关于广播组织权可不可以获赔,也存在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广播组织权是法律上认可的一个独立的权利,它和著作权人的权利是并行不悖的,当一个行为同时侵犯到著作权人的权利以及广播组织者的广播组织权时,两者都可以起诉,侵权责任有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等。广播组织的求偿权不应受影响,但求偿范围可能会受到影响和制约。赔偿范围可以考虑广播组织的再许可权收费标准、添附成本和播放成本等。
第三个问题是多重授权的认定。实践中授权链条较为复杂,往往不是赛事主办者直达传播者的,中间还有赛事运营机构等主体,链条越长,出现重复授权的可能性越大。《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侵害著作权案件审理指南》就是以先后的时间顺序来确定授权有效性,即在后被授权的一方可能侵犯在先被授权一方的合法权益,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这个规则用于体育赛事节目中会有一个特殊性,主办方跟电视台、平台授权的过程中,往往赛事还没有举办,节目还没有制作,著作权、广播组织权等权利还没有载体可以依附,此时怎么认定先后顺序,是以作品生成时刻起两个合同同时生效,还是有一个先后的关系?笔者认为该意思表示还是存在先后顺序的,从作品创作完成的这一刻起,意思表示溯及当初立约之时,仍可适用这样一个先后规则。
随着今年6月份新著作权法的施行,互联网时代体育赛事节目著作权法保护路径在更为清晰的同时,也会出现一些新的争议。如何为实现体育赛事多产业融合发展的目标提供更为有力的司法保障,需要我们在实践中继续思考、探索,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