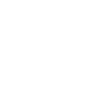作者:龙小宁 厦门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摘要:近年来,商标反向混淆案件在我国争议频发。在笔者看来,引发争议的直接原因在于一些案件中确定的损害赔偿金额畸高,而根源则在于司法实践中对反向混淆所造成损失的性质认定不妥,导致了简单套用正向混淆案件的分析逻辑,并基于被告利润来计算原告的经济损失。基于经济学理论框架,本文进行了如下分析:(1)澄清商誉与商标价值之间的关系,即企业商誉在本质上有赖于企业的长期经营,最终归功于企业在研发创新、生产设计、质量控制、售后服务、人员培训及社区贡献等方面的持续投入和经营成效;而商标的作用则在于通过将企业(或产品)的竞争优势固定于某一商业标识,助力企业(或产品)商誉的实现;因此,虽然商标可以帮助企业充分实现其商誉价值并具体承载企业的商誉,但商誉与商标之间是“皮”与“毛”的关系,即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前提,换言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2)讨论正向混淆和反向混淆案件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明确正向混淆中被告因攀附原告的商誉或知名度而获利,同时造成原告损失,因而损害赔偿金额的计算应该以原告损失为基础,或者在原告损失难以计算时,由原告选择依据被告的侵权获利进行计算,这符合《商标法》第63条规定的损害赔偿金额的计算方式;而在反向混淆案件中,由于被告并非因攀附原告的商誉或知名度而获利,其对在先商标权人造成的伤害,源自在后商标的使用导致商标权人对其在先商标控制权的减损,因而损害赔偿金额的计算思路需要另辟蹊径。(3)论证在商标反向混淆案件中将商标许可使用费的倍数作为合理确定赔偿金额的方法,具体而言,可以通过一个假想商标许可谈判来分配涉案商标显著性带来的合作利益;并基于纳什谈判解(Nash Bargain Solution,NBS)的概念来得到在先商标使用者和在后使用者分别对应的谈判利益和相应的商标许可费,也即NBS商标许可费;进而考虑到在后商标使用中类似于不当“强制”使用的影响,还可计算上述NBS商标许可费的合理倍数以作为损害赔偿金额。笔者认为,依据NBS商标许可费合理倍数确定的损害赔偿金额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商标的市场价值,并有助于遏制我国目前存在的商标滥诉和商标囤积乱象。
一、引子:从炎黄盈动诉亚马逊通案谈起
2018年7月,北京炎黄盈动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起诉北京光环新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亚马逊通技术服务(北京)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中,诉称二被告未经其许可使用“AWS”标识经营云计算服务,侵犯了其对“AWS”注册商标享有的专有权,索赔3亿元。2020年5月6日,该案一审判决结果宣布,法院判令二被告停止侵权,不得再使用“AWS”标志及近似标志,并共同赔偿原告损失及合理费用合计7672.3万元1。[1]
本案原告成立于2003年1月9日,注册资本2,105.2632万元,经营范围包括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销售自行研发的软件产品;经营电信业务。作为一家基础软件公司,原告通过为大中型企业/政府提供共享BPM PaaS平台,帮助简化企业流程应用的开发、运行和维护。原告称,AWS是其核心品牌,于2004年申请注册商标,并于2008年2月7日获准注册并持续使用。
本案第二被告亚马逊通技术服务(北京)有限公司系全球最大电商亚马逊的子公司。亚马逊于2006年推出其云服务AWS(Amazon Web Services),根据Canalys全球云服务市场调研报告,2019年AWS的全球云服务市场份额为32.3%,居全球第一。而亚马逊公布的2019第四季度及全年财报显示:2019财年,亚马逊营业收入为2805.11亿美元,同比增长20.45%;其中云计算业务AWS收入350.26亿美元,同比增长36.53%;在第四季度,亚马逊总营收为874亿美元,同比增长21%,净利润为32.68亿。2016年8月,本案第一被告北京光环新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亚马逊通技术服务(北京)有限公司签订运营协议。根据协议,亚马逊授权光环新网在中国境内提供并运营北京区域的亚马逊云技术及相关服务(AWS云服务)。
基于以上事实,无论是从规模、历史还是知名度来看,本案中的被告均比原告有悬殊的优势,导致本案与一般商标纠纷案件大不相同。在一般商标纠纷中,被告依靠使用与原告相同或相近的商标,令相关公众产生混淆或者误认为其与原告存在某种特定联系,从而达到攀附原告以取得商誉并获得相应经济利益的目的。相较之下,本案中的情形反而是:相关公众会“误认为炎黄盈动公司(也即本案原告)是他人(也即本案被告)相应服务品牌的代理商或出于攀附他人商誉目的而使用‘AWS’商标”。在诉讼中原告也提交了相关证据用以证明,在实际商业活动中“公众容易将炎黄盈动公司提供的相关商品或服务与光环新网和亚马逊通联系在一起”,并被法院所采信。可见,本案是一个典型的反向混淆案件。
抛开与本案相关的亚马逊通注册AWS商标过程中的争议不谈,无论是7672.3万元的一审判赔金额还是原告一审提出的3亿元诉赔金额,都难免不令人唏嘘。网络上关于“碰瓷儿”的说法也是甚嚣尘上,毕竟“攀附”的方向错位,而原告却提出了高达自身营业收入十几倍的损害赔偿诉求金额,即使是打折后的判赔金额也达到其注册资本的数倍!
那么,应该如何客观看待这一案件及其判决结果呢?笔者认为,为了对此案结果做出正确的评判,需要首先解决其中的核心问题,也即在反向混淆案件中应该如何确定损害赔偿金额。下文将基于经济学理论框架首先澄清商誉与商标价值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比较正向混淆与反向混淆的异同,进而给出以商标许可费及合理倍数作为确定反向混淆案件中损害赔偿金额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示例,最后将讨论使用合理许可费倍数确定赔偿金额对于解决我国当前商标囤积乱象的意义所在。
二、商标与商誉之间的关系
为更清楚地讨论商标纠纷案件的本质,以及正向混淆与反向混淆两类案件的联系与区别,需要澄清商标与商誉之间的关系问题。根据财务会计理论,商誉(goodwill)也即企业从其商品生产和销售中获得的超额利润,具体是指企业获得高于正常投资报酬率的盈利能力所对应的价值。究其根源,则是因为企业在技术、生产、管理、人员、历史、地理位置等方面所具有的优势,令其在同等投入条件下可以获得超出同行企业的超额利润。换言之,企业表现在具体商品或服务中的超额利润或商誉,在本质上仍然有赖于企业的长期经营,最终归功于企业在研发创新、生产设计、质量控制、售后服务、人员培训及社区贡献等方面的持续投入和经营成效。
图1:商誉与商标价值的关系
而商标的作用则是通过将企业(或产品)的这些竞争优势固定于某一商业标识,助力于企业(或产品)商誉的实现。图1展示了企业商誉与商标价值之间的关系:整个圆形为企业的总体超额价值,也即等同于企业的整体商誉2;中心圆部分对应的核心超额价值是企业商誉的基础,可以称为核心商誉;而外围的环形部分对应商标价值,也即商标利用其显著度来帮助实现的那部分企业商誉。
从图中可知,商标的使用提高了企业的利润,表现为企业商誉的提高;并且显著度更高的商标可以带来更大的商誉增值,因此也就对应更高的商标价值。但从图中也可以看出,商标价值必须依附于企业的核心商誉而存在,是“毛”与“皮”的关系。虽然商标的设计和推广也需要额外付出成本,但商标及其价值却不能独立于企业或产品而存在。若无企业的核心商誉,商标的显著度再高,也只能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具言之,一个注册商标在未被商标注册人自己使用或者已完成许可/转让他人之前,也仅是一个商标注册文件而已。3
假设企业核心商誉为π0,使用的商标对企业利润的贡献率为 x 。核心商誉与商标贡献率的乘积,即为商标给商标权人带来的超额利润,也即商标对应的价值;而对应每单位核心商誉的商标价值 x ,也即商标显著度。此时,企业商誉变为π=π0(1+x)。显然,商标显著度越高,其为企业带来的额外商誉越多;但同时,企业的核心商誉越多,商标能够帮助实现的超额利润也越多。在图中表现为,更大的x值和更大的π0值,均可以提高商标带来的企业利润增加部分
,也即商标价值。可见,更高的商标价值不仅与商标自身的显著度有关,更有赖于企业的核心商誉。换言之,商标的作用是令企业的核心商誉价值π0得以更加充分的实现,因而其价值π0x自然也更依赖核心商誉本身的价值。
从另一个角度观察,也可以帮助澄清商标与商誉的作用。假设没有了商标的加持,企业商誉会有所下降,但企业基于自身多年经营的核心商誉π0仍然存在,并不会因商标的改变而受到影响。相较之下,无任何企业或商品可以依附的商标,虽然可能拥有较高的显著度x,但正如图1中所示,因其变成失去商誉中心圆核心部分的环状,因而只能作为一个空洞的边缘存在,并不具备独立的价值。此时,如果该“空心圆”商标要取得不为零的价值,其必须通过找到另一个具有核心商誉的企业,并附着其上才能得以实现。换言之,企业的核心商誉是商标价值得以体现的必要基础和前提条件;反之则不同,缺少了商标,企业的核心商誉仍然存在,只是商誉的实现程度会有所降低。
三、不同方向的商标混淆比较:正向混淆与反向混淆
商标侵权纠纷主要体现为商标混淆纠纷,具体是指由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服务上使用相同或者近似商标,从而使消费者产生了混淆误认。一般情况下,消费者会将在后商标误认为是在先商标,也即发生正向混淆。但也会出现反向混淆的情形,即由于在后商标的使用,令消费者误以为在先商标权人的商品或服务来源于在后使用者或者与之相关。反向混淆之所以发生,显然是因为在后商标的使用者具有更高的知名度和商誉,这一点在下述的相关分析中至关重要。
与正向混淆的商标侵权纠纷案件相比,反向混淆是一个较新的概念,对其中受害者提供法律救济的逻辑,也与正向混淆完全不同。在正向混淆中,被告利用相同或近似商标对原告的知名度和商誉进行攀附并从中获利,同时导致原告商誉的减损,因此需要通过补偿原告的损失来对其进行救济。而对于反向混淆案件来说,鉴于被告本身拥有更高价值的商誉和知名度,其对在后商标的使用并未攀附原告的商誉,因而原告遭受的损失主要表现为其对在先商标控制权的减损。相应地,反向混淆案件中法律救济的目的则是为了防止更加有名、资金雄厚的企业从不太知名的企业手中强行夺取他人的商标。需要特别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在后商标的使用并非出于干扰在先使用者的经营活动并攀附在先使用者的商誉,而只是因为涉案商标更符合在后使用者的经营策略。因此,在计算相应的损害赔偿金额时不应以给在先使用者商誉造成的损失为基础,而需要另辟蹊径。
基于图1,可以比较容易地说明正向混淆与反向混淆这两类商标侵权纠纷案件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在正向混淆案件中,原告(在先使用者)既是涉案商标的所有人,也同时拥有稳定的高额核心商誉,两者的结合令其实现了超高的企业商誉。表现在图1中,整体企业商誉π均为原告所拥有,既包括核心商誉π0,也包括具有显著度x的商标。也正是这样的企业商誉,让竞争对手产生了攀附的企图和盗用商标的行为。具体而言,正向混淆商标纠纷案件中的被告,通过在自己生产或销售的商品或服务上使用与原告商标相同或近似的标识,令消费者产生混淆,误以为其商品或服务系由原告生产或销售的,从而达到从原告商誉中获得不正当的超额利润的目的。例如,基于对原告商誉的依赖,消费者可能购买了被告的商品或服务而提高了被告的市场份额,或者支付了更高的价格从而增加了被告的利润率,等等。
在正向混淆案件中,鉴于整体企业商誉π为原告(在先使用者)所拥有,被告对其商标进行攀附造成的损失即表现为原告从其商誉所得利益的减损。因此,确定正向混淆案件中的损害赔偿金额即应该以原告的商誉收益损失为基础,在原告损失难以计算时,由原告选择将被告的违法获利视为原告的损失4;此处的假设是被告的商品和服务销售替代了原告的市场份额,因而被告的违法获利可以等同于原告的经济损失。这就解释了,为何在正向混淆案件的司法实践中,最常见的做法是基于被告的侵权获利来计算原告的损失金额。
而在反向混淆案件中,原告(在先使用者)是涉案商标权人,但其是否拥有稳定的核心商誉却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原因在于,在反向混淆案件中,消费者产生的混淆是误以为原告生产和销售的商品或服务是由被告提供的,也即被告才具有明显超过原告的商品知名度和稳定的高额企业商誉!换言之,如果此时商标起到了引导消费者和帮助充分实现企业商誉的作用,那么反向混淆案件中商标所依附的反而是被告的核心商誉,而非原告自身的核心商誉!表现在图1中,原告虽然具有较高显著度x的商标,但其中真正发挥作用的核心商誉π0却不属于原告,当然图中的企业商誉π也并不为原告所拥有。
显而易见,在反向混淆案件中,被告使用涉案商标对原告造成的损失不能基于图1中企业商誉π的减损来计算;同理,上述关于将被告违法获利等同于原告经济损失的逻辑也不能成立。根本原因在于,反向混淆案件中,并不存在被告(在后使用者)对原告商誉进行攀附的前提条件。被告对涉案商标的使用虽然晚于原告,但其企业核心商誉却远远超过了作为商标权人的原告,其并无攀附原告的必要性;反之,除了涉案商标所具备的显著度之外,原告也并没有其他任何可以帮助被告提高其产品知名度或企业商誉的资源可供被告攀附。
因此,被告使用涉案商标所获得的额外利润,虽然对涉案商标的显著度有所依赖,但其价值基础仍然是被告自身所具备的核心商誉。可见,这两种商标案件中被告的动机和获利机制截然不同。在正向混淆中,被告依靠攀附在先使用者的商誉和知名度获取经济收益;而在反向混淆中,被告是为了最大程度实现自己核心商誉的价值以及商标布局策略,使用了容易引起与在先使用商标相混淆的涉案商标。例如,在本文开头所引用的亚马逊通一案中,被告的母公司亚马逊使用AWS作为其云服务的商标,是基于亚马逊云服务所对应英文名称(Amazon Web Services)的首字母缩写。5
当然,即使并未攀附在先商标权人的商誉,反向混淆案件中的被告因在后商标的使用仍然是给在先商标权人造成了伤害,即导致其对在先商标控制权的减损,对此理应予以补救和赔偿。下文即讨论何种救济方式和损害赔偿确定方法更为妥当。
四、假想商标许可协议谈判和纳什谈判解(Nash Bargaining Solution)
如上文所述,正向混淆商标案件中的损害赔偿金额计算以原告的商誉收益损失为基础(对应图1中整个企业商誉π中可能发生的减损部分);而在原告损失数据不可获得时,可以将被告的违法获利视同原告的损失,用来替代计算损害赔偿金额。上文讨论中也已经澄清,在反向混淆案件中被告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来源于原告对其拥有的在先商标的控制权的减损,因此不能基于图1中企业商誉π的分析来计算损害赔偿金额,进而也不能用被告违法获利来近似计算原告的经济损失。
那么,应该如何确定反向混淆商标案件中的损害赔偿金额呢?基于上文的讨论可知,在后商标使用人在实施自身商标策略的过程中,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方面,在后商标的使用令其商誉和超额利润得以提高,增加值也即商标使用给在后使用人带来的收益;另一方面,在后商标的使用给在先商标的使用带来了混淆,使得在先使用人不能完全获取自己基于商标显著度x可以得到的经济利益,其减损值即对应在后商标使用给在先使用者造成的损失。假设在先使用人的核心商誉为,从上文讨论可知,在先商标使用人的商誉远小于在后使用人的商誉,也即
。又鉴于上述两个后果对应的金额大小分别由
和
决定,可以推导出下面的结论:即反向混淆案件中在后商标使用给在后使用人带来的收益,一般会远高于其给在先商标使用人造成的损失(也即
)。而这种收益远高于成本的情况,恰好使商业谈判成为可能。
可以假想下面的谈判,目标是签订在先商标的许可协议,其中在先使用者将其商标许可给在后使用者。谈判中的核心内容是许可费标准的确定,本质是合作收益如何在双方之间进行分配。如果谈判失败,则双方各自应对不合作的后果:在先商标使用者(S)获得对其商标的完全支配权并获得基于自身商誉的收益,即
;而在后商标使用者(J)需要停止使用涉案商标,以及设计和推广新的商标来帮助充分实现自身商誉。假设J所需的额外商标成本为c,则其在与S谈判失败情况下的收益为(π0 -c)x,也即J在支付了额外商标成本之后的商誉增值。两者在谈判失败时得到的结果均独立于合作之外,相应地把这些对应的收益称为外部选项(outside option)。
如果能够在上述谈判中引入双方均可接受的商标许可协议,则其中的商标许可费可以作为反向混淆案件中计算损害赔偿金额的基准。考虑到争议已经发生,假想的商标许可谈判未能成功,实际中发生了在后商标使用人对涉案商标的“强制”使用,因而可以在假想谈判达成的合理商标许可费基础上再乘以一个合理的倍数,例如3倍。但需要强调,这里的倍数使用是为了考虑谈判未能达成时发生了类似“强制”使用的情形,而并非是对在后使用者进行惩罚,因此不应该使用惩罚性赔偿一类的指代和描述。
在假想商标许可谈判中,如何确定合理许可费呢?纳什谈判解(Nash bargaining solution)的概念提供了答案。假设有公司J和公司S,通过谈判来分配大小为1的合作收益,两个公司的收益分配份额分别为(α ,1-α ),其中α 越高,公司J从合作收益中分得的份额也越多;如果二者不能达成合作协议,则公司J和S各自得到(OJ ,OS),其中OJ ,OS分别表示谈判不能达成时J和S分别面临的外部选项(outside option)。
根据纳什谈判解的概念,满足有效、公平、合理这几项标准的收益分配份额由下式给出:
(1)
图2用图示形式展现上述解,其中横轴OJ - OS表示双方外部选项价值的差异,随着OJ 的增加而增加,随着OS的增加而减少;纵轴表示分配给公司1的份额α *。显然,最优谈判解(也即纳什谈判解)对应的公司J的收益分配份额α *,会随着自身外部选项价值OJ 的提高而增大,会随着对方外部选项价值OS的提高而减小。
图2:纳什谈判解中分配份额与外部选项价值的关系
将纳什谈判解的概念应用于本案中,双方要分配的合作利益等于商标为被告带来的超额利润,也即商誉提高值,;对于原告S来说,外部选项对应的价值是涉案商标能为自身产品经营带来的超额利润,也即许可协议的合作安排不能达成时原告将得到的商誉收益增值,
;而对被告J来说,外部选项则是要为得到涉案商标对应的超额利润,在设计、推广次优商标等方面额外支付费用c,对应的外部选项价值也即(π0 -c)x。鉴于模型中将双方谈判中的合作收益标准化为1,双方各自的外部选项价值也需要与合作收益进行同样的标准化处理。据此可得,双方各自的外部选项价值分别为:
进而可知,基于纳什谈判解的双方各自的分配份额分别为:
(3)
五、反向混淆商标案件中损害赔偿金额的确定:一个示例
下面基于具有现实合理性的参数假设,来分析反向混淆案件中的损害赔偿金额应该如何确定。其中,除了应用纳什谈判解概念来给出假想商标许可谈判对应的合理许可费金额之外,还将比较其他几种在已有司法案件中出现过的损害赔偿计算方法。
具体的参数假设如下:反向混淆纠纷中涉及到的在先商标使用者S,其年均营业收入为1亿元,超额毛利润5000万元,其中在先使用商标贡献度为20%,对应商标对超额毛利的贡献额为1000万元;在后商标使用者J在诉讼之前的年均营业收入为100亿元,超额毛利润50亿元,在先使用商标贡献度也为20%,商标对超额毛利的贡献额为10亿元。诉讼后,在后商标使用者被禁止使用涉案商标,需另外追加商标的设计和宣传成本10亿元。
由上一节中关于纳什谈判解的讨论可知:x=0.2,π0=50,=0.5,c=10。因而,双方的合作收益为
=10,S的外部选项价值为
,J的外部选项价值为
。对应的在后商标使用者J的谈判分配份额为:α *=0.895,而在先商标使用者S的谈判分配份额为:1-α *=0.105。因此,基于双方谈判中涉及的合作收益为10亿元,在先商标使用者S从纳什谈判中得到的利益分配金额为1.05亿元。
需要指出,上面的参数设定中包含了几个比例关系:商标贡献度20%,公司广告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10%,以及在先商标使用者S的规模为在后使用者J规模的百分之一;其中前两个假设是基于消费品行业的代表性数据,而第三个条件是在J远大于S的基础上的假设。鉴于消费品行业中商标的作用偏高,而现实发生的反向混淆案件中两者的规模比例通常会更加悬殊,因此,上述参数假设基础上的分析会倾向于得出更有利于在先商标使用者J的损害赔偿金额。6换言之,如果选用更有现实代表性的参数设定,所得的谈判分配结果会比上述分析中的分配方案更有利于在后商标使用者J。
表1比较了4种不同计算方法分别得出的损害赔偿金额,其中(1)-(3)列总结了示例中的相关参数设定,(4)-(6)列分别给出前3种计算方法,即分别依据被告毛利润、被告毛利润中商标贡献额以及纳什谈判解概念得出的损害赔偿金额。从表中可见,已有案件中常用的损害赔偿金额确定方法,不论是基于被告毛利润的计算方法(计算方法1,例如亚马逊通案中原告一审诉求所依据的逻辑),还是基于被告毛利润中商标贡献额的方法(计算方法2,例如亚马逊通案一审判决中所采用的分析),均会得出远高于纳什谈判解(计算方法3)所得到的结果。7
为什么表1中几种不同的计算方法会得出差别巨大的损害赔偿金额?究其原因,是否考虑商标对利润的贡献度可以解释计算方法1的结果数倍于计算方法2的结果;而计算方法3(纳什谈判解)的结果又比计算方法2大幅降低的原因则更为复杂。首先,在计算方法2中,涉案商标的利润贡献额直接给出了损害赔偿金额,而在计算方法3(纳什谈判解)中,这一商标贡献额是双方需要通过谈判来分配的合作利益,也即只是计算的起点;其次,在纳什谈判解中,双方的利益分配份额由各自的谈判地位所决定,而后者又取决于其在谈判失败时得到的对应收益,也即外部选项的价值;再次,双方对应的外部选项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各自原本具有的核心商誉大小,而在后商标使用者J相比在先使用者S有超高的核心商誉,因而获得较高的谈判地位。相应地,纳什谈判解中J获得的合作利益的分配份额更高,占到89.5%。
但需要考虑到在现实中上述商标许可谈判并未能达成,在后商标使用者J实际是“强制”使用了会与在先商标发生混淆的涉案商标。为了顾及类似不当“强制”使用的影响,表中增加了第(7)列,也即计算方法4,其中给与了三倍于合理许可费的损害赔偿金额。从表中可见,即使提高了3倍后的许可费金额也仍然不到计算方法2(被告毛利润中商标贡献额计算方法)对应结果的三分之一。8
六、结论与启示
通过上述示例中的4种方法计算所得损害赔偿金额之间的比较,可以揭示出目前涉及反向混淆商标案件中判赔金额确定所面临的挑战,也即有些案件中判赔金额明显过高。原因在于反向混淆案件中确定损害赔偿金额时,如果简单比照正向混淆案件,将在后商标使用者的规模和商誉作为计算损害赔偿金额的基础,显然是完全未予考虑反向混淆案件与正向混淆案件之间在影响机理和救济目的等方面的本质性差异。
众所周知,商标反向混淆的理论和案例最早出现在美国,1977年的Big O Tire Dealers, Inc.诉Goodyear Tire & Rubber Co.案(简称“Big Tire”案)被广泛认为是最早正式确立商标反向混淆理论的案件[2]。而商标反向混淆理论中为在先商标使用者提供救济的逻辑基础如下:在后使用者对涉案商标的使用造成了与在先商标之间的混淆,使得在先商标使用者无法完全控制对其商标的使用,从而使其可以从中获得的商誉增值遭到了减损[3]。基于此,在“Big Tire”一案中,美国初审和二审法院均以发布更正广告(correct advertising)的费用为基础来确定损害赔偿金额。
而反向混淆理论在中国引起广泛关注,则起源于2007年的“蓝色风暴”案[4],又由于其后发生的“纵横两千”案[5],“卡斯特”案[6]以及“新百伦”案[7]而备受关注和质疑。在这些案件中,均系按照在后商标使用者的毛利润来计算损害赔偿金额。但通过与美国反向混淆商标案例的对比可知,反向混淆事实在中国案件中的认定以及所确定高判赔额的逻辑,显然并不符合反向混淆理论和实践的初始逻辑。
回归到反向混淆概念的正确逻辑基础,意味着首先需要明确合适的损害赔偿概念和计算范围,即反向混淆给在先商标使用者带来的经济损失是其因对自身商标控制权的减损而不能完全获取基于商标显著度可预期得到的经济利益,这种经济利益的减损值即对应因在后商标使用而给在先使用者造成的损失。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损失并不是源于在后商标使用者对在先商标使用者商誉或知名度的攀附,因此不能基于在后商标使用者的营收、利润或利润中的商标贡献额来进行计算。
而上文讨论中所提出的依照纳什谈判解概念计算出的商标许可费(Nash Bargaining Solution,或NBS),则不失为反向混淆商标案件中确定损害赔偿金额的一种合适方法。首先,这种方法全面考虑了以下多个因素:原被告双方各自的核心商誉水平,以及商标显著度(或贡献度);其次,如果需要顾及类似不当“强制”使用的影响,还可以在上述NBS商标许可费基础上再乘以一定的合理的倍数。
上文讨论对其他商标侵权案件也具有一般性的启示。具体而言,关于商誉和商标价值之间关系的讨论也同样可以帮助澄清一些存在争议的商标侵权案件中的经济概念,并帮助提供更为合理的损害赔偿计算依据。例如,在一件商标侵权案件中,即使认定被告存在对原告合法注册商标的侵权使用行为,且被告因此得到了违法获利,同时造成了原告市场份额和盈利的损失以及未来商誉的减损,那么损失金额的计算也应该基于原告的商誉和商标显著度的乘积进行计算,而不是简单套用侵权获利的计算逻辑。如果原告选择明显高于其损失的被告营收或利润金额作为损失计算基础时,则应当提供充足的理由和证据。此时,虽然需要考虑原告损失难以计算的因素,但更需要特别警惕这一理由被用来作为选择错误计算逻辑的借口,尤其是在原、被告的规模和商誉差别巨大的情况下。
显而易见,如果在商标侵权案件的损害赔偿计算中,能够遵循前述商誉和商标之间的正确逻辑关系,将使那些并不具有真实核心商誉的企业缺乏足够的动机,去通过抢注和囤积商标而向大规模实体企业发起商标诉讼来“碰瓷儿”获利,不论这些商标纠纷是被认定为正向混淆或是反向混淆。进而,通过令损害赔偿金额与商标的真实市场价值相匹配,也可以促使商标许可和转让等市场交易的正常进行,从而有利于实现商标等资源在生产、消费和创新过程中的最有效配置。最终,这将有望改进我国当前面临的商标抢注、囤积和滥诉等现象,帮助避免社会资源转向以财富分配为目标的投机行为,转而引导社会资源更多地投向创造性活动和生产性行为。
近年来多个商标反向混淆案件中的高判赔额引发了较多争议,导致学界和业界对商标反向混淆理论提出一些质疑和批评[8]。而如果能够在商标反向混淆案件中,正确认识损害赔偿金额计算的经济逻辑,则将有助于推动商标反向混淆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注释:
1.见亚马逊AWS商标侵权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京民初127号民事判决,此案目前正在二审中。
2.企业的总体超额价值是超出了本行业中投入要素规模相同的其他企业平均价值的部分,是企业生产要素正常投入所产出的价值之外的部分,其产生归功于本企业在创新和经营效率、历史和地理地位、人员素质水平、服务和社区声誉等各方面所具有的竞争优势。因此,在反映公司价值和财务状况的财务会计报表中,企业的超额价值也即商誉。举例来说,A公司在购买B公司时,收购价格为10亿元;但对B公司的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和专利技术进行价值评估,结果是6亿元;两者之间的差距,4亿元,即是B公司的商誉。显而易见,公司商誉中包含的是B公司比较同行业其他企业的超额价值,其中包含了B公司常年发展中积累的各种竞争优势,例如高素质的管理团队、常年维护的客户关系,等等。而其中商标的作用是通过建立固定的标识而令这些核心商誉得以更加充分的实现,因此商标对应的只是公司总体商誉中的一小部分。
3.诚然,商标的转让或许可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而其费用水平则与商标本身基于显著度的价值有关。商标的显著性越强,其每单位核心商誉带来的增值越高,也即商标显著度越高,则对应更高的商标价值。但鉴于其具体实现需要依托某个企业或商品的核心商誉,商标价值的确定会涉及其他市场因素,包括商标市场的供需关系等,将需要另外著文加以论述。
4.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三条,“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难以确定的,可以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权利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参照该商标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对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赔偿数额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5.如前文所述,本文分析是基于亚马逊通一案已被法院认定为反向混淆纠纷的假设前提下展开,而对于亚马逊公司使用的“Amazon Web Services”和“AWS”商标在商标注册和复议过程中的争议,以及本案原告是否在云服务领域对“AWS”享有注册商标专用权、“Amazon Web Services”和“AWS”商标作为知名产品特有名称的事实是否应该影响案件的一审裁决等问题,本文不做评述。
6.从公式(3)可知,J的分配份额与商标贡献度和广告费用占比呈反比,而与J与S之间的规模比例呈正比。
7.鉴于司法实践中是使用毛利润而非此处示例中的超额毛利润来计算损害赔偿额,因而表1中的比较实际上仍然低估了计算方法1和2与纳什谈判解给出的损害赔偿额之间的差距。
8.计算方法4所得损害赔偿金额与计算方法2所得结果之间的比例等于0.315/1,显然不及三分之一。
参考文献:
[1]亚马逊AWS商标侵权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京民初127号民事判决。
[2]Big O Tire Dealers, Inc. v. Goodyear Tire & Rubber Co., 561 F.2d 1365, 1371-72 (10th Cir.1977).
[3]Thad G. Long & Alfred M. Marks, Reverse Confusion: Fundamentals and Limits, 84 TRADEMARK REP. I, 4 n.7 (1994).
[4]蓝野酒业诉百事可乐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07)浙民三终字第74号民事判决。
[5]“纵横两千”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08)浙民三终字第108号民事判决。
[6]“卡斯特”案: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提字第25号民事判决。
[7]“新百伦”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粤高法民三终字第444号民事判决。
[8]李扬:《商标反向混淆理论的“七宗罪”》,中国知识产权杂志,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1MjEzMjg3OA==&mid=2649667991&idx=1&sn=50adfc621f4c85d07b6e275f02fba072&source=41#wechat_redirect,访问日期:2022年7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