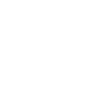作者:
马 乐 华东政法大学涉外法治学院教授、副院长
陈昂雨 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最高人民法院在华为诉Netgear标准必要专利纠纷中应华为公司请求针对Netgear公司在美国法院提起的禁诉(执)令请求作出反禁诉(执)令裁决。这是我国法院首次就诉讼一方当事人首先在域外法院提起禁诉令请求后作出的反禁诉令裁决,也是我国法院继2020年在一系列标准必要专利诉讼中适用行为保全规定作出禁诉令裁决后再度依此司法方法作出禁诉令裁决。以标准必要专利争议为典型代表的涉外知识产权纠纷领域极易发生平行诉讼,由此催生出禁诉令与反禁诉令的申请以及法院据此裁决的空间。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法院都有反禁诉令的司法实践。从个案来看,我国法院作出的反禁诉令裁决不仅是对当事人正当程序权利与实体权利保护的积极作为,也是保障我国司法管辖权以及诉讼程序不受域外禁诉令干扰的必要防御措施,是在知识产权领域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重要实践。
关键词:标准必要专利;禁诉令;反禁诉令;行为保全
文章简介:本文是作者主持的202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标准必要专利国际平行诉讼中的禁诉令问题与中国对策研究”(23YJC820023)阶段性成果。作者曾在2022年Fourth IP & Innovation Researchers of Asia (IPIRA) Conference(第四届亚洲知识产权与创新研究者大会)以“Anti-ASI over SEPs Dispute: A Way Out?”(标准必要专利纠纷反禁诉令:一种可行路径?)为题作主题演讲,本文可视为这一思考的延续。
一、问题的提出
标准必要专利(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简称SEPs)因其广泛适用性与更强垄断性成为全球科技巨头竞争的主战场。特别是在通信、物联网(IoT)等高度依赖技术兼容性与互操作性的领域,华为、中兴、小米等中企与苹果、三星、高通等外企以及交互数字等外国非专利实施实体(Non-Practicing Entities, NPEs)就5G等前沿领域SEPs许可在不同司法管辖区频发诉讼。其中,SEPs权利人与实施者在不同法域就同一专利以不同诉由互诉产生平行诉讼。为维护司法管辖权并以此保障SEPs许可费的决定权,中、外法院爆发禁诉令(Anti-Suit Injunction, ASI)与反禁诉令(Anti Anti-Suit Injunctions, AASI)的司法混战。中国法院在面对域外SEPs禁诉令从未颁发反禁诉令的情况下于2020年4个月内签发5项禁诉令裁决,被认为是SEPs诉讼领域最“咄咄逼人”的司法管辖区。[1]这不但引起受影响外国法院签发反禁诉令予以对抗,还引发欧盟在WTO对中国“起诉”。[2]最高人民法院此番在华为诉Netgear标准必要专利纠纷中应华为公司请求针对Netgear公司在美国法院提起的禁诉(执)令请求作出反禁诉(执)令裁决,是我国法院首次就诉讼一方当事人首先在域外法院提起禁诉令请求后作出的反禁诉令裁决,也是我国法院继2020年在一系列标准必要专利诉讼中适用行为保全规定作出禁诉令裁决后再度依此规定作出禁诉令裁决。从禁诉令到反禁诉令,尽管裁决依据和司法逻辑相似,但其司法意义有所不同,在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中的工具价值也值得进一步探究。
二、华为诉Netgear案中的反禁诉(执)令
(一)案件事实
华为与Netgear之间的知识产权纠纷,始于2020年,聚焦于Wi-Fi相关的SEPs许可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裁定书的认定,华为作为全球领先的通信技术企业,多次向Netgear提出根据公平、合理、无歧视(Fair, 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 简称FRAND)原则进行专利许可的协商,但Netgear的反应始终冷淡,未能促成实质性的谈判进展。[3]随后,华为于2022年至2024年间分别在中国、德国以及欧洲统一专利法院(UPC)提起涉案标准必要专利侵权诉讼,其中包含在中国的两次专利侵权诉讼。对此,Netgear采取了激烈的反击策略,不仅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中区地方法院对华为提起反垄断民事诉讼,指控华为违反美国《谢尔曼法》并企图垄断Wi-Fi技术市场,还进一步在美国法院申请禁诉令与禁执令(Anti-Enforcement Injunctions, AEI),意图限制华为通过外国法院获取或执行禁令的能力。面对Netgear的行动,华为向慕尼黑第一地区法院和UPC分别申请反禁诉令和反禁执令(AAEI),同时向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提交了行为保全申请,请求禁止Netgear在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法院、海关或行政执法机构采取类似行动,以确保专利纠纷的公正处理。目前,慕尼黑第一地区法院支持了华为的反禁诉令申请;UPC的慕尼黑分庭也作出了反禁诉令,判决华为胜诉,判定Netgear侵权且行为不符合FRAND原则,针对Netgear下达了覆盖德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丹麦、芬兰和瑞典7个UPC成员国的禁令。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反禁诉令性质的行为保全裁定书,裁定Netgear不得向美国及其他外国法院申请禁诉令或禁执令,已申请的须在24小时内撤回或中止,且不得对本裁定提出对抗性申请,即Netgear不能针对中国法院作出的反禁诉令再申请禁诉令,也就是反反禁诉令(Anti-AASI)。
(二)反禁诉(执)令裁决
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华为的行为保全申请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查知识产权纠纷行为保全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从以下几个因素考量,即申请人的请求是否具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包括请求保护的知识产权效力是否稳定;不采取行为保全措施是否会使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或者造成案件裁决难以执行等损害;不采取行为保全措施对申请人造成的损害是否超过采取行为保全措施对被申请人造成的损害;以及采取行为保全措施是否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其他应当考量的因素。
法院认为,首先,华为作为两件有效中国发明专利的专利权人,指控Netgear侵犯其专利权,并在中国法院提起诉讼。济南中院认定Netgear侵权,并判决其停止侵权。Netgear试图通过美国法院申请禁诉令来阻挠华为在中国的诉讼,此举缺乏正当理由。其次,华为因Netgear在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谈判中存在明显过错,请求停止其侵权行为。Netgear在美国法院申请禁诉令,若成功,将迫使华为放弃在中国的诉讼,损害其合法权益。华为作为善意许可人,其权益应受法律保护。再者,在华为与Netgear的专利侵权纠纷中,若不实施行为保全措施,华为将面临显著损害,包括无法及时获得专利收益和正当程序权利受损。相比之下,批准华为的行为保全申请,仅要求Netgear在一定期限内不采取某些行动,不会给Netgear带来额外损失。最后,作出反禁诉令裁决不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华为的申请具备充分的事实和法律支撑,应当予以支持。据此,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裁决,要求Netgear及其关联公司在本两案审理期间及裁判作出后,不得向美国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法院、海关或者其他行政执法机关提出旨在禁止华为就本两案所涉专利在中国继续进行或者提起新的专利侵权诉讼或申请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就本两案所作判决的申请,如已提出,应当在收到本裁定后24小时内撤回或者中止上述申请,并不得针对本裁定再行提出对抗性申请。裁决还规定了明确的处罚措施,如违反本裁定,自违反之日起,处每日罚款人民币100万元,按日累计。[4]
三、从禁诉令到反禁诉令的司法裁量
中国法院在涉外知识产权纠纷领域作出禁诉令裁决的司法实践可以追溯至2020年一系列涉外标准必要专利诉讼,包括华为诉康文森案[5],小米诉交互数字案[6]、中兴诉康文森案[7]、三星诉爱立信案[8]和Oppo诉夏普案[9]。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立法体系中并无禁诉令这一来源于英美法系的规则。在这些案件中,法院通过适用民诉法中的行为保全规定作出了具有禁诉令功能的裁决。这由此被视为中国法院作出的禁诉令裁决。其中,法院主要考虑的因素包括:域外诉讼对本诉及未来判决执行的影响、行为保全措施是否确有必要、行为保全对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利益影响的考量(不采取行为保全措施对申请人造成的损害和采取措施对被申请人造成的损害相比较)、行为保全措施是否损害公共利益、对国际礼让原则的影响。最高院在华为诉Netgear案中的反禁诉令裁决也基本依循了法院此前在禁诉令裁决中的裁量方式。
禁诉令与反禁诉令本质上都是法院对诉讼一方当事人在另一司法管辖区诉讼行为的限制。从司法效果上,禁诉令可以阻止一方当事人在另一司法管辖区启动重复性诉讼,或者在其已经提起重复性诉讼后要求其停止该诉讼程序。如果在另一司法管辖区的诉讼程序已经结束,禁诉令可以起到阻却当事人请求该法院执行其作出判决的效果,也就是禁执令。反禁诉令与禁诉令在原理上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反禁诉令旨在阻却当事人在另一司法管辖区向法院申请作出的禁诉令的执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华为诉Netgear案中的反禁诉令之所以被视为中国法院作出的首例反禁诉令裁决,是因为该裁决是在Netgear首先在美国法院申请禁诉令后旨在阻却该禁诉令执行而作出的。中国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此前在三星与爱立信标准必要专利纠纷中应申请人三星及其关联公司请求甚至曾作出针对爱立信及其关联公司可能在其他司法管辖区申请反禁诉令的禁诉令,即反反禁诉令(AAASI)。[10]
四、反禁诉令司法裁量的国际比较
需要再次指出的是,中国并非全球首个作出反禁诉令裁决的司法管辖区。在此之前,美国、德国、印度等国法院都曾在标准必要专利纠纷中作出反禁诉令裁决。对比中外反禁诉令裁决有助于进一步厘清反禁诉令的司法原理及裁量方法。印度德里高等法院在IDC诉小米案的裁定书中参考印度最高法院在Modi Entertainment Network案和Dinesh Singh Thakur v. Sonal Thakur案中阐述的禁诉令颁发条件,对授予禁诉令的原则进行了列举,着重从国际礼让与公共政策两个角度对法院给予申请人以临时救济(即反禁诉令)进行了说理。法院认为,根据公平原则,以及允许原告提起一项仅适用于本法院管辖权的诉讼,并且可以在本国法律范围内维持,授予临时禁令是非常合理的。[11]慕尼黑州第一法院在IDC诉小米的德国诉讼中援引慕尼黑州高等法院在诺基亚和戴姆勒案中的意见,认为考虑到专利权的特殊性及其法律保护的必要性,申请临时禁令的请求权成立,并结合存在普遍意义上的紧急性、存在时间上的紧急性、以及相互对立利益的权衡三个方面,应当签发反禁诉令。法院同时指出,基于国际礼让原则考虑,该反禁诉令不会影响在中国确定全球FRAND许可费率的主诉讼。[12]美国德州东区法院在爱立信诉三星案中根据第五巡回法院提出的Unterweser因素[13],结合MWK和Kaepa两案,认为中国武汉法院的诉讼和禁诉令裁定,妨碍了发布禁令的法院政策,具有纠缠性或压迫性(vexatious and oppressive),且对被申请人构成损害或违背其他公平的原则,从而签发了反禁诉令。[14]
综观各国法院反禁诉令的司法裁量,印度德里法院将公共政策作为侧重点进行大篇幅的论证说理,更强调本国司法管辖权不容侵越;德国法院则更重视对专利权人所享有专利权正当性和保护必要性的论证并由此证成反禁诉令的正当性;美国法院主要考虑外国诉讼的不利影响。相比而言,我国法院在作出反禁诉令裁决时严格依据民诉法关于行为保全的规定及其相关司法解释从申请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当事人权利及本诉维护、双方损益衡量以及公共利益几个方面进行衡量,兼顾当事人个人权利与司法主权。
五、结语
我国法院作出的反禁诉令裁决具有积极意义。首先,当事人正当程序性权利得到肯定与保护。《民事诉讼法》第103条明确规定,民事诉讼一方当事人因另一方当事人的行为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的,可以申请法院责令该另一方当事人作出一定行为或者禁止其作出一定行为。本案中,Netgear在美国法院针对华为申请禁诉令的行为即属此种情形。最高人民法院依据华为申请作出反禁诉(执)令并无不妥。其次,国内法院管辖权和正当程序免受干扰。本案所涉及在中国境内的诉讼不论是一审程序(济南中院)还是上诉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均建立在法院依法具有管辖权的前提下且诉讼程序正当,并不存对美国诉讼构成所谓“纠缠性或压迫性”的情形。反之,如果不作出禁诉(执)令裁决,国内法院的管辖权和正当程序则会受到干扰,由此导致当事人的权利无法得到救济。因而,反禁诉(执)令是必要的。再次,反禁诉(执)令符合法院在面对禁诉(执)令时的通行做法。早在大陆集团诉诺基亚案(2019)中,面对大陆集团向美国法院申请的禁诉令以及美国法院可能作出的禁诉令裁决,德国法院就作出了针对该项禁诉令的反禁诉令。在IPCom诉联想案(2019)中,英国法院和法国法院也在美国法院应当事人请求可能作出禁诉令之前作出反禁诉令。此后,包括美国、德国、印度在内的域外法院都曾作出反禁诉令。特别是在与本案相关的欧洲诉讼中,华为也在12月11日从欧洲专利法院(慕尼黑分部)以及慕尼黑第一地区法院分别获得了针对Netgear公司的反禁诉令裁决。
总之,反禁诉(执)令是对当事人正当权利的保护。只要具备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中国法院通过适用行为保全规定作出反禁诉(执)令裁决并无不妥。在此前的康文森诉华为与中兴案(2018)、华为诉三星案(2018)中,当事人面对英国法院和美国法院所作禁诉令裁决对其在中国境内诉讼的影响都没有程序法上的救济途径。以后在类似的情形中,当事人都可以申请中国法院作出反禁诉(执)令维护自身正当权益。这不仅是中国法院在现有立法框架内进一步提升涉外司法效能的积极实践,也向全球展现了中国法院依据行为保全规定作出反禁诉令裁决的司法智慧。
注释:
1.See Wentong Zheng, Weaponizing Anti-Suit Injunctions in Global FRAND Litigation, George Mason Law Review, Vol. 30:2 (2023), pp413-425. Mark A. Cohen, China’s Practice of Anti-suit Injunctions in Standard-Essential Patent Litigation: Transplant or False Friend?, Jonathan M. Barnett and Sean M. O'Connor ed., 5G and Beyo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Competition Policy in the Internet of Thing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3, pp.215-241.
2.See WT/DS611/5, China-Enforc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9 December 2022.
3.参见(2024)最高法知民终914、915号裁定书。
4.参见(2024)最高法知民终914、915号裁定书。
5.参见(2019)最高法知民终732、733、734号之二裁定书。
6.参见(2020)鄂01知民初169号之一裁定书。
7.参见(2018)粤03民初335号之一裁定书。
8.参见(2020)鄂01知民初743号裁定书。
9.参见(2020)粤03民初689号之一裁定书。
10.武汉中院在(2020)鄂01知民初743号民事裁定书中的第五项裁决提到,“五、被申请人爱立信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在本案审理期间至案件裁判生效时,不得向中国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法院请求责令申请人三星株式会社、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撤回本行为保全申请或禁止申请人三星电子株式会社、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申请执行本裁定,并立即撤回或中止可能或已经提起的此类请求;”,此项裁决被视为法院作出的反反禁诉令(AAASI)。See also King Fung Tsang & Jyh-An Lee, The Ping-Pong Olympics in Antisuit Injunction in FRAND, 28 MICHIGAN TECHNOLOGY LAW REVIEW (2022), pp.305-383.
11.See InterDigital v. Xiaomi, 8772/2020 in CS(COMM) 295/2020, High Court of Dehli India.
12.See InterDigital v. Xiaomi, District Court (Landgericht) Munich I, judgment dated 25 February 2021, Case-No. 7 O 14276/20.
13.See In re Unterweser Reederei v. Gmbh, 428 F.2d 888 (1970).
14.See Ericsson Inc. v. Samsung Electronics. Co.,2:2020-CV-00380-JRG (E.D. Tex. Jan. 11,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