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杜颖 中央财经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专栏作者
为克服争议解决者作为中立裁判方而带有的自身主观认知的偏见,法律会经常运用特殊的技术手段进行主体置换,将争议解决主体定格为一个以客观化标准设定的行为人和判断者,即拟制主体,“善良管理人”“理性人”假设均属此例。[1]在商标法中,相关公众就属于这样一种拟制主体。商标显著性、商标知名度、混淆可能性等问题的判断,均涉及到拟制主体“相关公众”的适用;商标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查审理人员以及从事司法审判的法官,在解决争议之时,不是基于自己的知识结构和认知能力做出判断,而是要将自己置于“相关公众”的立场进行分析,从拟制主体的角度权衡考量而后得出结论,因此正确识别和界定相关公众就极为重要。但是,由于商品和服务的性质不同,市场消费和流通形态各异,要准确把握相关公众的范围并进而判断商标在相关公众中的知名度及相关公众的注意力水平就必须依照现实情况精细化处理。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将相关公众与普通消费者等视,如不限定消费人群的一般食品;但也有些情况下,相关公众根本不是普通消费者,或者主要不是普通消费者,如药品和医疗辅助用品。2015年5月13日,在Ferring BV与OHIM以及第三人Kora Corp. Ltd商标异议案的判决中,欧盟普通法院明确指出,对于医药和兽药制剂、医用卫生制剂,相关公众包括终端的消费者以及医疗和制药领域的专业人员,而对于填塞牙孔和牙模的材料等则只包括专业的医疗保健人员。[2]我国司法审判也采取类似观点,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在亿华药业公司“希能”商标异议案件中明确,对于用于疾病预防、诊断和治疗的药品,相关公众包括可能或实际使用前述类别药品进行病患预防、诊断和治疗的医护、药剂、病患人员,以及经营销售前述类别药品的相关经营人员。[3]
处方药的相关公众界定则会出现更为复杂的情况。通常情况下,患者获得处方药的途径是从医院购买以及通过执业医生开方后去药店购买。目前,在我国,患者从医生处获得处方后去药店购药的现象比较鲜见,更多的情况是患者从开方医生所在的医院直接购药。在这种情况下,为患者选择开出什么样的药品,医生往往会根据医院购进的库存药品的基本信息、医保政策、患者的病症以及身体综合状况(如年龄、过敏性反应、基础疾病等情况)做出综合考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相关公众的范围一方面要进行限缩,将患者界定在具有特定疾病的患者范围内,而不能以所有的普通消费者为对象范围判断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另一方面,在商标显著性和知名度的判断中,尤其要重点考虑医院和医生的认知状况,因为医院和医生首先决定了患者可选择的药品范围,在采购和推荐的过程中会对不同来源的药品进行选择取舍。我国《处方管理办法》规定,医师应当根据医疗、预防、保健需要,按照诊疗规范、药品说明书中的药品适应症、药理作用、用法、用量、禁忌、不良反应和注意事项等开具处方。这也充分说明,医师对于药品来源、药品疗效的了解远胜于患者。同时,特定药品的治疗效果也会通过医生的临床观察、患者服用反应等反馈给医生和医院,并对药品形成比较专业的评价,进而影响药品的进一步采进。根据我国《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管理办法》的规定,国家实行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制度。药品生产企业(包括进口药品的境外制药厂商)、药品经营企业、医疗机构应当按照规定报告所发现的药品不良反应。因此,在药品的流通环节,药品生产企业和药品销售企业以及直接与患者接触的医疗机构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医疗机构关于药品反应信息的评价会直接影响药品是否能够保持在流通领域;另一方面,根据《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管理办法》的规定,医疗机构也有义务进行药品反应追踪并及时进行信息报告,这必然会导致医疗机构在药品来源方面进行专业判断。同时,受国家新药推广政策、医保政策变化等影响,医院和医生可选择的药品很可能会具有特定的顺位排序,例如,国产新药优先推荐、医保政策调整后特定药品列入选择范围等。在此种情况下,特定品牌的药品可能会受政策推动于很短的时间内在医生和医疗保健的群体范围内产生广泛认知和群体效应,并进而带动患者的消费。那么,在判断该药品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时,我们就要对药品流通的上述特殊性给予充分的考虑。对于治疗特定疾病的药品,要着重审查特定相关公众对该药品商标的认知,所述特定相关公众通常也就是该药品生产、销售环节的从业人员以及药品使用终端的医务从业人员和特定疾病的患者。
笔者下文主要从法律依据、主体构成及范围界定等三个视角对相关公众界定问题做出进一步分析。
一、相关公众的法律规定
目前,我国对相关公众进行明确规定的法律文件有三个,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以及《商标审查及审理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第8条规定,商标法所称相关公众,是指与商标所标识的某类商品或服务有关的消费者和与前述商品或者服务的营销有密切关系的其他经营者。《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第2条第2款规定,相关公众包括与使用商标所标示的某类商品或者服务有关的消费者,生产前述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其他经营者以及经销渠道中所涉及的销售者和相关人员等。《商标审查及审理标准》4.1规定,驰名商标是指在中国为相关公众所熟知的商标。相关公众包括但不以下列情形为限:(1)商标所标识的商品的生产者或者服务的提供者;(2)商标所标识的商品/服务的消费者;(3)商标所标识的商品/服务在经销渠道中所涉及的经营者和相关人员等。
从内容来看,尽管在文面表述上存在区别,但三个文件在相关公众的构成范围的框定上并无实质性区别,因为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变化,营销已经从单一的分销活动发展演变为交易双方提供利益的管理活动和为社会创造价值的组织活动。[4]营销的前端起于商品的生产者和服务的提供者,中端以经销商为主要载体,末端体现为终端消费用户。而上述三个定义虽然在表述上各有偏重,但其对相关公众范围的考虑都是覆盖生产、经销和消费全链条的。
二、相关公众的主体构成
由上文分析可以得出,通常情况下,商标法中所称的“相关公众”主要由下列主体构成:产品的生产者和服务的提供者,经销环节中的批发商、零售商及物流商等,直接购买者和终端用户。需要说明的是,一般情况下,产品的生产者和服务提供者的信息占有优势明显、专业知识充分、识别能力强,因此在做相关公众认知的判断时并不需要对其进行特别考虑,这在我国相关司法判决中是有体现的。例如,在 (日本 )丰田自动车株式会社与浙江吉利汽车有限公司等侵犯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一审民事判决指出,“本案涉案产品为汽车,与其相关的消费者应指汽车的购买者或使用者,与其相关的经营者应指经销、提供汽车维修和其他服务的经营者,因此,本案中,相关公众应指汽车的购买者或使用者以及经销或提供汽车维修和其他服务的经营者。[5]该案对汽车生产者并未给予特殊考虑。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消费端,特定商品的流通渠道、使用途径、购买及消费方式等往往会导致终端用户与直接购买者之间存在区分。举例来说,药品的流通渠道极为特殊,特别是处方药。处方药的终端用户是患者,但是在药品到达患者之前,医院可能是从药品的生产商或者经销商那里直接购买药品的主体,而医生是处方药品到达终端消费者的必经主体。再如,培训用软件的直接购买者是教育机构,但是运用培训系统进行学习的终端用户是培训者和被培训者。在美国的Educat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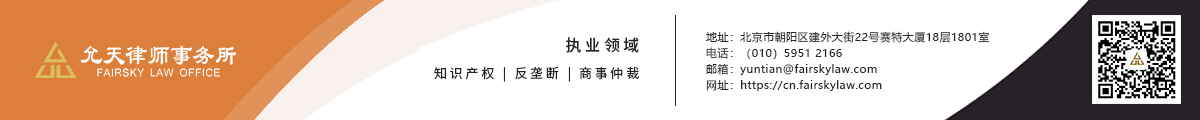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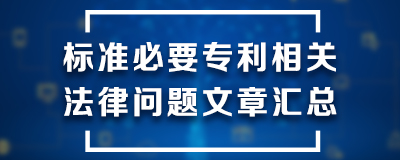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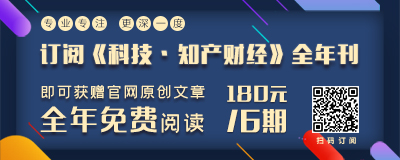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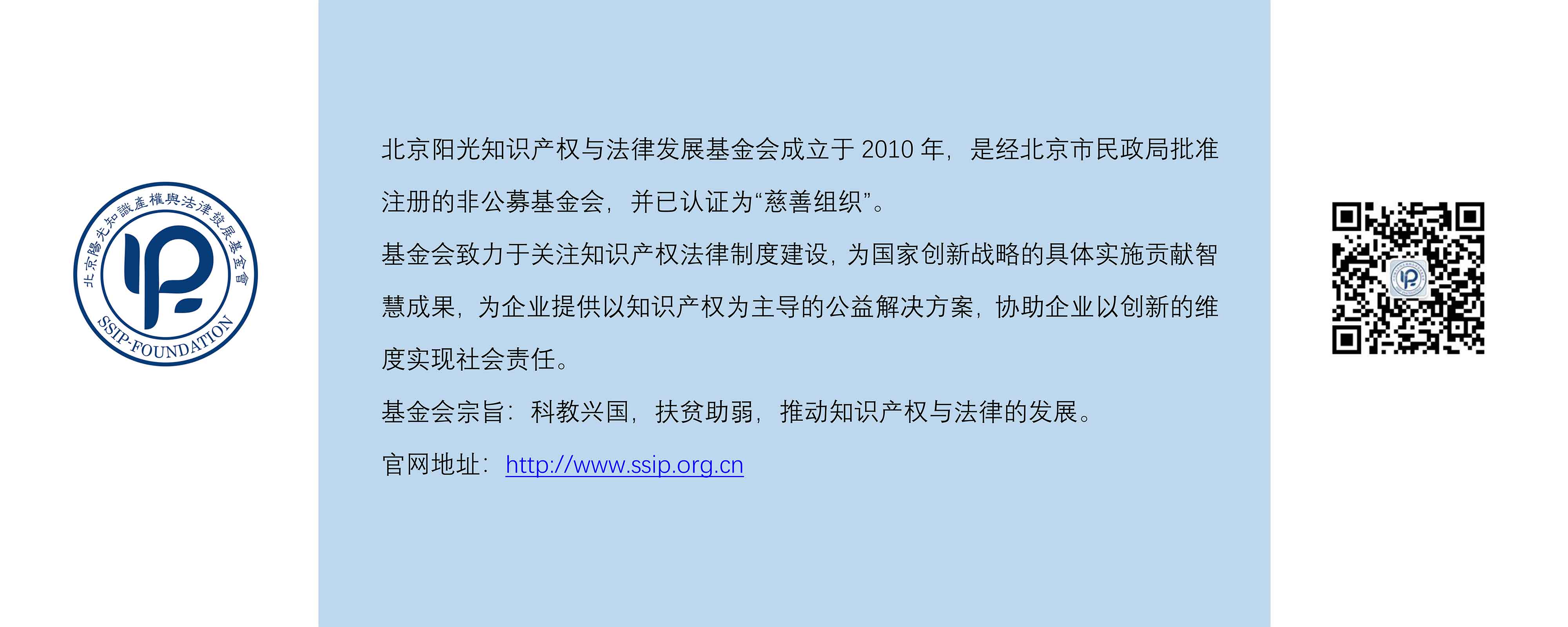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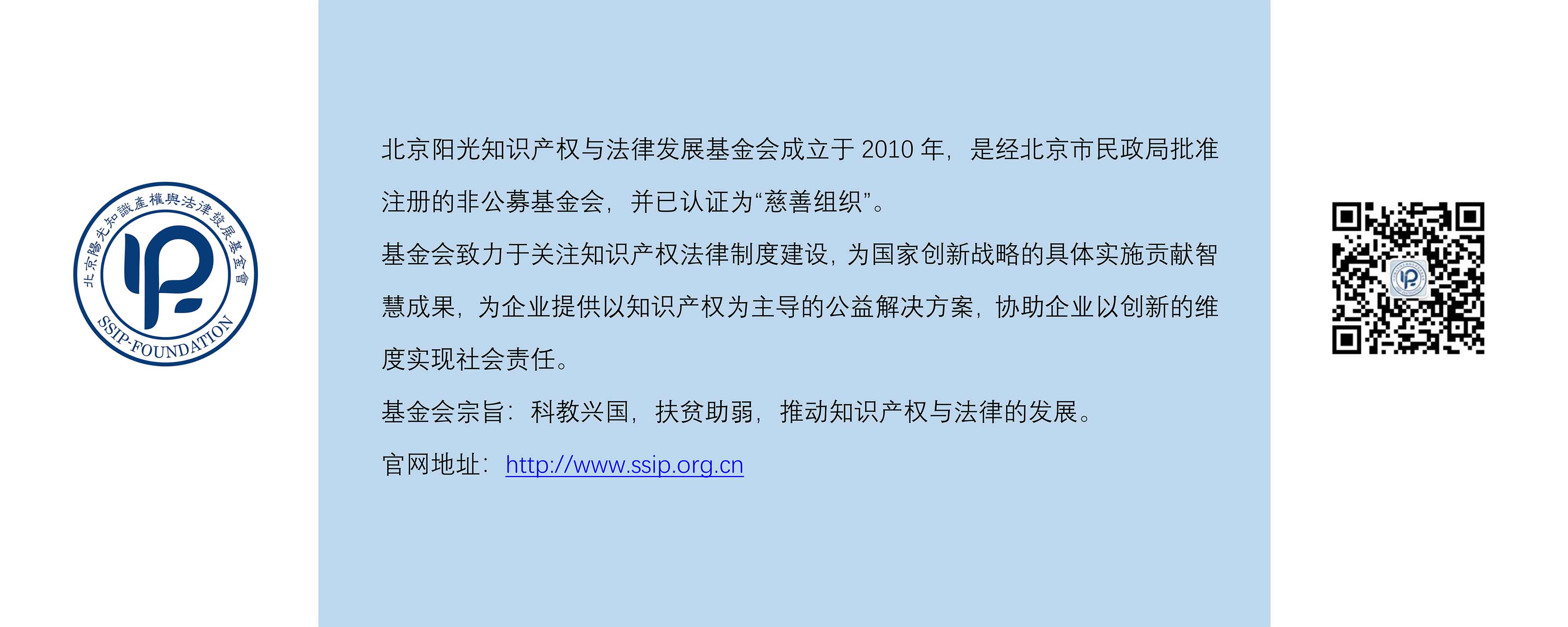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9464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9464号